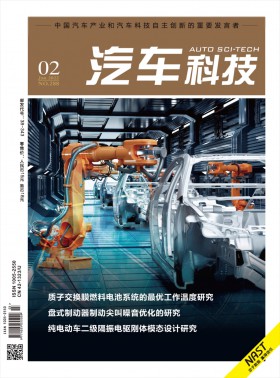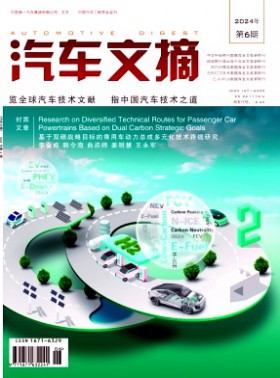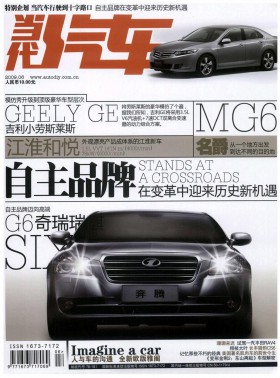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汽車歷史研究新方式,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Simon Gunn 丁雄飛 張衛(wèi)良 單位:萊斯特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杭州師范大學
1960年4月,在英國國會的一場關于道路交通的辯論中,工黨議員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GordonWalker)發(fā)表了一番演說,他的主題是“預想未來”。沃克說:汽車是能夠促進我們國家當下社會變革最有活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改變我們城市、道路和鄉(xiāng)村的面貌……我認為擁有一輛汽車正開始取代擁有一所住房,這體現(xiàn)了人的獨立感和自尊感。汽車已然日漸成為人的社會必需品,于是,我們道路上的汽車數(shù)量會急劇增長。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精力,根據(jù)汽車這一維度來重新建構我們整個工作和生活的環(huán)境。①其他的一些專家并沒有那么樂觀,他們更擔心的是大眾汽車化可能導致的種種后果。1961年,英國重要的交通規(guī)劃師柯林•布坎南(ColinBuchanan)警告?zhèn)惗爻鞘幸?guī)劃研究院:“作為機動車影響的一個結果,許多可怕的事情將會發(fā)生。”
現(xiàn)在,汽車“正威脅著城市地區(qū)的文明化運作”;根據(jù)布坎南的說法,汽車正在“產(chǎn)生讓那些地方呈現(xiàn)出一派冷漠的面貌的惡劣影響”[1]。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初,英國所有評論家一致認為,隨著大眾擁有汽車時代的到來,這個國家的景觀及其社會生活正在發(fā)生改變。在這方面,英國遠不是獨一無二的。遍及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包括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正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這些年里,社會學家們所謂的“汽車體制”的東西才嵌入進來。當然,就汽車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它們在20世紀初的時候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隨著大眾擁有汽車的規(guī)模擴展,全球大部分地區(qū)的基礎設施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才開始發(fā)生變化。在這些年里,英國的汽車數(shù)量增長了五倍。[2]1958-1968年間,法國經(jīng)歷了一場消費革命,文化評論家視其重要性堪比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工業(yè)革命。盡管洗衣機、電視機和電冰箱都是這場消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最具標志性的符號就是像雪鐵龍德尚(CitroenDS)這樣的汽車。[3]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單單在1960-1970年間,日本的汽車和卡車數(shù)量就增長了16倍,從而在10年之內創(chuàng)造了一個大眾汽車社會。即便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汽車國家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建造了全國高速公路系統(tǒng)和州際高速公路系統(tǒng)。②[4]
在20世紀下半葉,汽車體制吞噬了西方社會。沒有一個發(fā)達國家可以阻擋這種趨勢。但是,汽車大眾化在不同國家產(chǎn)生了相當不同的影響———新建了道路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物質方面的影響;政府獲得了一個大眾汽車社會,并給予回應,產(chǎn)生了政治方面的影響;汽車被作為消費者的駕駛人所專用,產(chǎn)生了文化方面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一部全球范圍的關于汽車體制的歷史。我們有的僅僅是一些零碎的關于汽車使用的編史。例如,以英國和日本為例,主要的撰稿者是一些企業(yè)史家和經(jīng)濟史家,因此,有一種著名的汽車制造和汽車企業(yè)史,例如像尼桑和福特這樣的歷史;但是,在北美之外關于汽車對城市形態(tài)或者社會生活方式影響的歷史研究卻非常罕見。③盡管如此,由于各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汽車對于碳排放和全球變暖的影響,也因為我們即將步入亞洲汽車革命這一新階段,所以,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思考1945年之后那幾十年間發(fā)生的所謂大眾汽車化的“第一次浪潮”。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樣,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已經(jīng)開始逐漸拋棄那些相對淺顯的思考方式,比如僅僅涉及汽車制造和汽車擁有規(guī)模的擴張。在這篇短文中,我試圖就大眾汽車化這一歷史現(xiàn)象,查考一些更為重要的研究新路徑。這些路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汽車體制”的概念、大眾汽車化對于城市形態(tài)的影響、大眾汽車擁有權的政治學及其對于改變日常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
一“汽車體制”
首先,最近有關汽車化的歷史研究已經(jīng)受到了社會學家們所謂“汽車體制”這一術語的影響。[5-6]這意味著,研究汽車化不能將與之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割裂開來,正是汽車化導致了這些基礎設施的出現(xiàn)。當大眾汽車制造業(y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開始騰飛的時候,一系列新的現(xiàn)象隨之應運而生:各種新的道路系統(tǒng)以應對一個飛速機動化的社會;一個為汽車業(yè)供給燃料的石化工業(yè),像殼牌和美孚這樣的跨國石油公司便是這一現(xiàn)象的縮影;汽車銷售的經(jīng)銷商網(wǎng)絡以及維修汽車的修理站;大量小型產(chǎn)業(yè)提供一切從汽車配件到道路標志的相關產(chǎn)品。其他的產(chǎn)業(yè),比如廣告業(yè),開始大規(guī)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車品牌化和偶像化。這種全新工業(yè)上層建筑的增長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汽車業(yè)在經(jīng)濟領域中越來越占有主導地位,最明顯的是,大規(guī)模的汽車產(chǎn)業(yè)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已經(jīng)確立起來。不同形式的汽車運輸業(yè)成為一個主要的就業(yè)雇主,汽車制造業(yè)亦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紡織、造船這樣的傳統(tǒng)工業(yè)走向衰弱的時期。各國政府設法通過調整消費者的借款利率來管控消費行為,因為大多數(shù)的普通人是依靠貸款來購買汽車的。同時,汽車產(chǎn)業(yè)本身也開始將自身確立為一個能夠施加政治壓力的集團,這個集團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團體、公路貨運公司、汽車銷售商團體,等等———這個集團以“公路游說團”(‘roadlobby’)著名。到20世紀60年代,這個“公路游說團”被認為是英國議會中最強大的政治壓力集團,它們試圖對從稅費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務施加影響。[7]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汽車在歷史上不僅僅是一種消費商品,或者一種交通工具,毋寧說是一種體制———汽車體制———的一部分。這種體制同時還是一種經(jīng)濟、政治、技術和社會的集合。
城市史學家的一個任務就是去理解,這種集合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很多國家是在20世紀50-70年代之間確立起來,但美國要更早一些,在20世紀的30-50年代之間就已經(jīng)建立。只有意識到汽車深度嵌入社會這一本質,我們才能理解以下事實:汽車本身具有非凡的適應能力;政客們屢次試圖限制汽車使用的努力,皆毫無效果;汽車有能力在油價連番上漲之后依然生存下來。和其他的基礎設施形態(tài)一樣,如電力、自來水、計算機網(wǎng)絡等,汽車化已經(jīng)深深地植根于我們的建筑形式、日常經(jīng)濟乃至現(xiàn)代都市社會的消費想象之中。[8]#p#分頁標題#e#
二汽車與城市形態(tài)
大眾汽車化的第二個特征是汽車對于生活環(huán)境造成的影響。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規(guī)劃建設了各種道路系統(tǒng),包括高速公路和州際公路,這改變了道路所經(jīng)之地的景觀,也改變了沿途城鎮(zhèn)的經(jīng)濟,就像19世紀鐵路所發(fā)生的作用一樣。[9]這些道路系統(tǒng)的作用在交通最集中的城鎮(zhèn)和城市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首先,私人汽車的普及加快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的進程,亦即人們搬離市中心的街區(qū),遷往位于城市邊緣的郊區(qū)社區(qū)。正如肯尼思•杰克遜(KennethJackson)在《馬唐草邊疆:美國的郊區(qū)化》(CrabgrassFrontier)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雖然大眾汽車化并沒有產(chǎn)生美國郊區(qū)化的經(jīng)典模式,因為后者出現(xiàn)于汽車擁有擴張之前的20世紀20年代,但是大眾汽車化大幅度地促進了郊區(qū)化,于是,像洛杉磯這樣的城市就變成了邁克•戴維斯(MikeDavis)所謂的“一個沒有邊界的城市”:洛杉磯以一個永遠擴張的郊區(qū)網(wǎng)絡為特征,這種網(wǎng)絡互相聯(lián)系的要點便是高速公路。[10-11]然而,大眾汽車化導致的不僅僅是低密度的郊區(qū)化,更是一次對城市的激進重組。在二戰(zhàn)之后的一段時期,許多歐洲國家的城市規(guī)劃師抓住時機,圍繞著汽車優(yōu)先原則重構城市。最突出的例子是聯(lián)邦德國,在像科隆和漢堡這樣曾遭受炸彈猛烈轟炸的城市,如今大量的市內高速公路便在其中穿行。[12]嶄新的環(huán)城公路圍繞著各大城市,從而限定了市中心的范圍,市中心被改造為一個沒有居民居住的空間,僅留給各種商店和辦公樓———這也就形成了所謂的中心商務區(qū)。在一些國家,比如說英國在20世紀40-70年代期間,新建道路與清除貧民窟相吻合;在伯明翰,內環(huán)路的建造導致沿途大約3萬座房屋被鏟平。[13]毗鄰新建道路的區(qū)域皆成了“衰退”(twilight)區(qū),那里人口日益減少,有不能或是不愿搬離的老人和商店店主,過著岌岌可危的生活,這是高速公路將他們與城市其他區(qū)域隔離開來的結果。[14]新的道路系統(tǒng)實際上改變了整個城市的社會地理學,這往往是城市規(guī)劃師所始料不及的方面。第三,大眾汽車化時代的到來催生了一種關于城市的新概念,亦即城市以汽車擁有者而非以行人、騎自行車人或有軌電車駕駛者為優(yōu)先來組織。
對此,芭芭拉•施穆基(BarbaraSchmucki)更是得出以下結論: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西德的規(guī)劃師將城市視為“交通機器”,而城市規(guī)劃的主要目標便是為源源不斷的汽車提高速度。[15]不過,城市規(guī)劃本身也開始思考如何容納汽車———英國規(guī)劃師柯林•布坎南在其1963年著名的政府報告《城市交通》(TrafficinTowns)中使用了“交通建筑學”(trafficarchitecture)這樣的說法。[16]英國的確是發(fā)展這種新的“交通建筑學”的先行者。尤為重要的是,道路安全運動的相關人士提出了以下觀念:汽車交通應該與步行者嚴格分開。在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與上述觀念一起出現(xiàn)的還有:城市既要被縱向規(guī)劃也要被橫向規(guī)劃,從而分區(qū)規(guī)劃浮出水面。布坎南為倫敦的牛津街提出了一套分層式的設計方案,例如,汽車行駛在地面這一層,步行購物消費在上一層,而居民公寓在最高一層。這樣的設計轉而催生了所謂“超級建筑”(megastructure)的構想,即在這樣的建筑內部會設計道路和車庫,比如位于伯明翰的斗牛場購物中心(BullRing)。在一些新的城市,像蘇格蘭的坎伯諾爾德,把城市中心建成一個巨大的超級建筑,以供人們購物、工作和居住,而建筑本身由新型的道路系統(tǒng)相連接。[17]在這個意義上,汽車時代的到來促使規(guī)劃師和政治家去想象新的組織城市結構的方式,從而能夠回應新興的汽車化社會的理念。
三汽車的政治學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個研究路徑是,與汽車化相關的政治學和文化。我已經(jīng)指出,隨著汽車生產(chǎn)成為制造業(yè)經(jīng)濟的核心,社會開始日益依賴石化燃料,公路游說團也開始發(fā)揮能夠感覺到的影響,于是,在20世紀50—60年代汽車體制嵌入社會的時期,汽車體制開始重塑很多西方國家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一些晚近的歷史學家已經(jīng)意識到,汽車對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著更深刻的影響。在《司機共和國》(RepublicofDrivers)一書中,戈登•塞勒(CottonSeiler)認為,正是通過汽車化的各種實踐和形象,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人才理解自我與美國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解美國所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獨特形式。塞勒認為,“在20世紀,開車行為本身就呈現(xiàn)了典型的‘美國人’形象”,“做一個美國人就等于要將汽車化視為自己的棲居之所和生活習慣”。[18]我并不想詳細闡述塞勒討論的細節(jié)部分,或者判斷其觀點的對錯。這里的關鍵在于,他試圖通過透視由技術所媒介的主體性來理解政治;汽車被視為一種媒介物,通過這個媒介,清晰地表達對美國的國家認同以及嵌入到這種認同中的各種東西,不論是新移民還是既有分屬的不同公民群體。在法國,20世紀60年代克里斯廷•羅斯(KristinRoss)把汽車放在中心位置,對所謂的“日常生活殖民化”(colonizationofeverydaylife)做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在同一時期,由于法國在海外的非殖民化和資本主義,法國政府便將注意力集中在60年代國內的消費革命,這場消費革命的縮影就是汽車———“20世紀一切現(xiàn)代化的核心交通工具”[3](P.19)。就文化表征而言,羅斯指出,汽車在各大報刊上無處不在;大眾迷戀于像小說家阿爾貝•加繆這樣的全國名人慘遭車禍死于非命的新聞;在一些電影里,也展現(xiàn)了人們對于汽車的迷戀,像讓-呂克•戈達爾的《狂人皮埃羅》(1965)和馬塞爾•卡恩的《說謊者們》(1959)。對于批評家羅蘭•巴特來說,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話語中,只有食物是和汽車一樣重要的。汽車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汽車有助于在法國的日常生活中嵌入一種新的消費文化,一種“極端的日常性”(sublimeeverydayness),與其他相對遜色但也是消費革命必要組成部分的東西共同發(fā)生作用,像吸塵器和洗衣機。[3](P.22)在英國也是這樣的狀況,最近的一些寫作已經(jīng)指出,汽車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眾文化中處于中心地位。在英國很具特色的是,討論汽車問題的框架是在有關階級的爭論之中的,特別關注所謂的“富裕工人”(affluentworker)———在類似汽車制造業(yè)這樣行業(yè)中的高技能和高薪酬的男性工人,社會學家把他們視為正在發(fā)展一種私人化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這與工聯(lián)主義、合作社運動和工黨所體現(xiàn)的集體主義傳統(tǒng)是背道而馳的。用政治術語來說,這些工人被認為正在經(jīng)歷一個“資產(chǎn)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的過程,這讓他們遠離社會主義和階級意識,邁向一種被消費所驅動的生活方式,而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像汽車和電視這樣的物品將勢不可擋地導致一套“中產(chǎn)階級”的、保守的社會和政治態(tài)度。④不過,在我看來,更有意義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的大眾汽車擁有權的擴散開始以新的范式來編織生活。社會觀察家邁克爾•揚(MichaelYoung)和彼得維爾•莫特(PeterWilmott)在1958年就發(fā)現(xiàn)了這點,通過考察倫敦周邊新建房地產(chǎn)的布局以及家庭、工作地點、商店和親戚家之間的距離,發(fā)現(xiàn)這些都是“駕駛汽車的距離:一輛汽車就像一部電話能夠克服地理上的差距,從而將分散的生活組織成一個更易管理的整體”[19]。從我個人研究的早期證據(jù)來看,上述對生活的重組并不必然意味著對于過去種種生活模式的破壞。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用剛剛獲得的汽車來維系與原先社區(qū)以及熟人的聯(lián)系:開車回過去的酒吧(依然是“當?shù)氐?rdquo;),找人一起踢足球,去拜訪老鄰居、老朋友和親戚。起碼就短期而言,“社區(qū)”(Community)適應著汽車,而非被汽車所瓦解。⑤#p#分頁標題#e#
四結論:20世紀西方的汽車化
這些大眾汽車化研究的新路徑是把汽車作為接近于城市現(xiàn)代性的中心來思考的,不論是否假借了偉大的高速公路規(guī)劃師的做法,像紐約的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抑或將汽車與大眾神話式的自由相聯(lián)系。正如這里指出的,汽車的意義部分地在于其象征性;比起其他任何商品,汽車更加能象征自由地行動、自由地走出去大干一場,而這是構成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概念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過,正如我已經(jīng)試圖強調的,比這點意義更加深遠的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眾汽車化導致了種種物質與政治的后果。我們看到城市轉型的物質方面,城市根據(jù)汽車優(yōu)先原則來重組或重建。有人或許會說,汽車化成為了20世紀后半葉城市規(guī)劃的指導原則。
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從事于汽車化政治學的研究,如“碳經(jīng)濟”的歷史、石油政治學、在重新界定階級、種族和性別這三個范疇時汽車所起的作用。⑥我們只是剛剛開啟對于這方面歷史的書寫;然而,即便我們開始做這些工作,我們也都意識到21世紀的汽車化歷史將不僅僅由西方來書寫。于是,將會有關于南半球和東半球的大眾汽車化和特大型城市的歷史,將會有關于墨西哥城、首爾和上海的歷史。⑦我們還不知道這些歷史將會呈現(xiàn)出什么面貌,也不知道是什么主題,像氣候變化一樣,也可能這樣來書寫。可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當這些新的汽車化歷史在2015年或2050年被書寫出來的時候,將非常不同于自由、消費主義和現(xiàn)代性的敘事,因為它伴隨著整個20世紀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的汽車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