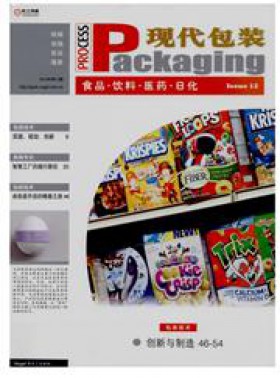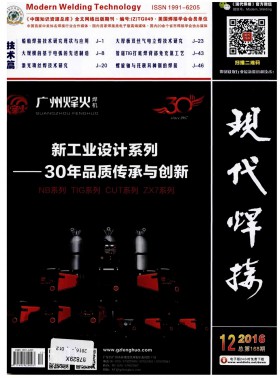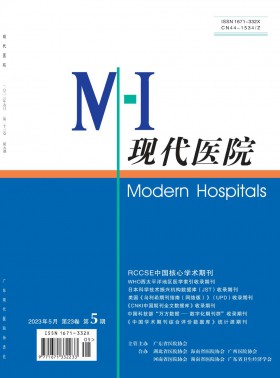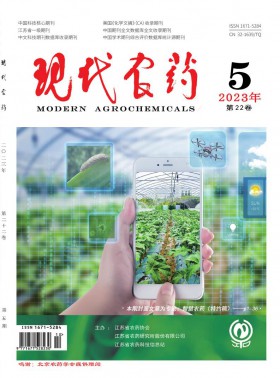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白話與現代短篇歷史小說,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宋先紅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將歷史作為精神活動的產物,較好地闡釋了歷史敘述與人對歷史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也是中國現代短篇歷史小說采取的話語方式的最好的注腳。我們認為中國短篇歷史小說話語方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現代白話和短篇小說的呈現方式。這三個方面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短篇歷史小說的主要特征,是通過比較的方式得出來的。作為現代文學重要一支的現代歷史小說,從外部形式上講,它與歷史文本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語體———文言與白話的差異。僅就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演變而言,就存在著由文言的史傳文!半文半白的長篇歷史演義!現代白話的現代歷史小說的轉變過程。而由“五四”白話文運動而引起的“文學革命”本身就是集語言本體論與工具論一身的思想啟蒙運動。所以,從語體選擇的角度來關注現代歷史小說的語言問題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雖然筆者并不完全贊同“文學語言的選擇永遠是一種政治事件,是一種政治無意識的觀念外化”[1],但也不得不承認任何一種語言都有書面語言與白話兩種語體的區分,且這兩種語體在使用者、使用者的歷史認知、使用場合和功用等方面的確有很大的區別。
1文言與正史書寫
文言所代表的書面語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并不為社會的全民所用,只有少數有特權和身份的人才能學習和使用它,而由它記錄下來的典籍毫無疑問是它的使用者的思想產物并對后來的學習者產生了影響。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史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官修史書的傳統,所以文言、歷史、史官的封建正統歷史認知就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特殊局面。因此,探討文言與正史書寫之間的關系,其實是分析封建正統的思想意識如何通過文言這種書寫工具滲透到它的使用者──史官頭腦中并通過正史的書寫表現出來。
1.1倉頡造書的暗示:史官與書面語
《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初造書契。”后人由此斷定:一,倉頡的身份是黃帝時的史官,二,漢字為倉頡所造。姑且不論這個傳說是否屬實,但是這則引文透露這樣的一個信息:在中國古代,史官和文字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進一步還可以說,只有掌握了文字才能作史官、記錄后人所稱的“歷史”。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學習、掌握文字并成為史官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從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狀況看到:學習文字其實是少數人的特權。《漢書•藝文志》源于劉歆《七略》,在敘諸子十家時,皆謂出于某官,如“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2]其實這里的某官,就是周代王官之所掌。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中闡發道: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又以知私門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后,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于庶幾于知言之學者也。[3]由此可見古代的文化要典都由百司之史掌握,所以有“百家之學,悉在官府”的說法,而能夠接近要典并向百史之官學習者,也只有公卿子弟,所謂庶民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機會。直到周代衰亡之際,王官失守,散為諸子百家,民間才得以師弟子的形式傳授知識。私授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文化傳播的范圍,但是他們授課的內容———也就是課本仍舊是用古代語言寫成的六藝和諸子百家的典籍,而不是私塾老師自己的著作,孔子的“述而不作”應該是這個方面的有力證明。也就是說無論是官學和私學的授課內容都來源于以史官為代表的人所做的著述中。據此可以得出書面語的如下特點。書面語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創造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書面語言的使用幾乎成了一種特權和身份的象征。它之所以被蒙上一層意識形態的面紗,與書面語言的以下特點有關:1)書面語言作為人類文明的創造物,與口語相比,需要通過教育才能夠獲得,所以在人類物質水平不發達的一段時間內,它的獲得和受教育機會一樣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那少數人幾乎就是特權階層和統治階級的代表。2)書面語言可以通過媒介得以保存的特點使人類社會活動通過書面語言的形式流傳下來,而人類社會活動如何書寫就只能由上述少數懂得書面文字的人所決定。如果將文字書寫當作聲音的另外一種形式,那么后世聽到的聲音只有特權階層或統治階級的聲音,而只會使用口語交流的大多數人的聲音早就在歷史的時空中蕩然無存。在這種意義上,書寫能力就意味話語機會和話語能力,也意味著被歷史記憶的可能性。3)書面文獻作為后來教育所使用的資源,它所承載的少數人的思想同時被傳達到受教育者那里,對受教育者起到一種浸潤和同化作用,所以,書面語作為語言被受教育者學習的同時,它所承載的思想和意識也被接納和吸收,并作為一種身份資本而一再得到尊奉和宣揚。在這種層面上說某種語言的使用者就是某種思想的遵循者并不過分。從而,語體的不同選擇就昭示著使用者不同的社會身份和不同的使用目的以及對事物的不同認知。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于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說“智力和語言只允許和要求有相互適應的形式”,雖然指的是不同語言與民族精神的關系,但我認為它同樣適用于討論同一種語言中不同的語體與使用者思想之間的關系。當時的文言只能為以史官為代表的少數人使用,這些使用者所受的教育乃是與統治者密切相關的正統思想。這一點,可以從史家修史的原則和觀點中得以明證。
1.2歷史、文言與史官的封建正統歷史認知
我國史書的寫作濫觴于孔子刪定的《春秋》和傳為左丘明著作的《春秋左氏傳》。經過后人闡發,“孔子刪定《春秋》”是孔子“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禮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委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4]11可見孔子所撰《春秋》并不完全是魯國歷史的原貌,而是根據孔子“勸惡揚善”、“提倡王霸、王道”、“強調以封建等級次序為核心的‘禮’”的目的對原有歷史進行重新編訂的。《春秋》為后世史書的做法開了先例,同時孔子連同其他先秦的賢士用自己的學說“奠定了整個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論晚近歷史》)。從先秦諸子大多“不用于世”的遭遇來看,他們的話語并沒有在現實層面得到實現,這就有待于后世帝王用自己的權力來產生實際效應。官修史書就是實現這種話語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司馬遷《史記》雖然是私家著作,表達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但它之所以獲得正史的崇高地位,固然與《史記》在敘事、記載等方面的成就有關,也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史記》從撰述目的到實踐都是符合儒家正統思想的。從他推崇孔子的話來看,他的“古今之變”還是以王道為依據的。從各下面史家的論述也可以看出來這一點。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之廢,王道之大者。”[5]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開辟草昧,歲紀綿綿,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原乎載籍制作業,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予奪,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6]劉知己《史通•直書第二十四》:“況史之為務也,申以勸誡,樹之風聲。”[4]249劉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制第一》:“用使之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為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4]389司馬光《資治通鑒序》:“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本,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7]官修史書作為各個朝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它的理想宗旨就是將這個“道”通過“撰述”的方式在歷史中得以表達、并幻想帝王能借鑒學習歷史成為“道”的完美體現者。中國各朝各代的明臣賢士也無一例外的都是“忠君”、“重道”的表率。幾千年過去了,他們所遵的“道”還是“先王之道”,而且始終堅信有那么一個“道”可以貫穿歷史,經天緯地。這樣,文言、史書、儒家正統觀念三位一體的局面也得以形成。文言的簡潔、古奧、莊重、正式等特點也在經典的一再重復、歷史的一再撰寫的過程中得到強化和確認。#p#分頁標題#e#
2半文半白與中國傳統長篇歷史演義
文言與白話作為語體不僅存在使用場合的不同,也跟使用對象的知識層次和接受范圍、接受程度有關。文言是書面語言,是和智識階層聯系在一起的,而白話是老百姓的語言,是日常生活語言。要和老百姓溝通并要他們接受某一特定的觀點或信仰,就必須用他們的語言。有人曾經講過,中國古代社會思想存在上下層、表里、雅俗分離的現象。在統治階級上層、社會思想的表層和廣大知識階層,他們奉行的是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在普通老百姓、社會思想的里層,他們奉行的是一套功利的、世俗的觀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著文言與白話兩大不同的語言系統。所以,要想從上至下地推行某種思想或者獲取更多的受眾,推行者在迎合百姓口味的同時,還得調整所使用的語言。值得注意的是,世俗變文中以中國古代歷史為內容的有:《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文》、《李陵變文》、《捉季布傳文一卷》、《前漢劉家太子傳》、《孟姜女變文》、《王昭君變文》、《舜子變》、《董永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一卷》等。歷史變文藝術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它基于史實又不為史實所限,這種真實與虛幻相結合的筆法,使歷史傳說人物以有血有肉的面目呈現在變文中。這無疑影響了后世歷史演義的寫法。
宋代“講史”在語言上對歷史作民間傾向的改造,更多的是出于娛樂、商業利益的考慮并充分注意到受眾的文化層次特點。“講史”作為宋代民間說唱藝術“說話”的四家之一,和“小說”是最受聽眾歡迎的形式。它面對的主要聽眾是城市里聚居的商人、小業主、手工業者、工匠、軍士、吏員、伙計仆役等等構成的一個市民階層。說書人在瓦肆里面對上述觀眾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如《武王伐紂書》、《七國春秋后集》、《秦并六國平話》、《前漢書續集》、《三國志平話》、《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等,都是有文獻根據的。如果說書人只是照搬史書,自然顯得嚴肅、呆板,不受聽眾歡迎。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說:“大抵唐人選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斗,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欲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他在這里說的是小說,但是面對相同的受眾,其所論的“通俗”標準同樣適用于“講史”的說法。明代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蔣大器(肖愚子)序說:“前代嘗以野史作為平話,今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厭之。”[8]這里“言辭鄙謬”就是“講史”的語言特點,雖然“士君子多厭之”,可是仍不妨礙普通市民對之青睞。歷史演義是在“平話”的基礎上,經過若干代人的不斷修改創造,最后由文人編纂而成的。它一方面繼承了“平話”民間化的特點,另一方面又由于文人個人的創造而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而使它與史書和“平話”相比更具文學品格,也打下了作家個人在時代特點、世界觀、歷史觀上的很多印記。可以說,歷史演義是歷史資源、民間文化、文人創作三者統一的結果,其敘事語言的半文半白是這三方面糅合的最好證明。
最早對《三國演義》的語言特點作出說明的是明人蔣大器。他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來總括《三國演義》的語言面貌,并獲得了廣泛的認同。高儒《百川書志》則把《三國演義》的語言概括為“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詼諧之氣”。也就是說,《三國演義》的語言特點是介于純文言和口語之間的一種半文半白的書面語言。它既與說話的產物有關、加工者的文人身份有關,也與“歷史演義”這一文體有關。作為說話的產物,它的誕生地點是在熱鬧集市的瓦肆勾欄,所以它必須是口語的,是通俗易懂的。但演義的內容是歷史的、而非現代的,與話本小說相比,為了造成一種“歷史感”,使讀者感到作品的語言“時態”和歷史內容相一致,給讀者一種“真實”的假象,必然離口語較遠。生活在當時的文人將這兩種語言進行了調控、折衷,創造出一種既適宜大眾接受、又有適當歷史距離的文白夾雜的語言。具體說來,演義中的表章、信柬、詔旨、正式應對等內容多引用原有歷史文獻,如《三國演義》“定三分亮出茅廬”、“諸葛亮智激孫權”、“白帝城先主托孤”、“孔明揮淚斬馬謖”等章節中諸葛亮的語言幾乎是原封不動的引用了陳壽《三國志•蜀國•諸葛亮傳》中的有關章節。而對戰爭場面的描寫和渲染,則吸收了口語中通俗、極盡鋪張和夸飾的特點。例如在《三國演義》第五回呂布大戰劉關張一節中和第四十一回趙云趙子龍單騎救主上述兩則文中,“了”、“抖擻精神”、“把馬一拍”、“丁字兒”、“戰不到”、“轉燈兒”、“當時”、“只顧”、“不想”、“奪了”等都不是正統文言,而是當時的白話。那是不是歷史演義的語言作了朝通俗化方向的改變,就意味著它的主題跟帝王將相無關呢,或是思想離百姓更近一層呢?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首先,演義著重演述的還是《三國志》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他們的卓越事功,而且作者運用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對書中人物如曹操的奸雄、劉備的仁德、諸葛亮的智慧等等進行了大肆的夸張和渲染,以致“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狀劉備多仁而近偽”,使普通老百姓以一種仰望的角度看待這些已經逝去、但曾經左右歷史的人物,而進一步拉開自己和統治者的距離。其次,《三國志演義》的諸多主題中,儒家仁政思想是它的主導思想,不僅貫穿全部情節,而且貫通著對所有人物的評價。羅貫中就是用這個思想來處理千頭萬緒的三國歷史人物的,他反復強調: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基于此,《三國志通俗演義》雖然摒棄了平話中的因果報應觀念,使這段歷史成為一個悲劇,但德卻是全部情節的軸心。劉備集團廣施仁義,其行為充分體現作者出作者仁義高于成敗的觀點。如在劉備敗走江陵時,出現了十萬民眾隨部隊撤退、日行十余里的壯觀場面。面對曹操精兵的追殺,諸葛亮勸劉備暫棄百姓,輕裝前進,劉備說:“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又如當關羽戰死麥城,劉備不顧趙云等的勸說,感情用事,興師報仇,其理由是:“朕不與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可見,書中種種渲染、改動都是為了宣揚、贊頌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傳統思想,不出《資治通鑒》等正史闡發的義理之外。#p#分頁標題#e#
由此可見古代文人在長篇歷史演義的創作中雖然沿襲了“說話人”的口吻對敘事語言作了口語化的調整,使歷史演義獲得了娛樂性,但是創作主體———封建文人的正統儒家價值觀念和他們對歷史文本的固守,使他們不可能換一種眼光和一個角度打量歷史。從語言的角度說,白話在他們眼里只是獲取讀者的一種手段,而不能象文言那樣成為某種意識的承載者,或者說長篇歷史演義的作者根本無意賦予白話某種區別于正統儒家觀念的思想內涵。所以,半文半白的文學依舊是舊文學,白話再怎么向書面滲透,它始終是為通俗和娛樂的,而其中的思想意識始終是封建正統的和教化的。白話與現代意識的緊密結合還需要在現代短篇歷史小說里得到真正實現。
3現代白話與現代短篇歷史小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集文學、語言、政治、文化于一身的啟蒙運動。雖然在名稱上有“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等不同的說法,但它實際上是以西方“民主與科學”觀念為基礎,以語言變革為切入點,最終表現在文學上取得極大成就的一次思想文化、社會政治的革命。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自創刊之日起就通過譯述和介紹大量宣傳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陳獨秀、、易白沙等人先后發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晨鐘”之使命》、《孔子平議》等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舊禮教、舊文化,倡導民主與科學,宣傳西方的新思想、新學說,肯定人的價值、尊嚴、個性與自由,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人的解放運動”。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文學語言為切入點,將語言變革和思想變革融為一體。文中胡適提出:“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之中,“一曰,須言之有物”和“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是內容方面的,而“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五曰,務去陳詞濫調”、“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都是關乎語言方面的。而他在“不摹仿古人”這一項中,引人注意地提出了“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以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9]胡適在這里單單拈出“白話小說”作為“非摹仿之作”,一方面是他的文學進化論的思想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為他在以后用文言/白話的語言形式區別死的文學和活的文學以及撰寫《白話文學史》張目。一個月后,陳獨秀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以更為激進的態度舉起“文學革命”的大纛,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10]其中“雕琢的阿諛的”、“迂晦的艱澀的”、“明了的通俗的”是指文學的語言特點,而“貴族”、“國民”、“古典”、“寫實”、“山林”、“社會”乃是就文學的思想內容而言,所以,他的“三大主義”就將文學、語言、思想的變革裹挾在一起。繼而,錢玄同《寄陳獨秀》(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傅斯年《文學革命申義》(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號)、《怎樣做白話文》(1919年二月一日《新潮》1卷2號)、周作人《人的文學》(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號)、《平民文學》(1919年1月19日《每周評論》第5號)對此做出積極的響應,對新文學在語言建設和思想觀念兩方面發出了倡議。在現代文學語言改革的浩大聲勢中,魯迅于1918年5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雜志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史上成功的開山之作,表示中國短篇小說的現代性就體現在新的語言形式、結構形式、思想特點上。同樣是魯迅以《補天》開始了中國歷史小說的現作。現代歷史小說就是在現代短篇小說對體式和語言革新的基礎上開始了自己有別于史傳文體和傳統長篇歷史演義的創作之旅。現代白話本身的特點也許更能說明現代短篇歷史小說與長篇歷史小說的不同點和現代歷史小說由白話形式帶來的內在思想上的現代性。高玉在《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中說:“新白話在形式上的確從古代白話而來,但它又不同于中國古代白話,它已經融進了大量的歐化的術語、概念、范疇,是一種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話語方式。”[11]用這樣的白話寫歷史小說,帶給我們的必定是建立在新的語言形式之上的新思想和新視野。現代漢語是口語、西方語言和文言等多種語言資源綜合融會的結果,下面我們主要看現代漢語的口語化、歐化和文言的保留對現代歷史小說創作的影響。
3.1現代漢語的歐化與現代歷史小說中“人”的情緒的表達
現代漢語的歐化主要表現在大量歐化詞匯的運用,人物現代情緒的表達主要是指小說人物的各種情緒如欲望的覺醒、個性的抒發等的感知和表達。在20世紀初的中國,各種“人”的情緒和欲望幾乎全部來自對西方的譯述和介紹,所以這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某種同構的關系。傅斯年在《怎樣做白話文》中說:“我們的語言,實在有點不長進:有的事物沒有名字,有的意思說不出來;太簡單,太質直;曲折少,層次少。我們拿幾種西文演說集看,說得真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若是把他移成中國得話,文字得妙用全失了,層次減了,曲折少了,變化去了———總而言之,詞不達意了。”[12]說到底,歐化就是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在思維結構、表達內容和表達形式上感到古代漢語的不夠用而向西方看齊的一種結果。要想準確地表達從西方借來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最簡單、最直接、最貼切的辦法就是“直用西洋詞法”。于是,雙音詞及復音詞劇增,音譯詞加入到現代漢語中,“漢語句子的附加成分,像定語、狀語、補語明顯加長,”[13]詞匯傳達的思想歐化了,舊有詞匯使之具有新的意義等新的語法、詞匯特點出現在現代漢語中。這不僅使古人能夠說著今人的語言,而且形成語言在修辭上的多重效果,從而加強與現實的緊密聯系,這在魯迅、郭沫若、廖沫沙等人的歷史小說中得到很強的體現(在后文中我們將要詳細論述),而且對現代歷史小說的敘事技巧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在現代歷史小說如施蟄存、茅盾、李拓之等的作品中得到尤為鮮明的體現。例如在施蟄存的《鳩摩羅什》的第一段中,小說以鳩摩羅什視點出發,寫他和他的妻子騎著駱駝走在往秦國去的路上的所見所聞所感。敘事語言中夾雜著大段的景物和心理描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非常少見,但是在“現代歷史小說”中卻很常見。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在敘事中已經非常嫻熟地用著“歐化”色彩很濃的長句。句子變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詞匯方面的變化,①雙音節、多音節詞匯取代單音節詞匯。②數量詞的出現。③大量連接詞的出現。二是語法方面:①主語前面有長長的定語。②狀語前置。③頻繁使用被動句。④多用復句,如并列復句、轉折復句等。這幾種特點在以上這個三百多字的段落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如果使用古代漢語,上面這段文字就會變成:“大智鳩摩羅什攜妻過涼州,前往秦國。時呂氏涼州既遭秦兵,國破城亡,滿目荒涼”。肯定不會出現諸如“給侵曉的沙漠風吹拂著,寬大的襟袖和腰帶飄揚在金色的太陽光里”這樣細致、渲染的描寫,也不會出現“有幾所給那直到前幾天停止的猛烈的戰爭毀了的堡壘的廢墟上,還縷縷地升上白色和黑色地于今矗起在半天里地烽火臺上”這樣前置的、冗長的狀語。書面的“歐化”句式無疑會減緩敘事的節奏,而更加適合細致、精確的景物、心理描寫,為后來鳩摩羅什性欲和道義的沖突作了良好的鋪墊。#p#分頁標題#e#
3.2口語化與向大眾傳遞現代情緒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以文學運動為突破口的啟蒙運動,現代啟蒙家試圖通過對文學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品質的革新達到宣傳西方現代“民主和科學”思想的目的,那么,為了更好的言說這個來自西方的“現代”,達到為大眾所理解和認可的效果,大眾口語也是歐化之外的另一種語言選擇。現代文學通過大眾所熟知的語言形式———口語將現代精神傳達給被啟蒙者,從而將置身于蒙昧狀態的“祥林嫂”、“閏土”們引向現代,所以,現代文學的口語運用表達的就是啟蒙者對大眾的一種言說欲望和言說方式。晚清時期,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已經開了將口語引入文學的先聲,“五四”新文學運動期間,諸位啟蒙者也紛紛發表文章談論用口語寫作的重要性。胡適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從“八事入手”,提出了文學改革的大致方向,接著又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以上“八事”做出了“肯定的口氣”的修改,實際上就是一則做“國語的文學”的宣言,他提出“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要說我自己的話”,“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實際上還是繼續抨擊文言的“死文學”,提倡用“口語”寫出活的文學。傅斯年在《如何做白話文》中就將“留心自己的說話,留心聽別人的說話”作為做好白話文的兩條資源中的第一條,他說:“文學的妙用,僅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想把這層辦到,唯有憑藉說話里自然的簡截的活潑的手段。”[12]魯迅1927年在香港青年會講上發表了以《無聲的中國》為題的演講,更是講出了文言導致中國民眾無法發出自己聲音的害處———“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象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久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所以“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講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14]在這里,“口語”的運用已經清楚地和交流、和國家民眾的思想狀態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了,啟蒙者們想通過“口語”啟蒙大眾的目的也呼之而出了。
用歷史為教材,用口語的方式引導大家用民主和科學的觀念重新看待歷史,看到中國壞的根子究竟在哪里,這不失為啟蒙大眾最實在的辦法。魯迅說他用白話寫歷史小說是“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沒有把歷史小說的創作用意說得比這更直白的話了。鄭振鐸在《玄武門之變•序》中就指出:“中國的歷史一向是蒙著一層厚幕或戴著一具假面具的”,所以有必要“在多方面的剝落他們的假面具,而顯示出他們的真面目來”,并“揭發帝王們的丑相”,宋云彬的《玄武門之變》是如此,茅盾的歷史小說《石碣》是如此,鄭振鐸自己的《湯禱篇》也是如此。所以,歷史小說用口語進行寫作,其作用不是象“歷史故事”那樣普及歷史知識,而是擔負了更多啟蒙大眾的責任,所以其寫法不能只是白話翻譯文言歷史,而是有更多的思想內涵。現以魯迅的《奔月》來說明一下這個問題。
《奔月》中,魯迅不僅虛構了射日之后的后羿在打獵生涯中的窘境和因為獵績不佳遭到嫦娥冷遇的的日常細節。文中大量“生活化”的白話口語完全打破了人們對一個英姿挺拔、連射九日的英雄的想象,其言語之中的無奈和俯就完全是現實生活中一個無力照顧妻子的男子心聲。因為人物語言和現實語言的一致,就讓讀者不只是坐在戲棚中聽到或是在書中“隔岸觀火”地讀到、而是站在當下、進入人物處境中真切地體會到了一個末路英雄的無奈和悲哀。在那樣的社會,英雄的命運尚且如此,常人的生活更何以堪?美麗神話中的女子尚且如此世俗而且背信棄義,俗人的道德更值得我們幾許信任?作品用大眾能聽懂的語言將正史中的人物放置在日常生活中,說出了大眾在日常中感受到卻說不出的情緒。
4結束語
從文言正史到半文半白的歷史演義再到現代白話的現代短篇歷史小說,歷史材料并沒有什么變化,變化的是寫作者對歷史的認知方式,而這種認知方式變化主要是通過敘述方式的變化表現出來的,而語體的選擇又是敘述方式中最顯著的特點。從上面的比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歷代正史中的封建意志和文言書寫方式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書寫者們正是利用文言的特殊地位很好地實現了歷代帝王的統治話語權力;而傳統長篇歷史演義對敘事語言所作的口語化的調整,使歷史獲得了娛樂性,有迎合中下層老百姓趣味的傾向,但封建文人的正統儒家觀念使他們選擇了對正史觀念的固守,半文半白的語體運用只是獲取讀者的手段,并不代表著思想觀念的轉變;現代短篇歷史小說所使用的現代白話卻既是思想的又是藝術的,它既表示了創作者們在新思想的影響下重新打量歷史的一種姿態,同時也賦予歷史文本另一種藝術詮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書寫是和歷史認知、語體選擇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研究歷史認知必須從語言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