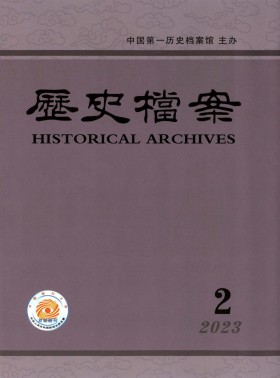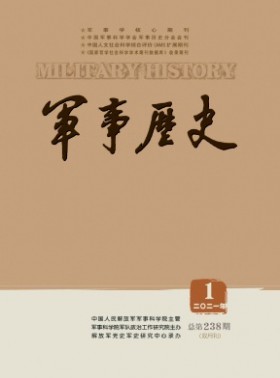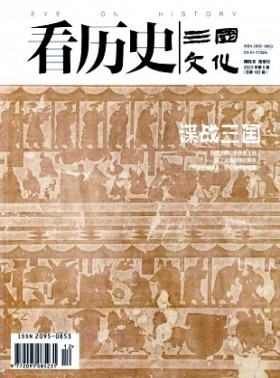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歷史文學多層次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童慶炳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歷史文學創作的發展與繁榮,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奇葩,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和觀眾,也引起了爭議。史學家常常指責和批評當前歷史劇、歷史電視連續劇、歷史小說沒有寫出歷史的原貌,違背歷史真實;文學批評家中多數人則認為歷史文學家有權力虛構,不必復制歷史原貌,況且何處去找歷史的原貌呢?就是被魯迅稱贊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測性的虛構嗎?“鴻門宴”上那些言談和動作,離《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少說也有六七十年了,他自己并未親睹那個場面,他根據什么寫出來的呢?他的《史記》難道不是他構造的一個“文本”嗎?另外,現實生活無限豐富多彩,無限生動活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從中尋找到無限的詩性,尋找到無限的戲劇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現實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卻對現實生活似乎視而不見,總是扭過頭去對那過去的歷史情有獨鐘,愿意去寫歷史,愿意去重建藝術的歷史世界呢?這里就關系到一個作家重建歷史文本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的問題。還有,人們需要歷史文學難道僅僅是因為需要它為現實提供一面鏡子嗎?或者說歷史的教訓可以古為今用?對于歷史文學來說,還有沒有更為深層的東西?我發現上面所提的問題,恰好就是歷史文學作品由表及里的三個層面。對這三個層面進行必要的探索也許能揭示歷史文學所面對的一些難題。
重建歷史世界
我在重讀了郭沫若的歷史劇之后,深感歷史文學應老老實實地定位為“文學”,而不能定位為“歷史”。為什么這樣說?歷史文學家生活在現在,可他寫的卻是數十年、數百年、數千年前的歷史故事。他的根據是什么?就是歷史文本(史書)。問題是這歷史文本能不能反映歷史的原貌呢?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不可能的。第一,歷史上發生的真實情景已過去了很長時間,他無法親眼去看去聽,更無法親身去經歷、去體驗,他所根據的仍然是前代史官和民間傳說留下的點滴的并不系統的文本。這些前代史官所寫的文本和民間傳說文本,也不是作者的親見親聞親歷,他們所提供的也只是他們自認為真實的文本而已。無論是前代的資料,后人寫的歷史,都只是“歷史是文本”,而不是歷史本身,它只是后人對那段歷史文本的闡釋而已。第二,既然是對前人文本的歷史闡釋,當然也就滲透進闡釋者本人的觀點。對一段歷史,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更不用說,史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秉筆直書”、“按實而書”,這里又有一個避諱問題,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是情之難免。
所以史劇作家所依據的歷史文本就存在一個真假難辨、有無難分的問題。這里的問題是,歷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實敘事,但如果歷史文學家不借助歷史文本的話,那么就無所依憑,創作也就無從談起。這是一個悖論,歷史文本不完全真實,可不借助歷史文本創作就沒有根據。那么歷史文學家是如何來解開這個悖論的呢?換句話說,歷史文學的創造者是如何來構筑他的作品結構框架的呢?在重讀了郭沫若的歷史劇之后,我想到了一個詞,這個詞就是“重建”。我的意思是歷史文學的創作者構筑藝術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虛構,也非完全的復制,而是根據歷史文本的“一鱗半爪”,尋找歷史根據,以藝術想象重新建立“歷史世界”。藝術重建就是另起爐灶,對歷史文本加以增刪,加以改造,不照抄歷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評價歷史中的人物與事件,另辟一個天地,構思成一個完整的世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所寫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371年的戰國時代。史劇的故事是這樣的:當時的晉國還沒有分裂為韓、趙、魏三國,魏國有一位武力高強的青年聶政,他因為小時候殺過人,只好到齊國隱沒在民間,做一個屠狗之夫。他受到韓侯卿相嚴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親去世后,來到了濮陽見了嚴仲子。嚴仲子主張韓趙魏三家不分裂,聯合抗強秦。但他遭遇到當時韓侯的丞相俠累的反對和排斥,他希望聶政能幫助他,把俠累刺殺掉,使國家不致分裂,人民免遭痛苦。聶政認為這是正義的事情,慨然應允。
聶政來到韓城,利用一個機會把俠累刺殺掉了之后,他自己也自殺了。但在自殺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容貌毀掉,使韓城的人不能把他認出來。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他的姐姐,不連累姐姐,因為他的姐姐聶與他是孿生姐弟,相貌十分相似。但聶知道后,與愛著聶政的姑娘春姑,來到韓城認尸,她們為此也都死在這里,為的是要把聶政的英名宣揚出去,不能讓他白白死去。《棠棣之花》的整個的歷史語境是郭沫若構想的。拿《史記》來對照,嚴仲子與俠累有仇怨是真的,但嚴仲子與俠累的分歧是主張抗秦還是親秦,主張三家分晉還是反對三家分晉,完全是郭沫若的藝術構思的結果,總體的歷史語境是作者重建的。作品中重要的人物酒家母、春姑、盲叟、玉兒,及其整個的人物關系,聶政與姐姐是孿生姐弟等等,都屬于重建歷史世界過程中的合理想象。至于劇中另一個重要的穿針引線的人物韓堅山,《史記》中只字未提到。所以,寫歷史文學不是寫歷史,不必受歷史文本的束縛,可以按照歷史文學家的藝術評價,重新構建出一個歷史世界來,把古代的歷史精神翻譯到現代。然而,如果我們對照司馬遷所寫的《刺客列傳》中聶政的有關段落,那么我們會發現,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憑空虛構,作者的確抓住了歷史文本的“一鱗半爪”:聶政確有其人;他確有一個姐姐;他因為“殺人避仇”而到齊地當屠夫是事實;嚴仲子曾親自去齊國拜訪他,請他出山,他以母在暫不能受命為由沒有同意,這也有記載;母死后他來到濮陽,見嚴仲子,毅然受嚴仲子之托而刺殺了韓相俠累也是真的;甚至他殺了俠累之后自殺前自毀容貌都有文字可尋。
可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創作的確是有歷史文本作為根據的。換句話說,歷史文學又要以歷史文本所提供的事實為基本依托,在歷史框架和時限中重建歷史世界,展現出藝術的風采。所以,我認為歷史文學作品的第一層面是重建歷史世界。所謂“重建”可以大體概括為三點:第一,重建的根據:把握和發揚歷史精神;第二,重建的空間:只需符合歷史框架和歷史時限,不受歷史文本的束縛;第三點,重建的關鍵:藝術世界的完整性。第一點,我將在第二節具體論述,第二點則是常識了,上面已經反復講過了。第三點最為重要,因為歷史文學是文學,文學作品所展現的世界,必須是完整的、自成一個天地的、自構一個系統的。史學家追求的主要是歷史真實,零碎的東西對他們很重要;文學家追求的是藝術,零碎的真實沒有意義,唯有展現整體的世界,才會具有藝術的印記。#p#分頁標題#e#
隱喻現實世界
現實生活無限豐富多彩,無限生動活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從中尋找到無限的詩性,尋找到無限的戲劇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現實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卻對現實生活似乎視而不見,總是扭過頭去對那過去的歷史情有獨鐘,愿意去寫歷史,愿意去重建藝術的歷史世界呢?這里就關系到一個作家重建歷史文本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的問題。這是歷史文學作品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歷史作為一個社會生活的發展過程,常常令人驚異。但經常出現“歷史的重演”。在這“重演”或“重復”中往往蘊涵寶貴的“歷史精神”。什么是歷史精神?我認為就是反映人民的利益、希望、愿望和理想的精神。
人民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精神,才能稱之為“歷史精神”。例如,愛國主義精神、以人為本精神、望合厭分精神、精誠團結精神、天人合一精神、清廉潔凈精神、臨危不懼精神、直面現實精神、改革創新精神等等,都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歷史的發展往往就是這些精神在更高階段上的重演或重復。這樣,歷史精神就往往成為現實的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似乎更能清楚地看清現實的種種問題和可能的演變。因此人們很重視“以史為鑒”,力圖在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中,掌握歷史精神,并以此映照現實,采取措施,使現實不再陷入歷史的死胡同,不再犯前人犯過的錯誤。要知道,我們處在現實生活中,現實與我們離得太近,或利害相關,不得不裝聾作啞,明知故犯;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習焉不察,常常看不清楚現實真相。但是我們看過去的歷史則可以拉開距離,可以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遠方已經起火,那火正在向近處蔓延,危機或災難已經迫近。更重要的是,歷史文學做家還可以把握歷史精神,挖掘歷史精神,重建歷史情境,賦予歷史以新的意義。所以在歷史和歷史文學這面鏡子里,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也更具有美感。
這就是歷史文學家鐘情于歷史的原因吧!也是現代人需要歷史想象的原因,需要把握歷史精神的原因吧!那么,1941年歷史學家的郭沫若寫了歷史劇《棠棣之花》,這是舉起什么樣的鏡子呢?他看到了什么危機呢?郭沫若自己說:“《棠棣之花》是主張集合反對分裂為主題,這不用說是參合了一些主觀的見解進去的。望合厭分是民國以來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國有歷史以來的歷代人的希望。因為這種希望是古今共通的東西,我們可以據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鑒今,所以這種參合我并不感其突兀。”〔1〕原來,《史記》只寫嚴仲子與俠累“有谷卩”。“谷卩”即“隙”,就是仇怨,他們之間有何仇怨,《史記》沒有寫。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則把三家分晉的事情結合進去,這樣就成為了是主張統一還是要搞分裂的斗爭,是聯合抗秦還是單獨親秦的斗爭。郭沫若在1941年寫歷史劇《棠棣之花》,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黑暗時期,就是以要團結反分裂的歷史精神警示人們,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面前,我們應該做出何種選擇。所以《棠棣之花》成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一面鏡子,就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在歷史文學中這種以歷史精神警示現實的功能,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如說“影射”,即以古代的人與事影射當前的人與事。如說“翻譯”,即把古代的精神翻譯到今天來。最為流行且影響最大的說法是“古為今用”,強調“用”,寫古代的人與事似乎只是一個軀殼,對比性地說明現代的一個道理,才是真正的“用”。這樣就把歷史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寓言化。我總覺得這些說法都有一點“急功近利”,在這種思想和說法指導下去寫歷史題材,被寫的歷史變得不重要,而為現實服務才是根本。并且作為歷史的文學作品往往會失之于淺露、直白和機械的生硬的類比。時過境遷,“用”的功能喪失,也很難作為真正的藝術品流傳下去。
因此,對于歷史文學中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我想用“隱喻”這個概念更為恰當。隱喻是一種修辭格,它是指某個言語過程中,此物被轉移到彼物上面。盡管此物與彼物是不同的,但差異中又具有相似點。歷史文學用言語寫歷史上的人與事,這就是“此物”;但這人與事中隱含的歷史精神,通過心理聯想,被轉移到現實,這現實就是“彼物”。《棠棣之花》是一個重建起來完整的歷史世界,但這個世界中的反分裂的歷史精神(彼物)被轉移到抗日戰爭時期的現實(此物)中來了。對于歷史文學作品來說,隱喻也大體可概括為三點:第一,隱喻的根據是現實中的問題,歷史文學不但不回避現實,恰好是要針對現實,沒有現實針對性的隱喻是沒有意義的;第二,隱喻的關鍵是必須要深幽、隱微、曲折、朦朧,讓人覺得作品完全是在寫古人的故事,并且那故事有自己的藝術邏輯,不直白,不淺露,歷史對現實的比較在那里似有似無,似是似不是,似可言又似不可言,直奔主題的隱喻沒有藝術特性,可能成為借古人的服裝演出現代人的戲;第三,隱喻的藝術理想是要為它所構造的藝術世界著色,應更有氛圍,更有情調,更有韻味,更有色澤,因而更具有審美品格,更具有藝術魅力。
暗示哲學意味
人們需要歷史文學難道僅僅是因為需要它來隱喻現實嗎?郭沫若有一個說法,他說:“總結寫歷史劇主要有三點:一是再現歷史的事實,次是以歷史比較現實,再次是歷史的興趣而已。”〔2〕這實際上道出了歷史文學作品的三個層面,“歷史的興趣”就是歷史文學作品的第三層面。“歷史的興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歷史場景往往具有戲劇性,或說得寬一些,就是文學性,如歷史場景那種氛圍、氣息、情調、韻味、色澤等,大體相當于“賦比興”中的“興”。“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是《詩經•周南》中《桃夭》的第一節,意思是說,桃花開得紅艷艷,這個姑娘出嫁了,找到了一個好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是所謂的“興句”,它所描寫的場景似與第二句“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似有關又似無關。說無關,找不到直接的聯系,說有關,似乎是借桃花的風調來烘托姑娘出嫁時候的紅火、熱鬧的氣氛、情調,僅僅一句“之子于歸”是沒有“興趣”的,現在有了前面的句子“桃之夭夭”就有“興趣”了,這“興趣”是通過“興”而獲得的。歷史文學的情形與此相仿。作品中所寫的“歷史的事實”以及“以歷史比較現實”,如果只是機械地生硬地去寫,那是不會有氛圍、氣息、情調、韻味、色澤的,不會有文學性,不會有興趣。必須透過對于歷史場景的藝術的渲染,像依托詩中的“興”那樣,歷史場景才會獲得一種讓人品味不盡的藝術氛圍、氣息、情調、韻味、色澤等,“文學性”、“興趣”才會油然而生。但是我覺得把歷史文學作品的深層僅僅歸結為“歷史的興趣”和“文學性”是不夠的。真正的歷史文學作品應該通過歷史場景的描寫延伸到人生“哲學意味”的呈現。“哲學意味”這個概念是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提出的。#p#分頁標題#e#
他說:“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3〕這就是說歷史文學作為一種詩性的活動也是哲學活動,同樣可以達到對于人生真諦的揭示。在亞里斯多德以后的大約兩千年,法國作家加繆也說:“文學作品通常是一種難以表達的哲學的結果,是這種哲學的具體圖解和美化修飾。”〔4〕實際上,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提出文學源于“道心神理”,也是講文學的哲學意味,與后來韓愈講的“文以載道”殊異。那么哲學意味是什么呢?“哲學”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意味”則是“形而下”的、感性的,“哲學意味”就是作品中所暗示出來對人生真諦的那種可言不可言、可道不可道的狀態。歷史文學若要達到極致,像其它偉大作品一樣成為不朽的經典,就不能停留在對于歷史的重建上,不能停留在對現實的隱喻上,還必須更上一層樓,要有暗示人生“哲學意味”的效能。那么,一部歷史文學作品是否有“哲學意味”,由誰說了算?是作者自己說了算,還是由讀者說了算?有的作者過于驕傲,常把自己的平庸之作說得天花亂墜。但有的作者則過分謙虛,講自己的作品“過時”了。郭沫若就屬于后面這一類。他的史劇在20世紀50年代初被翻譯成俄語,在蘇聯發行。郭沫若在《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一文中認為,他寫這個劇本是在1942年,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它所針對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他“耽心”這個劇本不一定能受到蘇聯讀者的歡迎,因為它“很快地失掉了象征現時代的那一段意義”。郭沫若的“耽心”是多余的,他的《屈原》不但在當時受到歡迎,就是在今天仍然受到歡迎。在現今的中學和大學的教材里,《屈原》仍然閃耀著它的光芒。郭沫若自己沒有看到他的《屈原》所暗示的“哲學意味”,但讀者發現了,眾多的讀者發現了。
這里且不說常為讀者津津樂道的第五幕的大段的“天問”式的“雷電頌”充滿哲學意味,就整個故事而言,我覺得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險惡和人生的溫暖。劇中人物南后竟然是那樣陰險,在幾秒鐘前還讓屈原興高采烈,覺得他的《九歌》在南后的改編和導演下變得那樣美麗,就要當著眾人的面,特別是當著楚懷王和秦使張儀等人的面演出,可幾秒鐘后在楚懷王等人進來的一瞬間,南后假裝站不穩故意倒在屈原的懷里,誣陷屈原要調戲她。人生的險惡只是頃刻間的事情。你不要認為你一切都很幸運,也許再過幾秒鐘厄運就會降臨。但人生也有溫暖,如郭沫若的朋友徐遲所說的“人間的陽光”。屈原遭南后陷害,以為再也沒有洗清之日,但劇中人物“釣者”,竟然就是目睹屈原遭受南后陷害的證人,他的突然出現,洗清了屈原的不白之冤,這不是人生的溫暖嗎!嬋娟被抓到宮中的牢里,以為必死無疑,但看守她的衛士甲良心發現轉而幫助她脫離險境,這不是人生的溫暖嗎!屈原最后眼看要被毒酒害死,但這酒無意間被嬋娟喝了,嬋娟替他死了,這難道不是人生的溫暖嗎?對于人生,險惡和溫暖并存,這就是《屈原》暗示給我們的難以言說的真諦。它讓我們激動,讓我們沉思。歷史文學中的哲學意味大體上也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這哲學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從生活體驗中提煉出來的,而不是生硬灌輸進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寫哲學講義;第二,這哲學意味是從作品的整體中透露出來的,不是個別細節插入;第三,哲學不同于常識,因此歷史文學中的哲學意味應該是深刻的,它像火種那樣點燃人生的希望,像陽光那樣照亮人生的道路,像魔鏡那樣照耀人的心靈,讓你的靈魂陰暗無所逃遁。歷史文學三個層面:重建———隱喻———哲學意味,由表及里,層層深入。重建完整的歷史世界,才能藝術地隱喻現實;而哲學意味則不是外加的,就在重建、隱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