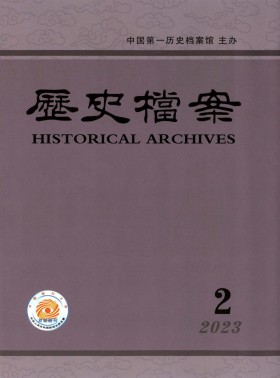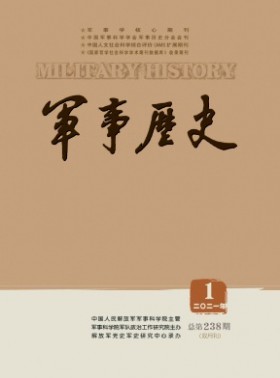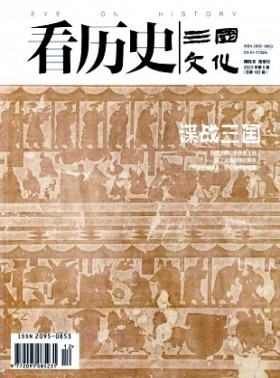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歷史文學理論創建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劉進才 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中國歷來注重修史,正是這種注重修史的觀念帶來了中國史傳文學的發達和繁榮。尤其到明清時代,在長篇章回體小說文類中,且不說《列國志傳》、《西漢通俗演義》、《三國演義》、《兩晉演義》、《隋唐演義》、《南北宋傳》、《皇明中興圣烈傳》等這些“講史類”小說占據了相當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煙粉類”、“諷刺類”、“神魔類”和“俠義類”等小說文類中也滲透著豐富的歷史內容。從《西湖小史》、《繡榻野史》、《金蓮仙史》、《嬋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諸小說題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歷史題材對小說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體察小說作者假借歷史以吸引讀者眼球并提升小說地位的微妙心態。中國傳統的歷史小說主要是演義體歷史小說,作家秉持著補正史之余的創作觀念,通過小說去演義歷史,《三國志通俗演義》小說作者遵照著所謂“七實三虛”的創作原則成為此類小說的典范之作。
這種演義歷史、再現歷史的創作觀念一直占據歷史文學創作的主導。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吳趼人仍然看重歷史小說再現歷史事實的社會價值:“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讀小說而身臨其境”。〔1〕(86)這一論述延續了傳統歷史小說的美學觀念。即使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歷史小說在創作的價值取向上已逐漸擺脫了中國傳統演義體歷史小說補正史之余的陳舊觀念,而理論批評方面卻較多地與傳統相連,批評思路上呈現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歷史小說創作上,史實與虛構之間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義體歷史小說批評家早已討論的話題。事實上,中國歷史文學創作盡管源遠流長,但在理論方面的探討卻非常有限,無論是金圣嘆“以文運事”和“因文生事”的論述,還是毛宗崗對歷史小說“據實指陳,非屬臆造”的強調;無論是謝肇制對《三國演義》“事太實則近腐”的批評,還是袁于令對歷史小說“傳奇貴幻”的提倡;以及李漁的“虛則虛到底”、“實則實到底”和金豐“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寫作原則的確立,都是想在歷史小說創作的虛實之間尋找一種理想的平衡。現代歷史小說批評家同樣在這一問題上徘徊與沉迷。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正是過多地糾纏于“虛實之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歷史小說理論的其他層面作深入細致的探討,致使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始終在傳統的陰影下徘徊游移,難以產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論體系。那么,當代的情況又如何呢?進入新時期以來,思想運動催發了歷史小說創作的空前繁榮。
僅1976-1981年間,公開發表和出版的中長篇歷史小說就達四十多部,短篇歷史小說在百篇以上。不但題材廣闊,內容豐富,數量上也遠遠超越了新文學前60年的總和。然而相對于創作的豐富和繁榮,歷史小說的評論和研究工作卻顯得相當滯后。即便是有些評論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體的作品,停留在介紹性、讀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論深度和深厚的歷史素養,沒有把歷史小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對之進行綜合考察和專門研究。正是在歷史小說研究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學術背景下,吳秀明在教學實踐中,以他所擁有的強大純正的藝術鑒賞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銳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熱忱的擁抱現實的激情,走進了歷史小說研究的領地。如果從他1981年在《文藝報》刊發的《虛構應當尊重歷史———歷史小說真實性問題探討》一文開始算起,吳秀明至今在歷史文學研究的園地中已經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尋常,吳秀明在這個屬于“自己的園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創獲頗豐,為學術界貢獻了一系列關于歷史文學研究的論著,總結并建構了歷史文學的創作原則和理論體系。自此,中國歷史文學研究終于超越了此前那種感悟評點似的評介和研究,有了屬于自己的宏富而嚴謹的理論體系。縱觀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的30年歷程,按照他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的演進、深化與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文學批評與文本解讀
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歷史小說創作較之普通的小說創作要困難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嘆:“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更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又難。”〔1〕(145)套用這一說法,我認為,作文學評論難,作歷史小說評論更難,作歷史小說評論能夠論述透辟,評論得當,視野宏闊,尤難之又難。對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幾年來,出現了幾部寫歷史的小說。我看了幾篇評論文章,都寫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讓人同意。為什么呢?因為寫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歷史,或者不熟悉小說藝術,歷史小說中錯誤地虛構歷史,評論者不僅沒有指出這些描寫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這原因可能就在于評論者自己也不曉得不認識這些描寫不符合歷史生活。”〔2〕歷史小說是歷史科學與小說藝術的有機融合,這種特有的藝術品性要求評論者不但要具有小說藝術的審美體悟能力,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素養。正如歷史小說作者在進行歷史小說創作時必須要熟悉所反映的這段歷史一樣,歷史小說評論者也應該對其評論對象所反映的這段歷史要了解。
面對歷史小說評論這一難題,吳秀明卻不畏艱難,知難而進。80年代初,作為一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教學的大學教師,吳秀明的文學素養、文學鑒賞和見微知著的文學評論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對歷史文學文本,作為一個歷史文學評論者如何過歷史關卻是一個極富挑戰又具有誘惑性的研究難題。那么,吳秀明是如何度過這一歷史關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為我們透露出他為此的付出和艱辛:“我是根據寫評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書。比如在寫到唐玄宗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唐玄宗這方面的史料,在寫到捻軍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捻軍這方面的史料。”〔3〕(365)他為了弄清楚劉亞洲長篇歷史小說《陳勝》所寫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觀看人獸相斗的殘酷娛樂表演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不但請教精通這段歷史的專家,還先后查閱了《史記》、《漢書》、《秦會要》、《太平御覽》等大量的歷史文獻乃至稗官野史、筆記小說。評論中有關此事失真的文字雖寥寥幾行,卻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正是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韌和執著,吳秀明把文本閱讀與文獻查詢相比照,徜徉于歷史與小說之間,在歷史小說評論這塊比較貧瘠而荊棘叢生的園地里堅持耕耘,開始走出了一條屬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p#分頁標題#e#
80年代初的歷史小說研究,吳秀明密切關注當下的歷史小說文本,對于新作給予及時的研究與評論,盡管有一些如《評1976至1981年的歷史小說創作》、《虛構應當尊重歷史》等綜述性和專題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作品的評論上,遵循的是文學批評與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徑。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文學文本,而文本細讀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基礎。吳秀明1987年結集出版的《在歷史與小說之間》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歷史小說長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評。他評論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論作品,其間往往以一部作品為例,生發出對于歷史文學許多重大關節問題的思考,滲透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通讀這些飽含著富有學術激情與問題意識的評論文章,可強烈感受到評論者的史思與詩思的相互輝映以及辨證的思維方式的縝密展演。比如在論及俆興亞的《金甌缺》通過展現生活場景風俗畫的細節營造小說的真實性時,吳秀明既肯定了小說作者對生活觀察的細密與處理題材平中見奇的本領,同時又筆鋒一轉:“不過,小說畢竟屬于藝術的范疇,而不是斷代的風俗志,因而對一個作者來說,光有世態習俗的描寫還是不夠的。風俗畢竟還只是‘外景’,哪怕寫得再逼真,也只能為作品提供一個好的背景或環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只有深入到社會關系的內部,深入到時代風云中去,準確有效地寫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
這種珍貴的辨證思考在他的評論中隨處可見,這樣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歷久彌新,得出的結論令人嘆服。辨證的思考方式是一個優秀評論家應該具備的思維品格,在此觀照下,不僅能夠對于一部歷史文學作品品評其優長,好處說好;也能夠體察出其不足,引領作家在創作中揚長補短。在評論楊書案的歷史長篇中,吳秀明能夠深入作品的肌理,指出作品所蘊含的濃濃詩意,并沒有單方面褒揚作家的這一優長,而是誠懇地指出小說“有些地方抒情太多,失去自我控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筆下人物形象的鮮明性和生動性,而且也使他作品的情節發展顯得拖沓緩慢。”〔3〕(231)當然,辯證的思維方式和良好的歷史素養只是吳秀明文學批評在“史思”方面的體現,他在文學批評和文本闡釋中也呈現出聰穎敏捷的審美判斷能力,充溢著強烈的批評激情。如對于《天國恨》剛健豪放格調的概括,指出作品“大筆淋漓,粗毫疏落,作干脆利索的粗線條勾畫,有些地方甚至還帶有歷史素材本身的毛糙樣子,仿佛是取自歷史礦床的渾金璞玉,不是打磨得精巧玲瓏的翡翠古玩”。〔3〕(267)
用這樣鮮活靈動的筆觸品評作品,語言如鮮花帶露,清新可感。沒有從邏輯到邏輯,從推理到推理的枯燥與繁瑣,而是面對一部充滿油墨香味的新作做洞幽燭微的直覺和感悟,這充分體現了吳秀明文學批評的“詩思”品格。與“詩思”緊密相連的是評論中主體情愫的投入。他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去擁抱體悟作品,寫到《秦娥憶》所描寫的“焚書坑儒”的慘烈場面時,吳秀明寫道:“嗟乎,慘無人道的屠戮!哀哉,炎黃文明的浩劫!在中國歷史上,還有比這更殘忍、苛烈的么?!這樣做的結果,豈止是焚燒了一大批詩書簡冊,腰斬了四百多個儒生,活埋了七百多個學士,不,這是在棄圣絕智,強鉗百家之口”。〔3〕(228)盡管他這一時期的歷史小說研究主要集中于具體作品的評論,但“史思”與“詩思”的有機結合使吳秀明的歷史小說研究沒有陷入就事論事的狹小格局,而是在問題意識的映照下獲得了一種廣闊的文學史視野。《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收入了他這之前刊發的單篇文章,許多文章通過評論不同的歷史小說,探討了他對歷史小說理論的初步思考,吳秀明在《關于歷史小說真實性問題的通信———致楊書案同志》、《一部很難組織的“教授小說”———談〈金甌缺〉的真實性》、《“七實三虛”寫風云———關于〈天國恨〉的真實性》、《虛構應當尊重歷史———關于歷史小說真實性問題探討》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探討了歷史小說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核心問題———歷史小說的真實性問題,這些思考是理論生長的萌芽,為以后歷史文學真實論的系統考察打下了堅實的根基,是進一步建構歷史小說理論大廈的基石。
二、理性思辨與理論建構
然而,不管上述文學批評多么富有魅力、不乏新見,它畢竟帶有直覺和感悟的印象批評的成分,離純粹的理論建構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如果文學研究僅僅停留于緊跟新作而展開的作品論層次的分析,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提升將會受到限制。正如孫武臣所指出的,吳秀明早期的有些評論文字“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論闡發和概括,往往顯得濃度不足”,“有幾篇文章寫法上有某些雷同”。如何豐富自我的知識結構、不斷突破自我、超越自我業已形成的學術研究框架,是所有學人都應該積極思考和面對的。好在吳秀明自己也有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深切感受:“寫著寫著,無形之中就有了個程式,題材啦,人物啦,藝術特色啦,最后帶一下缺點,如此這般,大同小異。”〔3〕(364)
就在他的第一部歷史小說研究集《在歷史與小說之間》出版之后,他開始了歷史文學理論的富有拓荒性的探討工作,試圖把歷史文學當做一種獨特的學科形態、系統整體地研究它的個性特征和基本理論體系。從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轉向歷史文學理論的總結與建構不但是吳秀明出于學術自我超越的考慮,也是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與歷史文學自身的蓬勃發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以及“百花齊放”、“古為今用”的文藝方針的強調,新時期歷史文學的興起成為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一個令人矚目的文學現象。與蔚為壯觀的這股創作潮流相比,歷史文學研究在理論上還遠遠不夠深入。從事歷史文學創作的作家也熱切期待能有與這一特殊文體形態相適應的理論著作的出現。吳秀明20世紀90年代初相繼出版的《文學中的歷史世界———歷史文學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歷史的詩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真實的構造———歷史文學真實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三部理論專著,正是呼應了歷史時代與文學自身的內在要求。自此,中國歷史文學研究初步具備了較為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p#分頁標題#e#
如果說吳秀明80年代初步入歷史小說評論要過歷史關這一難題,那么90年代之后的歷史文學理論的建構要突破重重的理論關這一更大的學術難題。我們知道,80年代中后期是學術界“方法熱”風起云涌之際,系統論、敘事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接受美學、闡釋學、結構主義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新理論“亂迷人眼”。在這種新方法炙手可熱之際,吳秀明并沒有急切地套用一種新方法去解讀某一部具體的作品,而是沉潛下來,正如他所言“有意識壓制自己的發表欲,而頗讀了一些美學、文化學、心理學、敘事學以及新方法論等方面的書”。〔4〕經過多年沉潛涵詠的閱讀和思考,吳秀明在歷史文學研究中終于達到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思辨的質的飛躍。縱觀這一時期的三部歷史文學的理論專著,論述問題雖各有側重,但不同問題又相互比照,相互闡發,相互補充,從而相得益彰,共同建構了歷史文學精深而完備的理論體系。從學術史意義上觀之,我認為吳秀明對于歷史文學理論的建構具有以下研究特色和學術個性。首先是理論的系統完整性和創新性。中國歷史文學盡管發達,但歷史文學理論則相對滯后。在古代往往存在于歷史小說的序跋或靈光一閃的評點中,即使有真知灼見也大多只言片語。到了現當代歷史文學創作中,魯迅、郁達夫、郭沫若、茅盾等不但創作了大量的歷史文學,也都對歷史文學范疇和理論做過富有意義的探求,也大多散見于單篇文章,鮮有像外國盧卡契的《歷史小說》、菊池寬的《歷史小說論》等系統的論著出現。吳秀明則圍繞歷史文學的諸多理論問題,比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歷史真實與創造主體、歷史真實與時代社會、歷史真實與讀者接受、歷史真實與虛構限度、歷史小說的現代化傾向、影射問題等等,撰寫了一大批富有洞見的文章,將歷史小說相關的理論問題,特別是不可回避的相關理論難點問題,都作了深入系統和富有成效的探究,把歷史文學的真實論、價值論、形式論相互融通,逐步形成了一套立體完整的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是歷史小說理論研究領域中富有個性的“這一個”。
吳秀明對歷史文學理論建構的系統完整性不僅表現在對于歷史文學諸多問題的探討,更表現在他對一個問題能夠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開掘和剝繭抽絲似的條分縷析。比如他的《真實的構造》,就是對古今中外歷史文學研究難以回避而又常常糾纏不清的“歷史真實”問題進行的專題性探討。我們都知道,真實性問題是歷史文學研究中所有一切理論問題的關鍵與核心,中外古今的文學家、美學家以及歷史哲學家都對這一問題作了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討論。而在過去相當一段時期內,每每觸及到歷史文學的真實問題,大多止于“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單向度的反映論的探究,要么把歷史文學的真實與一般文學的真實性結合起來,要么用歷史科學的標準來衡量歷史文學,這樣一來,歷史文學真實理論的研究實際上簡化成了解釋文藝與生活、歷史事實與藝術虛構的關系問題。
《真實的構造》則在此基礎上,利用系統論的觀念,把歷史文學真實看作是一個立體多維、涵蓋著映像性真實(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主體性真實(歷史真實與作家主體)、當代性真實(歷史真實與當代需要)、認同性真實(文本真實與讀者接受)等四個真實要素的系統耦合而成,將真實納入一個“作品-作家-社會(當下)-歷史-讀者”等多維互動共生的審美機制中進行全方位、立體性觀照。這樣的理論構架很顯然是一個跨學科的系統理論創新工程,他在運用傳統的社會學、文藝美學、歷史哲學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又廣泛借鑒了心理學、發生認識論、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新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的是,論著并非只是摭拾前人提出的新概念、新術語,而是在吸納了各種理論精髓的基礎上經過自我理性的思辨而有所創獲。在強調各種新思潮、新方法、新理論對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理論體系創新所做的貢獻時,我們不要忘記這種理論的創新更來自于他多年的史料積累和長期獨立的文獻準備。80年代初,吳秀明在大量閱讀歷史文學作品和評論的基礎上,曾相繼選編出版了《短篇歷史小說選》、《中篇歷史小說選》以及《歷史小說評論選》,曾專門作過“建國35年來(1949-1984)歷史小說書目輯覽”。不要小覷這費力費神的史料積累,正是這種獨立的文獻準備造就了他歷史文學理論研究的豐厚資源和堅實根基。其次是理論的現實針對性和視野廣闊性。
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和理論建構其背后的動力來源于強烈的問題意識的激發。他所提出的問題不是關在書齋里個人一相情愿的向壁虛構和主觀玄想,而是來自于異彩紛呈的歷史文學創作實踐,從大量的文學創作想象中思考總結得來的。他勤敏善思、獨立不依的學術個性使他長期密切關注當代歷史文學創作實踐和理論探討中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許多學術問題糾結在他的胸中,對此的思考也是一以貫之。比如《文學中的歷史世界》一書中專章探討了不同歷史文學的藝術表現與創作方法的關系,這關涉到作家的歷史文學觀問題,并由此展開現實主義歷史文學觀、浪漫主義歷史文學觀以及現代主義歷史文學觀的多方考察。事實上,這一思考淵源有自。早在1983年評論《金甌缺》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經提出了“在如何求得歷史真實的問題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區分”問題。此外,《文學中的歷史世界》探討了歷史文學的翻案問題。200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中仍在進一步探討與深化。此外,論著對影射問題、現代化問題以及作家虛構的自由與限度和如何深入歷史問題等,都有深入論述。他的理論來源于文學實踐,相應地也會指導文學創作實踐,只有這樣的理論才會煥發出持久的生命活力。《歷史的詩學》正是這種實踐性與現實針對性的集中體現,論著專列“實踐篇”一編,通過對歷史文學藝術實踐的總體描述和抽樣分析,對于藝術實踐的有關問題作了新解。在論述某一具體問題時,吳秀明往往貫通古今,融匯中外,跨越文史哲,因而顯得視野開闊,舒卷自如。
三、文化闡釋與空間拓展
經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學術沉潛和歷史文學的理論自覺建構階段,吳秀明的學術視野逐漸擴大,研究重心漸漸轉移到當代文學思潮、當代文學史寫作以及當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也興趣盎然地旁及教育學、生態文學、地域文學研究等領域,開始主動走出了歷史文學研究這片自己獨立開墾的學術根據地。此后,他在新開墾的學術領地相繼收獲出版了《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等學術成果。盡管歷史小說研究此時已不再占據主導,但吳秀明并沒有忘懷這塊屬于自己的園地,而是在成功申報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期長篇歷史題材小說研究》、《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創作實踐與歷史觀問題的綜合考察》的基礎上,展開了他歷史小說研究的再次突破和飛躍。十年磨一劍,200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正是這一階段的標志性成果。正如吳秀明所言,建立自身的學術根據地是一位學者在學術界安身立命之本,有沒有這個根據地是判斷一個學者有沒有形成自己的學術個性的標準。吳秀明在歷史文學研究領域早已建立了自己堅實牢固的學術根據地。按照常人的一般想法,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根據地里輕車熟路地走下去。相反,他卻主動走出了自己的根據地,走進了更為宏闊的文學史圖景中。正是這一學術研究的拓展與主動出擊,給他的歷史文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質。既然文學史研究可以放在一個廣闊的文化生態場域中加以觀照,歷史小說不也是特定文化場域的產物么?他正是帶著這樣的文化視野再次回到自己難以割舍、常常眷顧的學術熱土。在我看來,這一研究論題的回歸形成了與他之前的歷史文學研究不同的范式。#p#分頁標題#e#
首先是文化闡釋與文本研究的統一。80年代初的歷史小說評論,主要從小說題材選擇、人物形象、思想主題、情感取向、敘述結構、語言表達等諸方面而展開的文本內部的解讀,而《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則注重對小說文本和創作想象進行了深層歷史文化內涵的發掘,將歷史小說看做是一定時期文化現象和文化符號的載體,把歷史小說置于特定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復雜歷史場域和社會語境中加以考量,這樣就跳出了一般文本細讀所遵循的審美自律的狹小格局,拓寬了文學研究的內涵,這使他的歷史文學研究顯得大氣磅礴、視野宏闊。本書第二章選取姚雪垠、凌力、蘇童這三位作家,透視中國當代歷史小說的總體風格與內在結構,認為三位作家分別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他們的歷史小說創作依次采取了階級斗爭范式、人文主義立場和新歷史主義原則,這種以點代面、舉重若輕的研究理路顯示出吳秀明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高屋建瓴、胸有全局的整體把握能力。就青年作家所秉持的新歷史主義原則和呈露的叛逆姿態而言,吳秀明指出:“這些新歷史主義小說普遍顯露了濃重的存在主義傾向,在觀念形態上已由80年代的理性主義進化論向現在的存在論、生命本體論轉化。”〔5〕在此,吳秀明有意凸顯了形成并制約每代作家不同藝術風格的政治歷史語境和文化生態環境。本書第三章的論述更顯得氣勢恢宏,論著把當代中國的歷史敘事置于全球意識的宏大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認為《雍正皇帝》“落霞系列”、《張居正》、《白門柳》、《曾國藩》等歷史小說反映了封建末世之際中國傳統文化在異族文化或西方文化沖擊下的被迫轉型,找到了與當下全球化浪潮所激發起來的民族身份認同的契合點。這就把歷史文學的興起看作是與文化思潮相激相蕩的結果,不再視為僅僅是文學內部的事情。這種文化視野的闡釋和解讀在該書中俯拾即是。在“歷史守成主義敘事”一章中,吳秀明把唐浩明的長篇歷史巨著《曾國藩》、《曠代逸才》和《張之洞》與20世紀90年代后期興起的文化保守主義(如國學熱、新儒學)思潮聯系起來,指出了這些歷史小說所取得的對古人能達成體諒與理解的歷史同情這一成就,也辯證地指出小說作者這種認同性的體諒和理解往往潛在地支持了傳統的權力智慧所導致的專制欲,從而模糊削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
該書所采用的文化闡釋視角并非是大而無當與文學本體毫無關聯的純粹外部研究,因為所有的文化語境都必須通過作家這一中介,內化為作家的精神氣質和心理結構,再通過作品呈現出來。而作品文化視角的闡釋也必須建立在文本研讀的基礎上。“明清敘事與文化重建”一章,通過對反映官場文化、宮廷文化、政治斗爭的歷史小說的解讀,表達了對權力敘事的隱憂。并從藝術創作和讀者接受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權力角逐所蘊含的豐富動人的敘事資源和獨到魅力,這就把看似宏觀的權力話語落實到具體而微的作品的審美中,從而達到了宏觀的文化闡釋與微觀的文本研究相結合,把文學的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相互融通。其次是現代性視角與批判性立場的統一。本書不但把歷史小說放在文化的語境中加以闡釋,而且在評判歷史小說的創作得失時一直秉承現代性的眼光。運用現代性的目光去考量歷史小說,不但驅逐了人們受線性思維的影響縈繞在頭腦中的對歷史小說懷有偏見的迷霧,而且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完善地理解和把握現代性的本質,在實踐上做好正本清源、趨利去弊的工作,從而豐富和深化歷史文學研究,推動歷史題材創作進一步繁榮,這是本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所在。現代性話語充斥于學界已久,其概念邊界往往模糊不清,吳秀明沒有摭拾照搬西方的現代性概念,而是把歷史小說的現代性看做是與傳統相連,認為作家應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礎上,站在人類認識世界的制高點,用自己的時代精神和意識觀照題材對象,用現代意識和靈性激活歷史。吳秀明把作家是否具備現代意識作為能否達到歷史本質真實的評判標準。
現代性與批判性相連。正是在現代性視角的觀照下,吳秀明清醒地看到新時期長篇歷史小說的不足,因為有些作品的創作思路基本停留于表象歷史現象的直觀反映,沒有沉潛其中進行富有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燭照和深度開掘,甚至有些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思想意識降低到古人的水準上。也正是因為一些作家作品缺乏現代意識的燭照,吳秀明敏銳地指出權力敘事所隱藏的陷阱,批判了作者情感上流露出的對權力運作的欣賞,將權力的敘事與權力的認同混為一談的錯誤傾向。這一現代性視角不但把歷史文學創作視作“一部蘊涵豐富的跨世紀文化啟示錄”,是“再造中華文明”、接續民族文化血脈的媒介,而且對于學術研究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本土性和現代性之間尋求自我的理論基點,真正達到文化對接與理論對話,也富有啟示意義。吳秀明的歷史小說研究30年來跨越了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可替代的學術貢獻,當然也各自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這種超越自我、不斷精進的學術研究理路不但對歷史文學研究作出了自己獨特的學術貢獻,也為當下的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學術啟示。一個研究者如何建立屬于自己的學術根據地,又如何走出和超越這一根據地,這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認真思索。當然,吳秀明并沒有停下他對歷史文學研究的腳步,他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歷史文學生產體制、創作實踐與歷史觀問題的綜合考察》已交付出版社待出,我們熱切地期望這部論著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