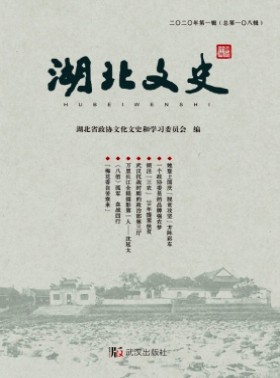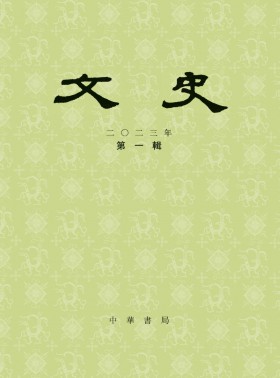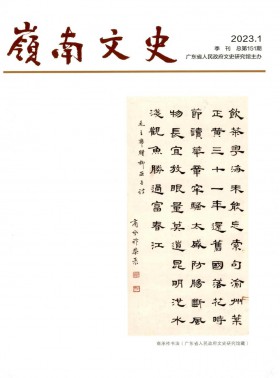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史通文史關系析論,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史通》中的文史關系矛盾,文學研究者和史學研究者都會注意到它。從先秦的文史不分到漢魏六朝的文史獨立,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演進過程,對于歷史中懷著不同稟賦的個體來說,亦會在其身上留下烙印。史學時代而具文才,文學時代而具史才,若才餒即喑啞其聲,若才盛即發為抗辭。作為文學時代的史學家,劉知幾以駢偶之文掎摭新史舊史,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現出文學的歷史觀;又以史律文,表現出歷史的文學觀。
一、從“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劉知幾認識到了個體稟賦與學術演進的關系,他在《核才》篇描述了文史之間從合到分這一歷史過程: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1](P250)孔子所言之“史”本為文辭繁多之義,而劉知幾徑以其為歷史撰述,并藉此談論上古時代文史密不可分的關系。又如:“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1](P180)“‘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1](P528)這一時代的“文”具有和“史”一樣的功能,可以勸善懲惡,所以劉知幾說: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1](P123)劉氏強調當時“文之與史,其流一焉”,是由于“周詩”、“楚賦”皆如《春秋》一樣可進行道德批評。屈平、宋玉“可以方駕南、董”,不是因為其藻采,而是因為他們“不虛美”、“不隱惡”。漢魏以降,文史殊途,各自從經學中獨立而出,在六朝都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但這一時代“文”愈來愈趨于駢儷雕飾,悖離了文史合一時代“文”的本義。若仍令文人修史,必然會“虛加練飾,輕事雕彩”、“體兼賦頌,詞類俳優”,造成“文非文、史非史”的弊端。[1](P180)《核才》篇所言“賦述《兩都》”者為班固,“詩裁《八詠》”者為沈約,像二人那樣能文能史者,在文史異轍的時代,畢竟難覓其才。人之才能各有所偏,長于文者為文,長于史者修史,陳力就列,方可成事。若陳壽,雖有良史之才,卻乏篇什之美,便應令其修史。反之,有文才而“不閑于史”者則不當修史。如《核才》篇論徐陵:“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1](P250)劉知幾致慨于“沮誦失路、靈均當軸”,[1](P250反復言文人不可修史,乃激于初唐史局皆文詠之士。“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肇興,文筆難行史筆之任,文史不能不分途而立。依知幾之見,才堪撰述者當學綜文史,但此“文”非六朝、初唐之文,而是孔子、左丘明之文,是司馬遷、班固之文。文史合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怎能仍以文章之士兼修史傳?劉知幾一面迥立于風尚之外,贊許“五經”、“三史”之文;一面又難免時代文風之濡染,以駢文論史。《史通》中的文史關系問題具有其特有的歷史基礎,必須在初唐文風演進的過程中加以揭示。
二、從貞觀到開元:史家在文學時代
劉知幾(661—721)身歷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太宗貞觀治世對他而言已是文籍中的歷史記憶。但作為一個評騭諸史的史家,他對貞觀修史并不陌生。劉知幾時代的文風與貞觀文風雖然有異,然追溯其制度根源,還應從武德四年(621)李世民開文館談起。當時在選中的十八學士,貞觀修史時,又多以文臣兼為史臣。武德九年九月(626),李世民即位,又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秦王文館及弘文館的設立,預示了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亦開啟了初唐文史之學交互影響的局面。貞觀三年(629),太宗命令狐德棻、李百藥、姚思廉、魏征、房玄齡等重修五代史。太宗以為史籍載文當刊浮華而取切直,是年三月,“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2](P6063-6064)后來,劉知幾的見解與之遙相呼應: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后《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若司馬相如之“文”,于“史”無用,當摒棄于外。至于何者可載入史冊,太宗以為是“詞理切直”之上書,劉氏則以為是“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之文,如《尚書》中的“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中的“大隧、狐裘之什”,[1](P124)因為它們正具有其贊許的文史合一之時“文”的特征。太宗對浮華文風的態度,在史臣中得到了更為有的放矢的回聲。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撰者在序、論中把矛頭紛紛指向梁陳宮體,如魏征《隋書》序及《梁書》、《陳書》、《北齊書》總論,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等。由此,貞觀修史對“文”的態度似乎當贏得劉知幾之稱許了。遺憾的是,此態度并未一以貫之,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等修《晉書》成,“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3](P2463)所以,劉知幾明確指出其以文為史之弊: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1](P82)從初始對質直雅正的追求,到重蹈淫靡綺艷之舊轍,都有太宗的影響存在。他是貞觀宮廷文臣的核心,“文勝質”抑或“質勝文”,帝王的趨避帶來的是上行下效。太宗雖曾反對駢儷文風,但在《晉書》中還是揮翰濡墨,自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編字不只,捶句皆雙,體現出史學處于文學籠罩之下的境遇。太宗雖躬為駢儷綺艷之辭,在主張上還是肯定文質相諧的文風。但到了武則天為政時期,則徹底主張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之文,使太宗朝向雅化的努力前功盡棄。這一文風變革從唐高宗龍朔元年(661)開始,①而劉知幾正是在此年降生于世。楊炯論當時文風遷移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4](P69)文學發展中的這段歷史,被描述為初唐四杰及陳子昂反抗的對象,他們以復古求新變,希望掙脫南朝之習,回到漢魏去。這一變革被反復渲染,甚至夸大了陳子昂的實際影響。而比陳子昂年輕兩歲的劉知幾,更為激烈地批評南朝文風,希望回到更遠的孔子、左丘明時代,則很少與前者相提并論。這只是因為文史異轍罷了。其實,史家對文的批評,在文風過度淪溺的初唐時期,具有特別的警醒意義。高宗永隆元年(680),劉知幾以弱冠之年射策登朝。次年,②高宗頒詔云:“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5](P161)可見其時經史之學的淪落,即令嗜史若知幾者,猶言“專心諸史,我則未暇”。[1](P289)但比起時流而言,劉知幾決無“進士不尋史傳”之病,他能在指責六朝文風時,以孔子、左丘明之文作為批評的準則。而同樣是不滿六朝文風,陳子昂只是追慕文學自覺的漢魏時代。這便是史家與文人的不同。武則天稱帝后,淫麗之文更盛。陳子昂明確提倡漢魏風骨,抨擊“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他贊嘆東方虬之詩,曰“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6](P896)可見其對建安、正始文風的推崇。比較起來,劉知幾對建安、正始文學便不那么尊重了。#p#分頁標題#e#
如其以史家眼光苛責曹植《洛神賦》:“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1](P521)此為假設之辭,言史籍不宜載非實錄之文。又如其論阮籍,曰“嗣宗沈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1](P326)劉知幾以史學家論曹植之賦、以道學家論阮籍之人固然可議,但他從文史不分的先秦時代(而非文史異轍的建安、正始)追尋文質彬彬的傳統,則是陳子昂所不及的。陳子昂之論止于詩賦,劉知幾則推溯至古文。劉知幾作為三入館閣的史臣,不僅是武后、中宗時期文風的旁觀者,更是直接的參與者。他曾先后為武后朝珠英學士和中宗朝景龍學士,入館閣詩賦唱和之列。武后圣歷二年(699),“以昌宗丑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跡,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3](P2707)知幾是年至京都任右補闕及定王府倉曹,旋即參與其列。長安元年(701)十一月書成,編修其間多游宴賦詩唱和,“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7](P1059)為《珠英學士集》五卷。今敦煌遺書P.3771、S.2717即為《珠英學士集》殘卷,其中S.2717有署作“右補闕彭城劉知幾”詩三首:《次河神廟虞參軍船先發余阻風不進寒夜旅泊》、《讀〈漢書〉作》、《詠史》,融史意于文心,風格與李嶠、宋之問等長于詠物應制者皆異。中宗景龍二年(708),劉知幾致蕭至忠書,求罷史職。去職后五日,復為修文館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8](P5748)劉氏悵恨于史官尸位素餐,憤而離職,輾轉卻又從行于文人狎客之間,生計艱辛,文場史林皆非凈土,而又不得不寄身其中。玄宗開元九年(721),《史通》成書11年后,劉知幾卒。武后、中宗朝文士,如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等,至此也已凋零向盡。史家劉知幾的一生見證了這段宮廷文學的發展歷程。正是游身于文館史館的經歷,才使劉知幾游刃于文史之間,以文衡史,以史律文,在《史通》中顯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三、以文衡史與以史律文
(一)以文衡史
劉知幾自敘云:“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1](P292)他雖然像揚雄一樣悔其少作,但其少年時期的文學修養還是滲透在其史學批評中。他發展了《文心雕龍》以駢文說理論事的傳統,以恣肆快意之氣驅遣凝重板滯之文,踔厲駿發,通脫暢達,語言朗朗可誦。更重要的是,劉知幾特別強調歷史中的敘事因素,時時以文衡史,他最推許的史籍《左傳》正是文史相諧的典范。“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與于此乎?”[1](P165)劉知幾在強調實錄即史之真以外,還強調史之美與史之善。歷史懲惡勸善功用的發揮,離不開言辭之美。《敘事》篇集中了劉知幾對言辭之美的理解,認為歷史敘事當尚簡、用晦、去妄飾。三者言可分論而義實相關,如“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1](P173)一句中即涵三義,它們完美地體現在《春秋》、《左傳》(尤其是后者)之中。既而丘明受經,師范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劉知幾對“晦”的解釋是“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1](P173)紀昀以為“即彥和《隱秀》之旨”,[1](P644)陳漢章則以為“然《史通》‘晦’字自本《春秋》‘志而晦’為義,未必祖述彥和”。[1](P644)其實,劉知幾提倡“用晦”在語源上雖本于《春秋》,但與劉勰“隱秀”之說未嘗不可相通。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與劉知幾所言“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不都是言有盡而意無窮之義?文史在“隱”、“晦”之義上渾然相通。史蘊文心,歷史敘事而可以“美句入詠歌”,[1](P451)③“則是史是詩,迷離難別。”[9](P164)劉知幾雖強調歷史敘事,但與近現代西方史家柯林武德、海登•懷特等夸大歷史敘述本身的虛構性并不相同,他是確信歷史之真存在的。但是,既然強調歷史敘事的文學特性,便不免對歷史之真有所犧牲。這一矛盾劉知幾隱約地意識到了。《敘事》篇曰:“《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1](P174)《暗惑》篇曰:“昔《武成》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1](P578)“血流漂杵”諸語乃史家夸飾,孟子已言其非,劉知幾稱其“語實周贍”,為敘事之美者,但亦指出其“文如闊略”,“蓋言之甚也”。劉知幾肯定文辭對史傳的意義,但對史傳中的夸飾與想象,則保持了足夠的警惕,認為這些是以文害史,應該排除在史籍之外。其實,史傳若重文辭,夸飾與想象是少不了的,《史記》之偉大即在此處。劉知幾以文衡史,亦常常以史律文,在史之美與真中難以權衡。
(二)以史律文
呂思勉曰:“劉氏論事,每失之刻核。……將尋常述情達意之語,一一作敘事文看。”[10](P296)又曰:“《漁父》之辭,《高唐》之賦,自非事實;昔賢采此,或亦以人人知為辭賦之流,使人作辭賦觀,非使人作敘事文觀也”。[10](P297)但在這里,劉知幾并未否定辭賦文的價值,只是以為文史異轍,史籍不當載之。他說:“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1](P522)這是以實錄為準則,把寓言、假說溝之于史籍之外。有時,劉知幾會把史的實錄之義無限夸大,以史之真律文之美,煮鶴焚琴,表現出歷史主義的文學觀。《雜說上》篇曰:《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睹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哉?[1](P452)人智不如葵,以人擬物;葵能衛其足,以物擬人。此乃文之宛轉見情致者,劉知幾反坐實其義。一方面,他并不反對《詩經》比興之旨,但又認為比興當取“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非“含靈蓄智”之義,其所謂“實錄”蘊涵著道德批評,對史之真的追求與對史之善的強調糾纏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以為“今俗文士”(即受南朝文風影響者)言花鳥有“啼笑之情”,不合古人雅正之意。針對劉氏以史律文之病,錢鐘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譏之曰:“劉氏未悟‘俗文’濫觴于《三百篇》,非‘今’斯‘今’。④唐太宗《月晦》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又《詠桃》云:‘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劉遽斥‘今俗文士’,無乃如汲黯之戇乎!”[9](P71)即便有左史、右史珥筆備錄,史家在整理史料、撰述史籍時亦需要設身處地,代作喉舌,其中難免文學虛構。劉知幾悟不及此,常以虛為實,穿鑿解之。《史通•暗惑》篇以文史異轍為主題,集中地體現了劉知幾對以文為史的吹毛求疵的態度。如“《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1](P578)不過是黎庶感戴方伯之意,劉知幾三難其事,其三曰“晉陽無竹,古今共知,……群戲而乘,如何克辦”,[1](P579)讀來甚煞風景,然后世學者反斤斤于有竹無竹之辯———“《困學記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1](P580)又如,“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劉知幾引《漢書》“項王叱咤,懾伏千人”為說,以為“文鴛武勇,遠慚項籍”,“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巋然無害也?”[1](P582)誠如張振珮所言:“文士以此夸張之辭,加諸文鴦之身,雖理所必無,亦文所或有也。”[11](P696)劉知幾嚴于文史之別,以致有此不情之論。#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