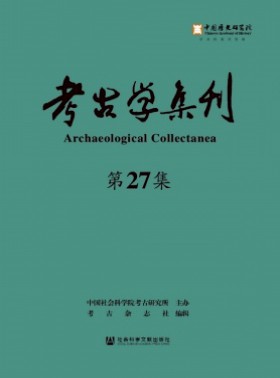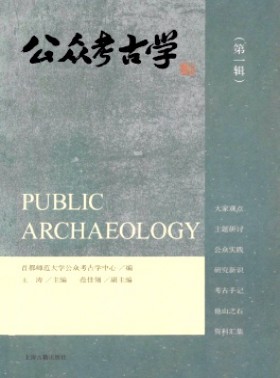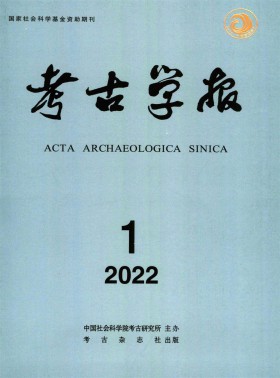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考古學內涵及歷史闡明,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徐承泰 蔣宏杰 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文化特征
(一)器物形態及其組合關系
1.器物形態
(1)南陽豐泰墓地仿銅陶禮器的器形,有一個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演化軌跡;制作工藝,有一個由粗及精,由簡到繁,再到粗而簡的變化過程。器形方面,從戰國晚期到西漢昭宣時期,各器類處在一個同步逐漸變大的上升階段,這一過程在武帝后期及昭宣時期達到頂峰。以鼎的高度為例,西漢早期前段與西漢中期后段最大高差達一倍左右。西漢晚期前段開始,器形開始逐漸變小,東漢以后各類隨葬品已小型化。制作工藝方面,戰國晚期至武帝前期,器物尤其是鼎的色澤多偏黃灰色,火候偏低易碎,質地粗糙,器表裝飾簡單。武帝后期開始,器物一般都呈深灰色,火候略高,器表一般都經打磨,光滑平整。器表裝飾漸趨豐富,而尤以器蓋表面的裝飾極具特色,蓋頂出現鋪首紐、人面紐、四葉紐等紐飾,有的蓋面有堆塑獸紋。西漢晚期后段,鼎、盒、壺均變為博山蓋,蓋面模制各類人物、動物、樹木紋飾,一般都十分清晰。王莽以后,博山蓋蓋面仍為上述模制紋飾,但開始模糊不清,至東漢以后,蓋面紋飾基本上已看不出來了。
(2)南陽豐泰墓地的部分陶器,在形態或裝飾方面的設計上非常具有特點,顯示出漢代南陽地區人們獨特的審美觀念與文化思維。陶鼎從武帝前期開始,鼎足根部施以人面形裝飾。人面飾五官清晰,須眉齊具,整體造型生動逼真,不同時期在細節上加以變化。這一裝飾特點對周邊區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肩上有一道寬凹槽的矮領折沿罐,是一類不見于其它地區的遺物。此類陶罐在豐泰墓地出現的時間是西漢晚期,在南陽計生委墓地的西漢中期偶有發現。其來龍去脈目前都還不能確定,但是非常有特點。器蓋共有三種形態。一種是弧頂蓋,這種器蓋非常普遍地流行于全國各地。第二種是有圈足狀抓手,這類器蓋在早期與各地所見此類器蓋基本相同,并無特殊之處,到西漢中期后段,大致是昭宣時期,開始在蓋頂普遍出現鋪首狀器紐,這種器紐是兩個鋪首相對,鼻部相合形成小蓋紐,鋪首的頭面形成紐座,原來的圈足狀抓手逐漸退化為一道凸棱。此外還可見到人面紐。第三類是博山蓋,這種器蓋的蓋面分上下數周模印有山巒、樹木、人物、動物等形象,其中動物類圖案可辨者有狗、馬、牛、鹿、虎、兔、象、駱駝等,并可見生產、狩獵等場面。蓋頂往往有蟾蜍紐、臥獸紐、盤龍紐、方塊形紐等紐飾。陶倉無論有足無足,其形態都與洛陽等地的同類器基本相似,但是倉門的裝飾則頗具特色。最初的陶倉無倉門,稍晚逐漸出現以兩條陰線刻劃門的形態,并進而以陰線劃出方形倉門,在倉門上及兩側模印門栓及插銷。隨后簡化為以圓孔代表倉門,最后倉門結構消失。陶灶為長方體,這種形態的陶灶在各地并不鮮見,但豐泰墓地的陶灶往往于灶面兩端設計有擋火墻,擋火墻的墻面上均模印反映現實生活場景的紋飾,簡單的內容有雙闕,復雜的有一人端坐亭中;兩人對座于傘蓋下,身后各拴一條咆哮的狗等場景。陶井的形態與許多地區的相似,但其最初階段的井,唇緣下垂極甚,從外側觀之唇極厚,并往往模印魚、蛙、菱形、逗點等各類紋飾,很有特點。此外,豐泰墓地的隨葬品中,從西漢早期開始出現陶質的模型車輪,以代表車馬。流行于西漢中期,西漢晚期以后消失。這類遺存及其喪葬觀念少見于其它地區。
2.組合特征
(1)南陽豐泰墓地的陶器組合,有一個由器類不多,組合不一,發展到器類不多,組合整齊統一,再到器類繁多,組合多變的變化過程。戰國晚期,器類組合包括仿銅陶禮器的組合、雙耳罐組合、高領罐組合、雙耳罐與高領罐組合等。各種罐類組合簡單,常見一、二件罐類器而已。仿銅陶禮器的完整組合為鼎、盒、壺、模型壺、杯、盤、匜、勺,但其組合搭配并不嚴格,多數墓葬器類并不完整,有鼎、盒、模型壺,鼎、壺、模型壺,盒、壺、模型壺,鼎、壺,鼎,壺等各種組合。西漢早期前段罐類組合依然常見,但以仿銅陶禮器鼎、盒、壺、模型壺為完整組合的墓葬數量開始增加,并從西漢早期后段開始成為幾乎是唯一的隨葬品組合形式,在武帝前期至昭宣時期呈現鼎、盒、壺、模型壺與鼎、盒、壺、小壺并行的單一組合局面。少量有伴出車輪的情況。西漢晚期前段仍以鼎、盒、壺、小壺組合為主;雙耳罐又一次流行;模型明器中的倉開始出現;南方地區的印紋硬陶傳入本地區;另外,在整個西漢晚期,還盛行一類肩部有一道凹槽的陶罐,這類遺存絕大多數是單出。西漢晚期后段,奩、方盒、倉、灶、井、豬圈、磨、狗、雞、鴨等器類大量出現,并且逐漸成為隨葬品的核心組合。王莽以后,碗、盤、碟、魁、熏這類生活實用器出現。東漢中期,案、耳杯等所謂的奠器開始流行,各類人物俑、牛馬等動物俑進入組合。從西漢晚期前段開始,仿銅陶禮器偶見有組合不全的情況。西漢晚期后段以后,以鼎、盒、壺、奩、方盒、倉、灶、井、豬圈、磨、狗、雞為核心器類的組合,很少可見器類完整的情況。其中傳統仿銅陶禮器的鼎盒壺組合在王莽時期已極少,東漢早期以后,再未見完整的仿銅陶禮器組合,東漢中期以后鼎、盒兩種器類基本消失。器類組合不全的現象,雖與磚室墓的被盜擾有關,但在一些未被擾動過的墓葬中,也是常態。因此,這一現象可以視為時代的特征。
(2)在隨葬陶器的數量方面,南陽豐泰墓地也有某些規律性。例如:A.豐泰墓地出土仿銅陶禮器的墓葬共計106座。以鼎為標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如鼎為1件,則盒、壺及小壺等亦為1件;如鼎為2件,則其余各器亦為2件。呈現出規律性。B.模型明器中,灶、井、磨、圈等一般是1件;動物模型中,狗1件,雞多為2件。陶倉的組合數量在不同時期呈現一定變化。西漢晚期前段,據保存完好的土坑墓看,有兩種情況:一是出土于傳統仿銅陶禮器墓中,以5件為常數;一是出土于傳統罐類文化中,數量是1件。西漢晚期后段,陶禮器傳統墓葬隨葬倉的數量有所下降,雖仍可見到5件者,但出土3件者比5件多,其次也有2件者。罐類文化墓葬中,倉仍為1件。王莽時期不再見出5件倉者。此時雖因多為磚墓被盜擾,但有土坑墓出3件者,而各磚室墓多者為3,其次為2、1。東漢時期墓葬基本上都是磚墓,大抵以1件為常數。
(二)墓葬形制
南陽豐泰墓地土坑豎穴墓從形狀到結構,與各地同類墓并無明顯差別,磚室墓則頗具特征。因此,我們主要討論磚室墓的形制特征。#p#分頁標題#e#
1.建筑方式南陽地區漢代的修建,一般是先挖一個不帶墓道的豎穴土坑,然后在土坑中修筑磚室,磚墓的四壁與墓壙間的空隙不過數十厘米而已。據現場觀察,墓室兩端根本看不出有門的結構。因此,磚室的砌筑過程是四壁同時一層層向上壘砌,并不存在門的設置。墓室四壁壘砌到起券高度后,將葬具及死者由墓頂放入墓中,然后再行封頂。當然,為數不多的大型墓葬則一般都有墓道,也就會有門的結構存在,死者經由墓道、墓門進入墓室。墓壁砌法,除普通常見的錯縫平鋪直砌外,西漢晚期已出現幾順一丁的砌筑方式,有一順一丁、二順一丁、三順一丁等多種砌法。而在其它地區,此類砌法一般見于東漢晚期以后。南陽豐泰墓地的磚室墓墓頂以券頂為主,早期階段偶見無券頂而以木板蓋頂的建筑方式,應是未掌握券頂建造技術的權宜作法。東漢中晚期偶見穹窿頂結構。豐泰墓地磚室墓的鋪地磚,有豎排錯縫平鋪、豎排對縫平鋪、縱橫相間平鋪、人字形平鋪等不同形式。以豎排錯縫平鋪為多,豎排對縫平鋪其次,人字形鋪地磚多見于東漢以后。
2.墓葬形狀與結構南陽豐泰墓地56座形制結構較為明確的漢代磚室墓,包括長方形單室券頂墓、雙室并列券頂墓、三室并列券頂墓、橫前堂前后室券頂墓、前后室穹窿頂墓等多種形態。長方形單室墓是主流形態,共36座,占全部總數的64.29%。此類墓葬有三分之一墓底一端低于另一端10~20厘米,器物一般均放置在低的一端,形成一個主室加器物室的結構。雙室及三室并列結構是南陽漢墓較有特點的墓型。此類并列的雙室或三室,各室獨立,各有自己的券頂。在形狀、大小、結構、砌筑方式等方面則完全相同。各室間于隔墻上設券門彼此相通。此外,大部分墓葬的各室也呈一端低一端高的結構。豐泰墓地的橫前堂墓,最早出現于王莽時期,較之洛陽等北方地區此類墓型出現的時間要早。
(三)葬俗與葬制
1.豐泰墓地各墓的方向,由于骨架均未保存,據墓葬的朝向判斷有南北向及東西向兩種。南北向一般在5~15°之間,東西向一般在95~110°之間,大體上較為一致,可見當時認真測定過各墓葬的方向。其方向不與現代的正南北、正東西吻合,應該是當時的磁偏角與現代不一致造成的。在可以確定年代的233座墓葬中,南北向147座,東西向86座,南北向墓葬占大多數,接近于東西向墓葬的兩倍。但這只是表象,事實上因時間的不同,墓葬方向的總體趨勢呈現出幾乎完全不同的面貌。以武帝前期為界,武帝前期(含)以前總計80座墓葬中,南北向墓葬為72座,東西向為8座,兩者之比為8:1,南北向占絕對多數。從武帝后期開始的總計153座墓葬中,南北向墓葬為75座,東西向墓葬為78座,兩者之比約為0.96:1,東西向墓葬數量已超過了南北向,與此前截然不同。但是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并不清楚。從現場觀察不存在地形地勢的因素,從出土遺物分析也非文化屬性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產生這種劇變的原因還是一個謎團。
2.葬具與葬式方面,由于保存條件不好,骨架基本不存,因此葬式情況不明。葬具保存者,有陶棺8具,木棺18具(其中一座為并列雙棺),木質一槨一棺2具。木質葬具皆腐朽,因此結構不明。而陶棺尺寸最大的只有150厘米,多數不足120厘米,少數不足90厘米。用陶棺者,其隨葬器物均為陶罐。說明陶棺的使用一方面限于未成年人,另一方面僅流行于罐類文化傳統中。
3.模型明器成為隨葬品組合器類,雖晚于關中地區,但較中原洛陽地區為早,而且器類獨具特色。其一,以陶質車輪明器用于隨葬,出土時一般都是一對,以局部代整體,作為車的象征,與其它地區往往以車馬器指代車不同。這一現象出現于西漢早期,流行于西漢中期,至西漢晚期前段基本消失。銅、鉛質地的車馬器,最早出現于西漢中期后段。其二,在西漢早期后段即開始以模型小狗這類家畜模型用于隨葬。其三,生活設施類模型明器從西漢晚期前段開始出現,但在西漢晚期前段及后段的相當長時段中,多見以倉為隨葬,倉灶井豬圈磨雞狗成組合出現于西漢晚期后段,但興盛與流行是從王莽時期開始的。
4.豐泰墓地各時期的隨葬品,皆以陶器為主,西漢早期前段有3座以鼎、壺,鼎、鈁為核心器類的銅禮器組合墓葬,顯示墓主身份較高。在豐泰墓地中,除少數時段有零星秦式銅容器伴出外,其余銅禮器僅見于此段3座墓葬中,不見于前,絕跡于后。因為豐泰墓地出土銅禮器的墓葬數量少,我們可以借助于南陽一中墓地的材料分析。南陽一中墓地在戰國末及西漢早期前段,有11座墓葬隨葬以銅鼎、銅鈁、銅勺為核心的銅禮器組合,銅鼎、銅鈁一般都是2件,銅勺則有2件與1件的情況,而在同一時期出土仿銅陶禮器的墓葬中,未見有2件一套的情況。因此,西漢早期后段開始出現的隨葬2件一套仿銅陶禮器的墓葬,其墓主的身份應與西漢早期前段隨葬銅禮器墓主的身份相近。由此表明,代表傳統禮制的銅禮器的使用,在西漢早期后段以后走向衰落,完全被仿銅陶禮器所取代。與此同時,南陽豐泰墓地西漢早期前段的仿銅陶禮器墓葬中,已有3座是2件一套,另外還有一座墓葬,同出陶鼎、陶鈁、銅榼。說明豐泰墓地較一中墓地更早開始了由銅禮器向陶禮器的轉化。
5.在墓葬的等級序列方面,由于磚室墓多數被擾,器類不全,不能準確反映其原貌。而土坑墓盡管也有一些器類未能復原,但其器類及數量還是較為清楚的。所以我們主要通過對土坑墓的分析,來探討墓葬等級問題。A.豐泰墓地的土坑墓中,墓壙長度小于2米的墓葬共有7座,其中有5座見有陶棺。而據我們在前面所作分析,陶棺的使用限于未成年人。因此可以認為,墓壙長度在2米以下的墓葬,是非成年人墓,應與身份等級無關。B.豐泰墓地的土坑墓,大約可以分為兩個身份等級略有高低的人群。身份略高的人群,其墓壙規模一般在3米以上,少數并有斜坡墓道結構;多隨葬銅禮器、2件一套的仿銅陶禮器、陶質車輪明器、玉器等遺物。身份略低的人群,其墓壙規模一般在3米以下,一般只隨葬一套仿銅陶禮器或日用陶器。C.隨葬仿銅陶禮器或日用陶器的墓葬,其器類組合的不同雖然起因于文化傳統的不同,但出土無耳高領折沿罐、無耳矮領折沿罐、雙耳罐的墓葬,在各個時期絕大多數墓葬的規模都在3米以下,而且這種現象在不同時伴出仿銅陶禮器、模型明器的罐類組合墓葬中尤其突出。15座出土車輪的墓葬,均不與罐類器同出。因此可以認為,使用日用陶器隨葬的人群,其身份在當時普遍略微偏低也是事實。
秦漢社會若干歷史背景的詮釋
前面對南陽豐泰墓地的文化結構、文化內涵呈現出來的面貌作了歸納分析。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就某些文化現象背后所蘊含的社會歷史背景略作探索。
(一)器類組合的變化,折射中央集權政治統治力的強弱態勢
南陽豐泰墓地出土仿銅陶禮器的墓葬數量最多,共計106座(包括同出其它器類者),占總數的59.89%,時間跨度從戰國晚期直至東漢晚期。出罐甕類陶器的墓葬數量其次,共計98座(包括同出其它器類者),占總數的55.37%,在數據比例上幾可與前類遺存分庭抗禮。兩者共同構成了南陽地區秦漢社會文明的基礎。但這種分庭抗禮的態勢并非貫穿始終,主要存在于戰國晚期后段、西漢早期前段、西漢晚期三個時期。從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雙耳罐及無耳高領折沿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獨立存在或彼此依存,武昭宣時期一度式微,基本不見,到西漢晚期,雙耳罐開始較多地進入了仿銅陶禮器和模型明器的組合中。興盛于西漢晚期的無耳矮領折沿罐,除個別情況下,它們一般不與仿銅陶禮器及模型明器同出,表現出了強烈的排它性。東漢以后,上述兩類遺存都走向了衰亡。南陽豐泰墓地仿銅陶禮器的核心組合是鼎、盒、壺,往往配以小壺或模型壺或小罐。這種穩定的組合形態貫穿西漢早、中、晚期前段,尤其是在西漢早期后段到西漢晚期前段,幾乎是唯一的組合形態。組合不全的情況主要集中在戰國晚期及西漢晚期后段至王莽時期。上述這些現象,向我們揭示出這樣的歷史背景,那就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政治局面,對文化的整合與規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并且隨著中央集權統治力度的強弱變化而產生一定的波動。在戰國晚期,本地區迭經戰亂,伴隨著韓、楚、秦的政權交替,各種文化勢力也相繼登上這一舞臺,加上中原傳統禮儀文化持續的影響,使得這一地區的文化面貌異彩紛呈。西漢早期后段至晚期前段的文化面貌則呈現出一種主流突出,漸趨一統,穩定發展的態勢。表明隨著秦漢統一大業的完成,中央集權政治的約束力、執行力不斷加強,社會穩定,思想統一,傳統禮儀對于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規范有著較強的束縛力。至西漢晚期晚段及王莽時期,隨葬陶器組合呈現出異常復雜的態勢,說明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不遵循傳統禮儀規范的行為存在。當然,由于這一時期磚室墓較多,被盜擾現象也較嚴重,因此使得各墓呈現出來的器類組合情況并不能完全反映其本來面貌,而顯得紛繁多變。但這一時期的土坑豎穴墓或雖屬磚室墓但未經擾動者,也多呈現出這樣的現象。因此,隨葬器類組合具有一定隨意性是不爭的事實,并由此導致本地區的文化面貌呈現出一種較為混沌的狀態。表明整個社會矛盾日漸激化,中央集權政治的約束力、執行力在逐漸削弱,社會處在動蕩與變革時期,傳統的禮儀制度對于人們的束縛力大為減弱。
(二)器類組合的變化,反映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進程及其新的文化傳統誕生
1.南陽豐泰墓地從戰國晚期前段開始形成,此時基本上只有韓文化傳統存在,偶見楚文化傳統,兩者間存在著一定的隔閡。戰國晚期中段,韓文化傳統仍略占優勢,楚文化傳統的地位上升,秦文化傳統開始進入本地區。其中韓文化與楚文化傳統有漸趨融匯之勢,秦文化雖也有融入之舉,但基本上呈現出與前二者各自為政的局面。到戰國晚期的末段,韓文化傳統與楚文化傳統并駕齊驅,兩者間并有較多的共存現象。表明從此階段開始,原來兩個不相兼容文化傳統,開始彼此接納,逐漸融合。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兩者長期共居于一地,逐漸消融了彼此間的堅冰,交往日漸增多,理解逐漸加深,開始變得可以互相接納,甚至可能出現婚姻關系。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此地被秦占領以后,原來分屬于韓文化和楚文化傳統的居民都屬被征服者,同是天涯淪落人,而他們的文化傳統較之于秦文化本來也更為接近,彼此間更容易產生親近感,從而逐漸融匯到一起。
2.從戰國晚期后段開始,出現了融匯中原、秦、楚文化傳統的新型仿銅陶禮器器類組合,預示著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在本地誕生。這種新的文明形式在進入漢代以后迅猛發展,很快確立了領導地位,并成為了整個西漢社會喪葬文化的主流傳統。而這種文明的結構形態,恰是秦漢社會諸多淵源關系的縮影。
3.罐類器中,雙耳罐、高領罐單獨或與缽、釜類同出,或它們之間的組合,基本上集中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無耳矮領折沿罐則流行于西漢晚期。可見此類遺存所代表的人群,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這一階段,具有十分強烈的獨立性,頑強保持著自己固有的傳統。罐類器與仿銅陶禮器同出的情況,在戰國晚期雖已出現,但數量極少,這種狀況一至延續到西漢早期。而且在這一時期的仿銅陶禮器與罐類器組合中,仿銅陶禮器的器類一概不全,未見有完整的仿銅陶禮器組合與之同出。說明在這類墓葬中,罐類器是主導,仿銅陶禮器是客體,是罐類文化傳統所代表的人群,接受仿銅陶禮器所代表文化傳統的影響。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并沒有全盤接受或者說沒有充分理解這一文化的內涵,并未完全遵循此類遺存的隨葬規范,因而在使用仿銅陶禮器隨葬的過程中,對器類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隨意性。這一點從西漢晚期陶倉出現以后,仿銅陶禮器傳統的墓葬中一般以三或五件為常數,而罐類文化傳統的墓葬中只出一件的情形,也可以得到印證。西漢晚期,罐類器與仿銅陶禮器和模型明器的組合同出者往往有組合較為齊全的情況。這種現象或許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是經過長時期的影響,罐類文化傳統已能完整理解仿銅陶禮器文化傳統的涵義,因而能正確運用其相關的喪葬規范。其一是仿銅陶禮器文化傳統開始接納罐類文化,并將之融匯于自身的隨葬規范中。
(三)器類組合的變化,昭示喪葬觀念、禮儀規范的轉化
1.喪葬禮儀由不健全到規范統一再到推陳出新南陽豐泰墓地仿銅陶禮器組合,在西漢早期至西漢晚期前段,呈現出鼎、盒、壺配以小壺或模型壺或小罐的穩定形態,并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器類不全的情況主要集中在戰國晚期及西漢晚期后段至王莽時期。東漢以后,仿銅陶禮器已不再見有傳統的完整組合,鼎在東漢中期以后不復存在,盒的流行也僅限至東漢中期。戰國晚期這種組合不全的情況,可能是由于仿銅陶禮器這種喪葬理念剛剛影響到這一地區,其真正的內涵還未能得到正確理解,因此規范還不夠健全,對隨葬器類的選擇有一定的隨意性。西漢早期后段至晚期前段,在大一統中央集權政治的推動下,仿銅陶禮器這種喪葬理念得到深入推廣,其相應的喪葬規范得到全面理解與執行,因而呈現出統一、穩定的局面。西漢晚期后段至王莽時期,出現大規模組合不全現象,部分原因是因為磚室墓往往被擾所致,但這不是主因,因為土坑豎穴墓或未經擾動的磚室墓同樣有器類組合不全者,而且東漢以后,無論擾與不擾,也多呈現出仿銅陶禮器不齊全的狀況。因此,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西漢晚期以后,傳統的禮儀規范已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人們的思想觀念漸行漸遠,其束縛力大為減弱。新的思想觀念、禮儀規范開始逐漸形成,仿銅陶禮器已不再具有原有的地位,而逐漸讓位于新的規范,新的物質載體。這一點由2件一套仿銅陶禮器出現于西漢早期,盛行于西漢中期,衰落于西漢晚期也可以得到印證。這種規律性的變化,當是由于在西漢早中期,傳統的等級制度及其物質載體對人們的行為還有著較強的影響力與束縛力。而到西漢晚期以后,這種規范已失去了作用,于是喪葬的禮儀也隨之發生了改變。#p#分頁標題#e#
2.喪葬觀念由尚虛禮向重實用轉化南陽豐泰墓地隨葬陶器,在戰國晚期至西漢晚期這一階段,基本上是以仿銅陶禮器為主,罐甕類其次的狀況。說明自東周以來的喪葬觀念、禮儀傳統,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內涵和普遍規范。以倉、灶、井、豬圈、磨為核心的模型明器則始見于西漢晚期前段,到西漢晚期后段大行其道;以奩、方盒為代表的一組器物在西漢晚期晚段開始流行;而以案、耳杯、碗、盤、碟為代表的一類器物在稍晚的時期也開始出現。三類遺物并為新生事物,且相伴流行至東漢晚期。奩、方盒從其仿漆器造型來看,實際用途大約應與盛放梳妝冶容等日常用品有關。而案、耳杯等器類,一般定義為奠器,理由是這類遺物一般都放置在雙室墓的前室,是作為墓內祭祀用器使用的[9]。其實這種理解是片面的。這類遺物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用器,當它們葬入墓中后,自然是被放置在了象征著前堂或廳的前室內。它們或者在葬入的時候確曾作為奠器使用過,但并不能由此就簡單地劃定它們的性質。上述遺存的出現,表明社會規范、人的觀念、喪葬禮儀在此時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原來的尚虛禮變為了重實用。在此之前的單一而齊整的仿銅陶禮器隨葬品中,其組合中有炊煮器、酒器、盛器,不包括食器,更不包括諸多的日常用器、生活設施,顯然更多地是從禮制層面出發的喪葬理念。到了西漢晚期,隨葬品中大量反映現實生活的器類出現,表明人們的喪葬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世俗生活的眷戀成為時尚的風潮,從而一種全新的喪葬理念開始逐漸形成。
(四)器物體形的變化,映襯秦漢社會經濟形勢的起伏,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們生活態度變遷
南陽豐泰墓地仿銅陶禮器的器形,有一個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演化軌跡:從戰國晚期到西漢昭宣時期,各器類處在一個同步逐漸變大的上升階段,這一過程在武帝后期及昭宣時期達到頂峰。西漢晚期前段開始,器形開始逐漸變小,直至東漢時期,各類隨葬品皆小型化。制作工藝,有一個由粗及精,由簡到繁,再到粗而簡的變化過程:戰國晚期至武帝前期,器物火候偏低易碎,質地粗糙,器表裝飾簡單。武帝后期開始至西漢晚期后段,器物火候較高,器表多經打磨,裝飾漸趨豐富。王莽以后,質量再次下降,裝飾趨于簡化。秦漢社會歷史的發展,呈現出由秦至漢初的民不聊生、經濟困乏,到文景的勵精圖治、漸顯生機,再到武昭宣的蓬勃發展、國力鼎盛,最后到西漢晚期以后政治經濟漸漸沒落的變化。南陽漢代墓葬出土器物形體方面由小及大,再由大而小的這一變化過程,與秦漢社會歷史發展的變化幾乎重合在同一軌跡線上,恰是秦漢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縮影。而隨著社會經濟起步、發展、繁榮、衰落的過程,人們的生活態度也由初期的因陋就簡,發展到中期的求大崇美,再到后期的粗疏草率。反映了隨著社會歷史發展的起伏,人們的生活心態也隨之產生波動。
(五)墓葬數量的變化,可窺秦漢時期人口數量的增減
南陽豐泰墓地各期墓葬的數量呈駝峰狀,戰國晚期前段至西漢早期前段,墓葬數量呈上升態勢,在西漢早期前段達到一個頂峰。西漢早期后段的墓葬數量急劇下降,整個西漢中期的墓葬數量均徘徊于谷底。西漢晚期前段數量再次上升,至西漢晚期后段達到一個新的峰值。王莽以后再次逐步下降。但東漢時期墓葬數量尤其是中晚期的數量偏少則未必是實情。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至少有兩個:其一,一部分磚室墓被盜擾一空,以致無法斷代,因此未進入數據統計中。其二,東漢時期盛行合葬墓,因此,墓葬數量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喪葬人口的減少。總體而言,上述現象應該反映出這一區域的人口生殖經歷了類似的運動曲線。西漢晚期是本地區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其總數是此前各時期的數倍。或者這一現象也是整個漢代社會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