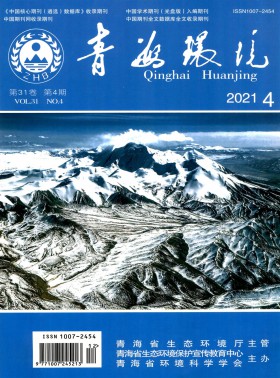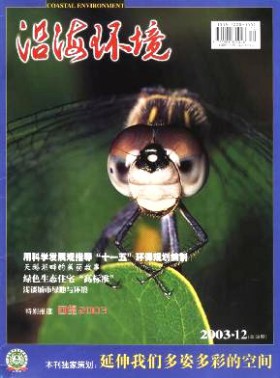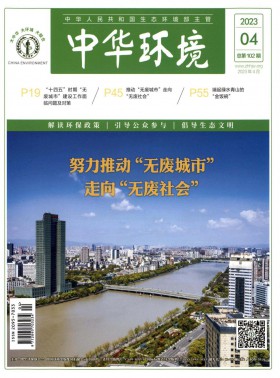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探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lái)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易詩(shī)雯 張萌 單位:吉林大學(xué)
對(duì)人類古老性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和進(jìn)化論,是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產(chǎn)生的一個(gè)重要背景。在18世紀(jì)晚期以前的歐洲,對(duì)于人類起源的解釋依賴于傳統(tǒng)的《圣經(jīng)》。“七天創(chuàng)世說(shuō)”以自然和人類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論否認(rèn)遠(yuǎn)古時(shí)代和原始人群,與此同時(shí),在那個(gè)時(shí)期地質(zhì)與古生物學(xué)所揭示的一些人類與滅絕動(dòng)物共存的事實(shí)也被掩蓋,以喬治•居維葉(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蘭(WilliamBuckland)為代表的一些地質(zhì)學(xué)家宣揚(yáng)“災(zāi)變理論”,一系列生命形式的進(jìn)化被解釋為上帝超自然的創(chuàng)造。然而,越來(lái)越多的地質(zhì)學(xué)與古生物學(xué)證據(jù)使得《圣經(jīng)》的解釋與人類古老性問(wèn)題備受爭(zhēng)論。1785年,詹姆斯•赫頓(JamesHutton)為地質(zhì)史提出了一種均變論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從地質(zhì)學(xué)上講古代與現(xiàn)代情況類似,所有地質(zhì)層都可以用長(zhǎng)時(shí)間里一直運(yùn)轉(zhuǎn)的、目前仍在發(fā)生作用的地質(zhì)動(dòng)力來(lái)解釋。1830年到1833年間,查爾斯•賴爾(CharlesLyell)發(fā)表了他的《地質(zhì)學(xué)原理》,支持了地質(zhì)變遷的均變假設(shè)。地質(zhì)學(xué)上的均變論表明,過(guò)去是一個(gè)漫長(zhǎng)和在地質(zhì)學(xué)上并未間斷的時(shí)期,其間有可能發(fā)生其他的事件。對(duì)人類古老問(wèn)題的正視同樣使生物進(jìn)化的觀點(diǎn)在一些科學(xué)家中被普遍討論。哲學(xué)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紀(jì)50年代開(kāi)始為科學(xué)和政治問(wèn)題提倡一種一般的進(jìn)化方法,環(huán)境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動(dòng)下完成了從原本的浪漫與美學(xué)的范疇向具體和科學(xué)意義的轉(zhuǎn)變。1859年11月,查爾斯•達(dá)爾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種起源》出版,這本書濃縮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變論和地質(zhì)學(xué)的啟發(fā),大大推進(jìn)了進(jìn)化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廣泛普及了自然選擇的概念。18~19世紀(jì),對(duì)人類古老性與進(jìn)化論思想認(rèn)識(shí)的核心在于:人們開(kāi)始將“人從哪里來(lái)”的問(wèn)題作為科學(xué)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釋。另一方面,均變論與進(jìn)化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機(jī)制,使得我們相信:我們完全可能透過(guò)現(xiàn)在的地質(zhì)材料為重新研究過(guò)去提供條件,也可以用生物進(jìn)化的過(guò)程來(lái)說(shuō)明現(xiàn)代物種的起源與分布以解決古生物學(xué)上的演變。對(duì)人類古老性的認(rèn)識(shí)和進(jìn)化論成為后來(lái)環(huán)境考古誕生的一個(gè)重要基礎(chǔ),此時(shí)期發(fā)現(xiàn)的眾多地層上的共存關(guān)系為后來(lái)的地層學(xué)研究提供了條件。可以說(shuō),均變論與進(jìn)化思想是環(huán)境考古“將今論古”原則的一個(gè)重要的思維前提,而地層學(xué)則是考古學(xué)發(fā)展的有力技術(shù)支持。
貳世界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發(fā)展簡(jiǎn)史
一、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分類———描述階段(20世紀(jì)30年代以前)19世紀(jì)中期,在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主的歐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學(xué)實(shí)踐,顯示了當(dāng)代考古學(xué)雛形的各種特征。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后期環(huán)境考古理論發(fā)展的淵源。斯文•尼爾森(SvenNielsen)是這一個(gè)地區(qū)最早過(guò)去的關(guān)注生存方式,并試圖通過(guò)考古材料推斷史前生存方式科學(xué)家。尼爾森運(yùn)用模擬實(shí)驗(yàn)和民族志標(biāo)本進(jìn)行系統(tǒng)比對(duì)以確定石器與骨器用途的嘗試,被認(rèn)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論貢獻(xiàn)之一。他還第一次將生計(jì)發(fā)展與技術(shù)變遷聯(lián)系起來(lái)研究,這也許是用過(guò)程方法來(lái)解釋史前變遷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學(xué)家約翰•亞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發(fā)掘丹麥泥沼的過(guò)程中,揭示出一種森林變遷的方式。大約在19世紀(jì)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開(kāi)始意識(shí)到文化進(jìn)化與環(huán)境史的聯(lián)系,并在最后將石器時(shí)代、青銅時(shí)代與鐵器時(shí)代分別與森林變遷的松樹(shù)、櫟樹(shù)、榆樹(shù)階段相對(duì)應(yīng),完成了湯姆森三期說(shuō)中的器物序列與環(huán)境變遷的對(duì)接。詹斯•沃爾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麥的原始古物》一書中將湯姆森三期說(shuō)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廣,并將其與尼爾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發(fā)現(xiàn)結(jié)合到一起,從而對(duì)丹麥?zhǔn)非笆纷鞒隽艘环N總體的解釋。1846年以后,沃爾塞訪問(wèn)了不列顛和愛(ài)爾蘭,對(duì)這些國(guó)家史前遺存的觀察使他深信湯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適用于歐洲大部分地區(qū)甚至整個(gè)歐洲的。
19世紀(jì)50年代初,以沃爾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約翰•喬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領(lǐng)銜的丹麥交叉學(xué)科委員會(huì)對(duì)“廚庖垃圾貝丘”進(jìn)行了研究。在這次的研究中雖然沒(méi)有就貝丘的年代達(dá)成一致,但內(nèi)容涉及到古環(huán)境的植物背景、季節(jié)變化和動(dòng)物馴化和人類行為干預(yù)等等方面,開(kāi)啟了考古發(fā)現(xiàn)與它們的古環(huán)境背景相結(jié)合的先河。他們整合了考古學(xué)、生物學(xué)和地質(zhì)學(xué)方法來(lái)調(diào)查史前丹麥人是如何生活的,無(wú)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嘗試。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樣。1853年到1854年間,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點(diǎn),將保存在飽水環(huán)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來(lái)。這些湖居遺址(LakeDwellings)為瑞士考古學(xué)家提供了一個(gè)機(jī)會(huì),來(lái)研究這些人群在自然環(huán)境中經(jīng)濟(jì)和生活方式的變遷,并最終考訂了他們的年代在新石器時(shí)代到青銅時(shí)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納維亞和蘇格蘭的研究有著更為優(yōu)越的材料,為環(huán)境考古嘗試提供了難得的條件。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早在19世紀(jì)中期,史前的考古學(xué)研究在以斯堪的納維亞為代表的歐洲就已經(jīng)具有當(dāng)代考古學(xué)的雛形。雖然此時(shí)北歐考古學(xué)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結(jié)合運(yùn)用共生發(fā)現(xiàn)物、簡(jiǎn)單的式樣排列和地層學(xué)背景來(lái)建立相對(duì)年代學(xué)的能力,即考古學(xué)的研究目的還停留在分類和分期上。但這一批北歐科學(xué)家們的研究方法已經(jīng)頗為超前。在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如進(jìn)化論、文化———歷史學(xué)、過(guò)程———功能方法論等有史前考古學(xué)特點(diǎn)的理論淵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論價(jià),而是作為一種了解過(guò)去人類行為的信息來(lái)源和了解人類歷史和文化發(fā)展的依據(jù)。但令人遺憾的是,北歐考古學(xué)家所用的這一套方法論,在后來(lái)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并沒(méi)有被普遍的接受與使用。
進(jìn)入到20世紀(jì)的初期以后,與環(huán)境有關(guān)聯(lián)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開(kāi)。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亞土庫(kù)曼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時(shí),第一次對(duì)恢復(fù)史前遺址的古環(huán)境進(jìn)行了努力;1914年兩河流域第一次完整發(fā)掘巴比倫王國(guó)城市建筑。科爾德維和安德烈發(fā)掘了巴比倫城和亞述城,成為生態(tài)考古的先聲。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類生活與現(xiàn)代沉積的關(guān)系,探討了美國(guó)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會(huì)環(huán)境及氣候變化對(duì)農(nóng)業(yè)的影響。……20世紀(jì)30年代左右,英國(guó)率先提出了環(huán)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倫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環(huán)境考古部,邁出了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系統(tǒng)實(shí)踐的第一步。生態(tài)學(xué)在這個(gè)時(shí)期(20世紀(jì)20年代)完成了從建立到框架化的發(fā)展。這個(gè)時(shí)期生態(tài)學(xué)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基于“過(guò)程———適應(yīng)”理論的分類,生態(tài)學(xué)建立起一個(gè)以不同地理區(qū)動(dòng)植物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框架,各種生物的多樣性和分布都被考慮,并相關(guān)聯(lián),最終為食物鏈、食物網(wǎng)和生態(tài)位等生態(tài)學(xué)概念作出了定義。這一時(shí)期的生態(tài)學(xué)與考古學(xué)看似是獨(dú)立發(fā)展的兩個(gè)單位,但實(shí)際上生物學(xué)理論與方法的發(fā)展為考古學(xué)的進(jìn)步提供了模范,這一時(shí)期生態(tài)學(xué)“過(guò)程———適應(yīng)”的理論為以文化生態(tài)學(xué)為基礎(chǔ)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識(shí)基礎(chǔ),對(duì)下一時(shí)期考古學(xué)理論的轉(zhuǎn)變有很大貢獻(xiàn)。#p#分頁(yè)標(biāo)題#e#
19世紀(jì)下半葉到20世紀(jì)30年代以前,環(huán)境在考古實(shí)踐中的應(yīng)用已經(jīng)初步包含了氣候,水文,古動(dòng)物群等古環(huán)境成分。但該時(shí)期大部分古環(huán)境研究,領(lǐng)域還不夠廣闊,針對(duì)環(huán)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然生物環(huán)境的描述和恢復(fù),很少涉及古代文化與其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的探討。19世紀(jì)20年代之前考古學(xué)基本概念還未建立,20年代到30年代的考古學(xué)處于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階段,考古學(xué)家傾向于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在具體的與環(huán)境結(jié)合的研究中,對(duì)人地關(guān)系或者人類對(duì)環(huán)境干預(yù)問(wèn)題上探討很少,比起之前19世紀(jì)中葉的北歐甚至可以說(shuō)是退步的。需要注意的是,這個(gè)時(shí)期人們研究環(huán)境變遷與考古學(xué)文化變化的關(guān)系時(shí)通常將考古學(xué)變化歸結(jié)為環(huán)境變化或直接把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看得很模糊,從而陷于“環(huán)境決定論”中,缺乏對(duì)環(huán)境、人類活動(dòng)和文化之間關(guān)系的系統(tǒng)探討和人類行為在考古材料中的解釋。另外,環(huán)境考古中研究的文化與這個(gè)階段定義的“與人群相對(duì)應(yīng)的遺存組合”的文化概念的不匹配(眾所周知,考古學(xué)文化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主要是器物組合,但器物的變遷不能與環(huán)境的變遷直接畫上等號(hào)),考古學(xué)文化所依賴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無(wú)法與環(huán)境變遷建立直接的聯(lián)系的事實(shí)在當(dāng)時(shí)的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二、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早期功能———過(guò)程階段(主要是20世紀(jì)40~50年代)隨著越來(lái)越多的考古學(xué)家意識(shí)到,文化———歷史的考古學(xué)方法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yùn)轉(zhuǎn)和演變的工作,新的方法應(yīng)運(yùn)而生。這些新途徑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guò)程論。需要注意的是,環(huán)境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技術(shù)在20世紀(jì)初就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但對(duì)考古學(xué)解釋仍沒(méi)有產(chǎn)生有效的支持。早在20世紀(jì)初期,地質(zhì)學(xué)家杰拉德•德•吉爾(GerarddeGeer)就開(kāi)始利用冰緣湖泊的疊壓紋泥序列來(lái)為斯堪的納維亞過(guò)去12000年來(lái)的冰緣消退斷代,并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歷紀(jì)年校準(zhǔn)的自然年表。使得將文化變遷不僅與序列而且可以與涉及的實(shí)際時(shí)間長(zhǎng)度一起加以考慮。另一位瑞典人倫納特•馮•波斯特(E.J.LennartvonPost)利用孢粉,改善了斯廷斯特拉普對(duì)冰后期植被變遷的先驅(qū)性研究。大約1916年,他得出了意在顯示斯堪的納維亞史前期相繼階段中各類樹(shù)種百分比圖譜,并對(duì)應(yīng)于德•吉爾的冰緣地質(zhì)年代學(xué)得出了更為精確的日歷。孢粉分析方法是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發(fā)展中最重要的進(jìn)步之一,這種分析方法有著更高的效率,它不僅分布廣泛而且為較大區(qū)域內(nèi)的差異性研究提供了可能。1940年到1960年間,生態(tài)學(xué)方法主導(dǎo)著斯堪的納維亞的石器時(shí)代研究。孢粉分析方法在20世紀(jì)30年代引入英國(guó),并由生物學(xué)家哈里•戈德溫用于考古學(xué)研究。類似的環(huán)境功能———過(guò)程論還被應(yīng)用于探討黃土堆積與聚落分布、糧食起源的綠洲與干旱理論、農(nóng)業(yè)起源等等問(wèn)題上,并涉及北歐、中歐、美國(guó)、俄國(guó)等等國(guó)家。由于篇幅問(wèn)題,在此不一一列舉。20世紀(jì)50年代左右,生態(tài)學(xué)進(jìn)入了時(shí)空上綜合研究的階段。生態(tài)學(xué)研究從標(biāo)準(zhǔn)的分類方法轉(zhuǎn)變成了注重相互過(guò)程的方法。人類學(xué)(包括考古學(xué))也在此時(shí)相應(yīng)地提出了人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問(wèn)題。這些對(duì)人類社會(huì)與他們的環(huán)境背景之間的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促成了人類行為重要方面的一種功能———過(guò)程觀點(diǎn)。這種方法鼓勵(lì)進(jìn)行古環(huán)境以及史前文化對(duì)這些環(huán)境進(jìn)行生態(tài)適應(yīng)的研究,認(rèn)為自然環(huán)境對(duì)于適應(yīng)種類會(huì)產(chǎn)生制約,導(dǎo)致對(duì)特定反應(yīng)的性質(zhì)產(chǎn)生可能的作用。
早期功能———過(guò)程階段與環(huán)境考古密切相關(guān)的主要探索包括柴爾德(V.GordonChilde)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ck)的生態(tài)學(xué)方法、泰勒(WalterTaylor)的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斯圖爾德(JulianSteward)的文化生態(tài)學(xué)和威利(GordonR.Willey)的聚落考古。柴爾德在20世紀(jì)20年代晚期就偏離了傳統(tǒng)的文化———歷史學(xué)方法,并在后來(lái)試圖仿效經(jīng)濟(jì)史學(xué)家的工作,尋找史前期普遍存在的經(jīng)濟(jì)趨勢(shì),并以此來(lái)解釋傳播的特定案例。他的研究結(jié)果展示在《遠(yuǎn)古的東方》(TheMostAncientEast1928)、《青銅時(shí)代》(TheBronzeAge1930)和《遠(yuǎn)古東方的新啟示》(NewLightontheMostAncientEast1934)三本書內(nèi)。柴爾德不只將文化變遷解釋為技術(shù)發(fā)明的結(jié)果,他也留意影響采納這些發(fā)明的廣泛經(jīng)濟(jì)和政治背景,并將一些經(jīng)濟(jì)變遷解釋成對(duì)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反應(yīng)(例如他贊同之前的綠洲理論)。這樣一種經(jīng)濟(jì)學(xué)方法本質(zhì)上含有一種多線進(jìn)化的視野,雖然柴爾德的有些論證有著解釋特定考古發(fā)現(xiàn)而非一般觀察的嫌疑,但是他也從另一方面拉近了對(duì)史前文化進(jìn)行靜態(tài)重建與求助于外來(lái)因素解釋演變之間的距離。在許多方面補(bǔ)充了功能論的另一種方法是由格拉厄姆•克拉克首創(chuàng)的。克拉克認(rèn)為,考古學(xué)應(yīng)該“研究人類過(guò)去是如何生活的”并指出要達(dá)到這個(gè)目的,考古材料必須從功能觀的視角來(lái)予以觀察,并只有與社會(huì)關(guān)聯(lián)才有意義。一個(gè)文化的基本功能或生活方式是要保證一個(gè)社會(huì)的生存,這意味著文化的所有方面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在著作《考古學(xué)與社會(huì)》(ArchaeologyandSociety)中,克拉克發(fā)表了一份流程圖,將文化的各個(gè)方面與食物供應(yīng)聯(lián)系起來(lái),后來(lái)又添加了生境(HABITAT)和群落作為生計(jì)之下的雙重基礎(chǔ),這也許是最早發(fā)表的將文化與環(huán)境因素作為單一系統(tǒng)組成部分加以聯(lián)系的圖示。在《考古學(xué)與社會(huì)》中克拉克宣稱,考古學(xué)家的最終目的應(yīng)該是從社會(huì)史的角度解釋考古材料。在后來(lái)十年里,克拉克試圖通過(guò)完善技術(shù)來(lái)發(fā)展他的生態(tài)學(xué)方法,并著重探討了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1949~1951年間,克拉克發(fā)掘的飽水遺址———斯塔卡(StarCarr),他對(duì)這個(gè)遺址的研究堪稱環(huán)境考古研究的典范。在發(fā)掘期間,克拉克撰寫了《史前歐洲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基礎(chǔ)》,將生態(tài)系統(tǒng)概念系統(tǒng)地應(yīng)用于考古學(xué)。文化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被克拉克視為相互作用,而經(jīng)濟(jì)則被定義為“對(duì)特定自然和生物條件所做的某種需求、能力、希冀和價(jià)值觀調(diào)節(jié)”。在克拉克的引導(dǎo)下,考古遺址出土動(dòng)植物遺骸的實(shí)驗(yàn)室研究,以及對(duì)它們從生態(tài)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進(jìn)行闡釋成為重要學(xué)科交叉的專業(yè)化趨勢(shì),并被諸如動(dòng)物考古學(xué)、古植物學(xué)、生物考古學(xué)的名稱所涵蓋。
1948年沃爾特•泰勒的博士論文《考古學(xué)之研究》(AStudyofArcheology)倡導(dǎo)一種“科學(xué)”的方法,認(rèn)為應(yīng)該將“為人類行為和文化演變尋找通則”是考古學(xué)與民族學(xué)的最終目標(biāo)。泰勒在論文中聲稱,幾乎沒(méi)有幾個(gè)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家關(guān)注系統(tǒng)重建史前人類的生活或解釋史前期發(fā)生了什么,相反,他們熱衷于純粹的“編年史”,進(jìn)而指出,由于美國(guó)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家有限的目標(biāo),造成了田野考古工作分析十分馬虎,動(dòng)植物遺存的提取和鑒定往往很不夠,因此考古學(xué)家對(duì)古人類的食譜、生業(yè)方式毫無(wú)了解。為了彌補(bǔ)這些缺點(diǎn),泰勒進(jìn)一步提出了一種“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建議在傳統(tǒng)的調(diào)查之外,應(yīng)特別留意考古材料的關(guān)聯(lián)性和數(shù)量、空間分布、制作與使用方法……也必須收集有關(guān)遺址的古環(huán)境背景信息和民族志材料。泰勒試圖從功能整合的文化形態(tài)來(lái)了解考古材料,“掇合方法”的一個(gè)獨(dú)特方面是賦予了一個(gè)遺址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重要性,并強(qiáng)調(diào)了考古的目的在于運(yùn)用證據(jù)重建史前遺址居民是如何生活的。泰勒的方法,使以前許多被人忽視的古環(huán)境細(xì)節(jié)被重新關(guān)注,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對(duì)象因此加以擴(kuò)展。但與克拉克不同的是,泰勒并沒(méi)有把文化看作一個(gè)生態(tài)適應(yīng)性的東西。#p#分頁(yè)標(biāo)題#e#
朱利安•斯圖爾特是第一位明確采納人類行為唯物主義觀點(diǎn)的美國(guó)民族學(xué)家,他極大地增進(jìn)了對(duì)生態(tài)因素在塑造史前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所發(fā)揮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發(fā)表文章指出,“考古學(xué)家和民族學(xué)家應(yīng)該設(shè)法了解文化變遷的性質(zhì),為人類行為的生態(tài)學(xué)分析作出貢獻(xiàn)。因此,考古學(xué)家必須停止專著與器物的形制分析,并開(kāi)始利用他們的材料研究生存經(jīng)濟(jì)、人口規(guī)模和聚落形態(tài)的變遷。斯圖爾特這種利用生態(tài)學(xué)方法了解文化變遷的理論被稱為文化生態(tài)學(xué),是現(xiàn)代環(huán)境考古的理論基礎(chǔ)。受到斯圖爾特和克拉克的影響,生態(tài)方法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美國(guó)已經(jīng)有一批重要的研究項(xiàng)目有了多學(xué)科團(tuán)隊(duì)的參與,開(kāi)啟了利用考古材料詳細(xì)研究人類歷史上重要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轉(zhuǎn)變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導(dǎo)的西亞農(nóng)業(yè)起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爾計(jì)劃、特瓦坎考古學(xué)———植物學(xué)計(jì)劃等。在聚落考古調(diào)查上作出重大貢獻(xiàn)的科學(xué)家是戈登•威利。在維魯河谷計(jì)劃中,他采納斯圖爾特的意見(jiàn),運(yùn)用聚落形態(tài)調(diào)查的方法。然而在對(duì)所收集材料的闡釋上,威利選擇視聚落形態(tài)為一種“對(duì)考古學(xué)文化作出功能闡釋的戰(zhàn)略性起點(diǎn)”,他進(jìn)而宣稱,聚落形態(tài)“反映了自然環(huán)境、經(jīng)營(yíng)者在其中采用的技術(shù)以及由文化所維持的、社會(huì)互動(dòng)和控制的各種機(jī)制”。與斯圖爾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將聚落形態(tài)看作人類行為諸多方面的信息來(lái)源而不僅僅是生態(tài)適應(yīng)方式。威利在維魯河谷的研究成為考古學(xué)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論突破。繼湯姆森三期說(shuō)把考古學(xué)研究的落腳點(diǎn)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擴(kuò)大為遺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圍內(nèi)對(duì)復(fù)雜社會(huì)起源和發(fā)展進(jìn)行深入的區(qū)域調(diào)查。考古學(xué)家逐漸認(rèn)識(shí)到聚落對(duì)研究小型社會(huì)內(nèi)部文化變遷以及對(duì)區(qū)域多樣性和適當(dāng)復(fù)雜性認(rèn)識(shí)的價(jià)值,并被鼓勵(lì)去研究人類行為而非與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相伴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從以上這些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脈絡(luò)中我們可以看出,20世紀(jì)以后的早期功能與過(guò)程理論正試圖通過(guò)內(nèi)部來(lái)了解社會(huì)和文化系統(tǒng),以決定這些系統(tǒng)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guān)聯(lián)、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dòng)的。功能———過(guò)程理論的出現(xiàn),意味著人們的研究視線從之前的歷時(shí)態(tài)轉(zhuǎn)向了同時(shí)性,在這個(gè)階段,人們更關(guān)注系統(tǒng)如何按慣例運(yùn)轉(zhuǎn)而不在意對(duì)主要變遷加以說(shuō)明。考古材料功能與過(guò)程分析方法的發(fā)展,以及20世紀(jì)50年代初威拉德•利比(WillardFrankLibby)建立的放射性碳測(cè)年法導(dǎo)致了考古學(xué)家對(duì)器物排列和交叉測(cè)年的依賴性減小。日顯技窮的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對(duì)民族身份的專攻,被史前文化如何運(yùn)轉(zhuǎn)和變遷的充滿活力的關(guān)注所逐漸取代。這一階段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從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jī)?nèi)容、研究技術(shù)上有了一個(gè)煥然一新的面貌,對(duì)文化解釋的關(guān)注與重視使環(huán)境考古的地位進(jìn)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視生態(tài)學(xué)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論擴(kuò)展了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jī)?nèi)容,高科技手段的發(fā)明則給予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強(qiáng)有力的支持……然而,此時(shí)的柴爾德、泰勒、克拉克等人雖然意識(shí)到了要從內(nèi)部來(lái)解釋文化的變遷,但是卻沒(méi)有提出一個(gè)很好的方法。早期功能過(guò)程階段的考古學(xué)理論仍然依賴于“考古學(xué)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對(duì)考古學(xué)材料和文化過(guò)程的解釋。但我們?nèi)詰?yīng)該看到,早期———功能過(guò)程考古學(xué)對(duì)文化研究興趣的衰退和對(duì)行為研究興趣的增強(qiáng),不僅與其他科學(xué)的發(fā)展趨勢(shì)相一致,也預(yù)示著史前考古學(xué)和環(huán)境考古學(xué)進(jìn)一步變革的到來(lái)。
三、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過(guò)程考古階段(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在沃爾特•泰勒《考古學(xué)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統(tǒng)內(nèi)部變遷的概念在美國(guó)考古學(xué)中達(dá)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這一轉(zhuǎn)變一方面得到了來(lái)自考古學(xué)內(nèi)部特別是生態(tài)學(xué)和聚落形態(tài)研究的發(fā)展的激勵(lì),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強(qiáng)調(diào)文化規(guī)律的新進(jìn)化論人類學(xué)日趨流行的推動(dòng)。20世紀(jì)50年代,一大批美國(guó)考古學(xué)家共同為新考古學(xué)的誕生和發(fā)展建立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榮,這個(gè)時(shí)期美國(guó)社會(huì)的樂(lè)觀與自信反應(yīng)到美國(guó)的人類學(xué)界則表現(xiàn)為對(duì)文化進(jìn)化興趣的復(fù)蘇,和新進(jìn)化理論的重大影響。生態(tài)學(xué)領(lǐng)域長(zhǎng)期性的、方向性的、規(guī)律性的變化理論影響到了美國(guó)人類學(xué)研究,與生物一樣,不同文化對(duì)相似環(huán)境的各種適應(yīng)方式也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特征。20世紀(jì)50年代,人類學(xué)中新進(jìn)化論(neoevolutionism)的兩位主要倡導(dǎo)者是萊斯利•懷特(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圖爾特。懷特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博厄斯學(xué)派主張的“不同文化群體不可以比較”的觀點(diǎn),提出了“一般進(jìn)化”概念,強(qiáng)調(diào)不同文化之間的可比性。斯圖爾特則倡導(dǎo)了強(qiáng)調(diào)生態(tài)適應(yīng)的文化進(jìn)化研究法則。1960年,新進(jìn)化理論在梅格斯(B.J.Meggers)的《作為實(shí)際研究工具的文化進(jìn)化法則》(TheLawofCul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1960)一書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運(yùn)用。梅格斯在書中提出“文化=環(huán)境×技術(shù)”的公式,認(rèn)為考古學(xué)家可以通過(guò)重建史前文化與環(huán)境以基礎(chǔ)推斷其他部分的關(guān)鍵特點(diǎn)。新進(jìn)化論提出的作為文化變遷原因的許多關(guān)鍵變量,包括生計(jì)、聚落形態(tài)、人口變化對(duì)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對(duì)比較容易把握,這一理論對(duì)文化規(guī)律性的認(rèn)定也為后來(lái)新考古學(xué)的主要理論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機(jī)。1959年,約瑟夫•考德威爾(JosephCaldwell)在科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新的美國(guó)考古學(xué)》(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學(xué)轉(zhuǎn)型的主要趨勢(shì),并認(rèn)同之前泰勒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變異無(wú)窮的文化現(xiàn)象和特定歷史狀況的背后是數(shù)量有限的一般性歷史進(jìn)程”。考德威爾認(rèn)為考古學(xué)不應(yīng)該繼續(xù)被看成是各種留存至今的器物類型和特征的總和,文化亦必須作為完整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上整合的系統(tǒng)來(lái)加以分析。考古學(xué)家的主要目標(biāo)必須是從文化進(jìn)程來(lái)解釋考古記錄的變遷。
路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發(fā)展了考德威爾的上述觀點(diǎn),并在美國(guó)年輕一代考古學(xué)家中普及,從而開(kāi)啟了自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lái)被世界公認(rèn)的美國(guó)新考古學(xué)或過(guò)程考古學(xué)的先河。在《作為人類學(xué)的考古學(xué)》(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統(tǒng)學(xué)與文化過(guò)程研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1965)兩篇文章中賓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綱領(lǐng),正式認(rèn)定考古學(xué)的目的與美國(guó)的傳統(tǒng)人類學(xué)一致———是全方位解釋文化行為的異同。賓福德還提議通過(guò)把人類行為與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lái)以達(dá)到這個(gè)目的。解釋被看作對(duì)系統(tǒng)變遷和文化進(jìn)化采取一種通則的形式,在賓福德的設(shè)想中,人類行為有著很強(qiáng)的規(guī)律性,這使在我們解釋社會(huì)的變遷的單一事件和類似變遷的整體事件上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因此他的主要關(guān)注在于說(shuō)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文化這一概念被賓福德視為人類體外的(超肌體的)適應(yīng)手段,只有在人類群體以不同方式適應(yīng)其環(huán)境背景時(shí)才有意義,為此,文化系統(tǒng)所有方面的變化可以從對(duì)自然環(huán)境波動(dòng)、人口壓力變化以及與鄰近文化系統(tǒng)競(jìng)爭(zhēng)的適應(yīng)性調(diào)節(jié)來(lái)解釋,另一方面,文化變遷則是由人類群體對(duì)自然生態(tài)變遷產(chǎn)生的壓力做出理性反應(yīng)的結(jié)果。在新考古學(xué)的理論背景之中,人類能像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樣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對(duì)文化規(guī)范的關(guān)注顯得次要,相比起對(duì)器物類型的特征比較,器物在活體文化系統(tǒng)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為此,以推論或者演繹的方法“驗(yàn)證假說(shuō)”成為了新考古學(xué)主要的研究方法,社會(huì)變遷程序的一般規(guī)律成為了新考古學(xué)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紀(jì)70年代后,為了進(jìn)一步廓清考古學(xué)與民族學(xué)的關(guān)系,賓福德設(shè)法對(duì)考古材料提供的行為解釋參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義,并發(fā)展了中程理論。中程理論關(guān)注從考古材料來(lái)推斷行為,在過(guò)程與他們的結(jié)果之間建立了穩(wěn)定和獨(dú)特的因果關(guān)系。這一方法成為后來(lái)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主要研究方法。另外,在有關(guān)新考古學(xué)的綱領(lǐng)性宣言中,賓福德反復(fù)呼吁用系統(tǒng)論(systemtheory)的方法來(lái)研究文化演變。肯特•弗蘭納利(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學(xué)最著名的系統(tǒng)論倡導(dǎo)者,他強(qiáng)調(diào)的一般系統(tǒng)論從過(guò)程而非歷史的角度研究生態(tài)驅(qū)動(dòng)的文化變遷方法,并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新考古學(xué),將各種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通過(guò)反饋的形式連接起來(lái),避免了單一的解釋。在系統(tǒng)論的背景下,任何一個(gè)模型的基礎(chǔ)都與環(huán)境背景和資源相關(guān)。這樣,環(huán)境考古不再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交叉學(xué)科,而是成為考古學(xu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考古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對(duì)環(huán)境考古概念的定型和體系的建立影響深遠(yuǎn),環(huán)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讀考古材料上的科學(xué)性進(jìn)一步凸顯出來(lái),從前期的一個(gè)輔助性的角色演變成了考古發(fā)掘中需要貫穿始終的必要手段。與此同時(shí),環(huán)境考古范疇大大拓展,并開(kāi)始頻繁地與其他學(xué)科發(fā)生交叉。新理念對(duì)解釋和系統(tǒng)論的強(qiáng)調(diào)促使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方法進(jìn)一步由原來(lái)的靜態(tài)向動(dòng)態(tài)轉(zhuǎn)變。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頁(yè)標(biāo)題#e#
四、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景觀考古學(xué)階段(20世紀(jì)80年代)有意地對(duì)過(guò)程考古學(xué)另辟蹊徑在20世紀(jì)70年代開(kāi)始出現(xiàn)。大約在1985年,伊恩•霍德(IanHodder)將這個(gè)新趨勢(shì)稱之為后過(guò)程考古學(xué)。后過(guò)程主義新理論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學(xué)物質(zhì)文化遺存中的文化、個(gè)體和歷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環(huán)境考古學(xué)領(lǐng)域,則是在后過(guò)程思潮的影響和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環(huán)保主義運(yùn)動(dòng)的催化下產(chǎn)生了景觀考古學(xué)。早在19世紀(jì)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國(guó)CranborneChase地區(qū)的考古工作就已經(jīng)注意到將考古發(fā)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區(qū)域性的復(fù)雜文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背景中考察。而現(xiàn)代景觀考古學(xué)的很多關(guān)注從霍德對(duì)史前歐洲房屋和墓葬與其地理背景關(guān)系的象征性研究發(fā)展起來(lái)。景觀考古學(xué)被看作一種后過(guò)程的、以文化為取向的聚落考古學(xué)。絕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強(qiáng)調(diào),景觀考古學(xué)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其理論基礎(chǔ)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過(guò)程考古學(xué)對(duì)環(huán)境的關(guān)注。景觀考古學(xué)更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人對(duì)環(huán)境的改造和人對(duì)周圍環(huán)境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而不似傳統(tǒng)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一般把環(huán)境作為純自然、靜態(tài)的實(shí)體,僅在研究目的上探討環(huán)境對(duì)人類文化和社會(huì)的影響。景觀不是靜態(tài)的、被動(dòng)的自然物體,而是人為的景觀。隨著人類認(rèn)識(shí)的變化,景觀的含義也發(fā)生變化。景觀考古學(xué)反對(duì)環(huán)境決定論,強(qiáng)調(diào)人與環(huán)境是互動(dòng)的,景觀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受制于人所處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觀考古就是要探討景觀的人文含義。侃普和艾室莫(Knapp&Ashmore)對(duì)景觀考古學(xué)的理論定位在西方較具有代表性。1999年,這兩位學(xué)者聯(lián)合主編了一本景觀考古學(xué)論文集。在為該書所寫的緒言中,侃普和艾室莫從理論上對(duì)景觀和景觀考古學(xué)作了系統(tǒng)論述。其他景觀考古學(xué)的代表人物還有費(fèi)曼(GaryFeiman)、費(fèi)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觀考古學(xué)的研究正方興未艾。這種理論對(duì)新的考古學(xué)研究對(duì)象———“人類過(guò)去物質(zhì)文化遺存的象征意義”的構(gòu)建,實(shí)質(zhì)上是考古學(xué)理論與方法從方法論到本體論的終極性反思。它的出現(xiàn)是環(huán)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過(guò)程論背景下的環(huán)境考古研究仍是環(huán)境考古的主流研究。
五、環(huán)境考古發(fā)展的兩條主線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環(huán)境考古作為一個(gè)交叉學(xué)科研究,是建立在兩條主線之上的,第一條是考古學(xué)理論與方法的發(fā)展,另一條是生態(tài)學(xué)對(duì)環(huán)境考古的推動(dòng)。
叁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發(fā)展簡(jiǎn)史
眾所周知,作為考古學(xué)的一門分支學(xué)科,環(huán)境考古的發(fā)展與考古學(xué)理論和方法的進(jìn)步息息相關(guān)。在中國(guó),雖然近幾十年來(lái)的考古學(xué)研究成就矚目,但由于起步晚、技術(shù)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與國(guó)外還有相當(dāng)大的差距,還停留在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和早期的功能———過(guò)程階段,這也使環(huán)境考古的發(fā)展程度大體僅停留在國(guó)外20世紀(jì)40年代的水平。與國(guó)外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不同,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至今還沒(méi)有發(fā)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可以說(shuō)是一件舶來(lái)品。20世紀(jì)前期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的方法和技術(shù)才開(kāi)始對(duì)中國(guó)的考古產(chǎn)生影響。由于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起步晚,發(fā)展還不充分,不能完全與西方環(huán)境考古發(fā)展的四個(gè)階段相對(duì)應(yīng),在此將其分為兩期:20世紀(jì)20年代———20世紀(jì)80年代的前環(huán)境考古時(shí)期和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的環(huán)境考古初步發(fā)展時(shí)期。考慮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現(xiàn)的研究趨勢(shì),兩個(gè)時(shí)期可以概括為分類———描述階段和功能———過(guò)程階段。
一、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分類———描述階段(20世紀(jì)20~80年代中期)前環(huán)境考古時(shí)期是一個(gè)中國(guó)考古學(xué)從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階段,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則伴隨著考古學(xué)譜系的建立以及與第四紀(jì)地質(zhì)學(xué)的結(jié)合而蓄勢(shì)待發(fā)。在半個(gè)多世紀(jì)的時(shí)間里,先是一批考古學(xué)和地質(zhì)學(xué)的先驅(qū)對(duì)石器時(shí)代文化與古人類的發(fā)現(xiàn)寫下了中國(guó)考古學(xué)的初篇,為環(huán)境考古提供了契機(jī)。20世紀(jì)20年代初,我國(guó)地貌學(xué)與第四紀(jì)地質(zhì)學(xué)的奠基人袁復(fù)禮先生參與仰韶村與西陰村考古發(fā)掘,他將地質(zhì)學(xué)與考古學(xué)很好地結(jié)合起來(lái),開(kāi)啟了中國(guó)新石器考古的初頁(yè),成為我國(guó)地質(zhì)考古的先驅(qū)。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肅史前考古報(bào)告》中難得的把地貌與遺址分布聯(lián)系起來(lái),使遺址的分布與環(huán)境變遷發(fā)生了關(guān)系成為我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的先驅(qū)。20年代左右顧頡剛先生和李四光先生開(kāi)始強(qiáng)調(diào)環(huán)境概念以及環(huán)境對(duì)文化與人生的重要性。這些環(huán)境與人生關(guān)系的科學(xué)論述為中國(guó)后來(lái)普遍接受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鋪墊。隨后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工作,我國(guó)考古學(xué)的類型、地層年代與譜系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第四紀(jì)地質(zhì)學(xué)的建立與走向成熟又為我國(guó)考古學(xué)與地質(zhì)學(xué)結(jié)合而孕育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創(chuàng)造了條件。前環(huán)境考古學(xué)時(shí)期,屬于科學(xué)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并沒(méi)有真正展開(kāi),但在此期間一些考古發(fā)掘中的綜合研究,關(guān)注環(huán)境與人、與人類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思想為后來(lái)環(huán)境考古的展開(kāi)樹(shù)立了榜樣。20世紀(jì)50年代以后碳十四與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進(jìn),則為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紀(jì)40年代以后,舊石器時(shí)代的大量材料被發(fā)現(xiàn),其中包括以元謀人、北京人、山頂洞人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舊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難得的是,對(duì)一些重要的舊石器遺址(廟后山、周口店等)進(jìn)行了地質(zhì)、氣候、植被、動(dòng)物的綜合研究,人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獲得進(jìn)展,舊石器文化演化有了眉目,成績(jī)斐然。這一期間中國(guó)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飛猛進(jìn),在考古地層學(xué)、類型學(xué)、碳十四年代學(xué)的基礎(chǔ)上,各區(qū)域的考古文化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遺址和考古資料的積累,考古學(xué)文化專題的研究被深入推展,包括農(nóng)業(yè)、聚落、生業(yè)方式的問(wèn)題被關(guān)注。20世紀(jì)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學(xué)與相關(guān)學(xué)科滲透,要求重視“物質(zhì)文化與自然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研究為考古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結(jié)合研究指明了道路。孢粉分析法于50年代開(kāi)始在我國(guó)建立,并應(yīng)用到半坡等遺址的發(fā)掘中,這一時(shí)期對(duì)古環(huán)境方法的引進(jìn)還包括沉積物古環(huán)境研究和人類食譜及動(dòng)物食性的研究。人類與生存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越來(lái)越受到重視。1957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設(shè)立了“中國(guó)第四紀(jì)研究委員會(huì)”來(lái)統(tǒng)籌我國(guó)第四紀(jì)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國(guó)第四紀(jì)地質(zhì)學(xué)在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等單位開(kāi)始步入有計(jì)劃的快速發(fā)展時(shí)期。60年代第四紀(jì)孢粉分析和碳十四測(cè)年實(shí)驗(yàn)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國(guó)第四紀(jì)研究實(shí)驗(yàn)的科學(xué)基礎(chǔ)。這個(gè)時(shí)期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礎(chǔ)性的文化分區(qū)、譜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對(duì)于高層次的諸如人地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探討涉及不多,與此同時(shí),該時(shí)期的學(xué)科合流還沒(méi)有形成大趨勢(shì),地質(zhì)學(xué)與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結(jié)合起來(lái),古環(huán)境研究的領(lǐng)域還不夠廣闊,環(huán)境考古的主要研究?jī)?nèi)容還處于對(duì)古環(huán)境的復(fù)原這一初期狀態(tài),考古學(xué)家多傾向于用傳播和遷移解釋文化的變遷。因此這一階段屬于早期的分類———描述階段。#p#分頁(yè)標(biāo)題#e#
二、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功能———過(guò)程階段(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guó)際交流的增加,國(guó)外當(dāng)代考古學(xué)的思想開(kāi)始影響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界。與此同時(shí),生態(tài)學(xué)、地質(zhì)學(xué)等自然科學(xué)和考古學(xué)的合流使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有了新的動(dòng)向。這個(gè)時(shí)候一部分環(huán)境考古工作者對(duì)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方法進(jìn)行了新的探索。環(huán)境考古開(kāi)始不單單停留在對(duì)古環(huán)境的復(fù)原工作之上,演繹、解釋等一套動(dòng)態(tài)的新因素開(kāi)始逐漸見(jiàn)于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開(kāi)始出現(xiàn)功能———過(guò)程甚至過(guò)程考古學(xué)的萌芽。1984年張光直先生應(yīng)邀在北京大學(xué)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講,包括文化生態(tài)學(xué)、聚落考古學(xué)等國(guó)外的早期功能———過(guò)程考古學(xué)思想在國(guó)內(nèi)得到宣傳。1990年,俞偉超先生在《當(dāng)代國(guó)外考古學(xué)理論與方法》一書的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國(guó)的考古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介紹了外國(guó)主流的考古學(xué)理論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論的研究,呼吁中國(guó)考古借鑒國(guó)外的方法。兩位先生嘗試用國(guó)外新的理論方法來(lái)推動(dòng)我國(guó)學(xué)術(shù)演講的努力,深深影響了一批年輕的考古學(xué)工作者。1987年,以侯仁之院士為主任、周昆叔先生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跡保護(hù)委員會(huì)環(huán)境考古分委員會(huì)”在北京市文物事業(yè)管理局的領(lǐng)導(dǎo)和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地質(zhì)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理所的合作下開(kāi)展了上宅遺址與平谷盆地的環(huán)境考古。這次由周昆叔先生提議并完成北京地區(qū)環(huán)境考古研究,將人地關(guān)系的演變作為了研究主題。該考古實(shí)踐證明:動(dòng)態(tài)的解釋在探討史前環(huán)境變化與人類生存空間的轉(zhuǎn)移上,以及從環(huán)境變化,生產(chǎn)的發(fā)展到闡述北京城的興起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實(shí)現(xiàn)了我國(guó)真正意義上的環(huán)境考古研究。
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環(huán)境考古的概念,標(biāo)志著現(xiàn)代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開(kāi)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論文《北京環(huán)境考古》中主要討論了北京地區(qū)30000年來(lái)環(huán)境變遷與古人類活動(dòng)的關(guān)系,將古環(huán)境視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淵由。周先生結(jié)合對(duì)待古環(huán)境與考古學(xué)文化的觀點(diǎn),意味著“環(huán)境”與“考古”自此正式從兩個(gè)獨(dú)立研究的部分走向了交融。這篇文章也被劉東生先生認(rèn)為是中國(guó)第四紀(jì)地質(zhì)與考古文化結(jié)合研究的第一篇論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論文《關(guān)于環(huán)境考古問(wèn)題》中,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任務(wù)是揭示人類及其文化形成的環(huán)境和人類與自然界的相互影響,并力主環(huán)境考古與其他學(xué)科的結(jié)合。作為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據(jù)自身的實(shí)踐,并結(jié)合中外學(xué)者的理論研究提出了一種可稱為“考古地理”的環(huán)境考古研究模式,在該模式下,環(huán)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環(huán)境演變規(guī)律,其次是認(rèn)識(shí)環(huán)境演變所引起的地質(zhì)地貌變化導(dǎo)致人類生活場(chǎng)所的變更,以及人類與文化的關(guān)系,環(huán)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學(xué)和歷史地理學(xué)特征。2004年,湯卓煒先生在《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一書中系統(tǒng)地論述了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基本理論問(wèn)題、研究方法,并對(duì)一些專題進(jìn)行了論述。他將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定義為:根據(jù)反映古人類生活時(shí)期的環(huán)境信息、資料及實(shí)物,利用環(huán)境學(xué)的理論方法和技術(shù),研究古代人類的環(huán)境特征及演變規(guī)律,進(jìn)一步弄清環(huán)境與人類及其文化特征、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生業(yè)模式的發(fā)展和演替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的一門學(xué)科。湯先生在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構(gòu)架了一套以“資源”為中心的環(huán)境考古研究模式,并從人類活動(dòng)與環(huán)境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出發(fā),積極地運(yùn)用環(huán)境學(xué)理論進(jìn)行環(huán)境考古解釋。湯卓煒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與西方研究接軌的積極嘗試,標(biāo)志著以遺址為中心、以資源獲取為切入點(diǎn)、以環(huán)境學(xué)理論為闡釋工具的多層次環(huán)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陳勝前先生從美國(guó)博士畢業(yè)回國(guó)后,從兩個(gè)角度開(kāi)展了考古學(xué)解釋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態(tài)學(xué)背景下的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起源的探索,二是在以遺址形成過(guò)程基礎(chǔ)上對(duì)考古遺存的功能的探討。這兩個(gè)角度均考慮到了環(huán)境變遷對(duì)考古遺存和文化變化的解釋。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從對(duì)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問(wèn)題,從問(wèn)題出發(fā)進(jìn)而綜合利用各學(xué)科的理論與方法對(duì)考古材料進(jìn)行解釋,為包括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在內(nèi)中國(guó)考古學(xué)找到了一條嶄新的研究路線。他繼承了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將文化作為適應(yīng)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人們共同體的遺存組合,這就為探索人類活動(dòng)和環(huán)境背景的關(guān)系找到了一個(gè)合適的切入點(diǎn)。之后其他學(xué)者也借鑒了這條思路,將動(dòng)物利用與生業(yè)方式相聯(lián)系,利用相關(guān)材料來(lái)形成一個(gè)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于分類和描述。
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的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受到外國(guó)新思想和多學(xué)科合流趨勢(shì)的影響,出現(xiàn)了多種對(duì)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學(xué)者的實(shí)踐、引進(jìn)與創(chuàng)新使得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界迎來(lái)了百花齊放的新時(shí)期。在傳統(tǒng)的文化———歷史學(xué)的研究方法以外,我們亦能看到早期功能———過(guò)程甚至過(guò)程主義研究的影子。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研究方向也隨著研究方法的變化產(chǎn)生了包括:人地關(guān)系問(wèn)題、遺址域研究的引進(jìn)、物種馴化與農(nóng)業(yè)起源、文明起源的關(guān)系的探索、考古遺址的解釋、文化生態(tài)學(xué)等在內(nèi)的幾個(gè)新的主題。與此同時(shí),隨著跨學(xué)科合作趨勢(shì)的加強(qiáng),DNA、食譜分析、鍶同位素、GIS環(huán)境考古等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應(yīng)用到環(huán)境考古中來(lái)。與國(guó)際接軌、應(yīng)用科學(xué)科技和跨學(xué)科合作似乎已成為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未來(lái)發(fā)展的幾大趨勢(shì)。然而,我們還應(yīng)該看到,當(dāng)前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主流研究與上世紀(jì)四五十年代的歐美一樣,是以考古學(xué)文化的概念為中心的。從研究理論與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大體上仍處于分類———描述階段。雖然也已經(jīng)有一小部分關(guān)于家畜起源、農(nóng)業(yè)起源、社會(huì)復(fù)雜化、文明產(chǎn)生等高層次考古學(xué)問(wèn)題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角度的探討,但畢竟不占主流。整體來(lái)看,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還沒(méi)有真正進(jìn)入到過(guò)程主義及后過(guò)程主義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下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范疇,我們的研究多以“客位”的視角看問(wèn)題,并缺乏主動(dòng)的解釋。所以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現(xiàn)在處于初步發(fā)展時(shí)期。
肆發(fā)展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
上世紀(jì)20年代初到現(xiàn)在這近100年的時(shí)間里,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從最初單純的記敘環(huán)境到科學(xué)時(shí)代對(duì)人地關(guān)系的實(shí)驗(yàn)求證再到今天在多學(xué)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釋人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嘗試……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已逐漸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嶄新的道路上成長(zhǎng)著。然而,由于作為科學(xué)的環(huán)境考古是從外國(guó)引進(jìn)到中國(guó)的,時(shí)間上與空間上的差異和長(zhǎng)期的封閉發(fā)展導(dǎo)致了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起點(diǎn)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與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一樣,在自身的理論建設(shè)上走一條自成體系的道路。俞偉超先生提出,在過(guò)去的30~40年的時(shí)間里,我國(guó)的考古學(xué)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國(guó)各地區(qū)考古學(xué)文化譜系這一基礎(chǔ)性的建設(shè)上面,這樣,盡管近40年來(lái)的中國(guó)考古學(xué)研究其目標(biāo)已達(dá)到歐美第三階段的水平,具體階段還是走在第二階段的道路上。豐富的研究材料與相對(duì)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間的矛盾是造成我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達(dá)不到國(guó)際先進(jìn)水平現(xiàn)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對(duì)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學(xué)材料來(lái)說(shuō),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一切都說(shuō)明,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需要改革,實(shí)現(xiàn)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大繁榮和大發(fā)展任重而道遠(yuǎn)。#p#分頁(yè)標(biāo)題#e#
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隨著多學(xué)科的合流和外國(guó)先進(jìn)理論的引進(jìn),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界才出現(xiàn)了許多對(duì)于功能———過(guò)程方法論甚至是過(guò)程論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傳統(tǒng)方法與新理論的博弈、各種新理論之間的交流,使得新時(shí)期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界呈現(xiàn)出許多種不同的面貌,為環(huán)境考古未來(lái)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選擇;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環(huán)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還處于探索階段的嘗試,并沒(méi)有形成國(guó)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之,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處于一個(gè)重要的方法論轉(zhuǎn)型時(shí)期,傳統(tǒng)研究模式目前仍主導(dǎo)著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導(dǎo)思想正在孕育和萌發(fā)之中。理論是科學(xué)研究的基石,它不僅左右一門學(xué)科的探索方向,而且也涉及一門學(xué)科中的方法論設(shè)計(jì)和分析結(jié)果的詮釋。而研究方法論的轉(zhuǎn)變是一個(gè)學(xué)科的研究進(jìn)入一個(gè)更高層次的、全新時(shí)期的標(biāo)志,它不僅能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學(xué)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賦予研究者更為廣闊和更有深度的視野,是研究工作進(jìn)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的發(fā)展軌跡中,這樣的轉(zhuǎn)型在上世紀(jì)40年代和60年代左右經(jīng)歷過(guò)兩次,分別是從分類———描述階段過(guò)渡到功能———過(guò)程階段以及從功能———過(guò)程過(guò)渡到過(guò)程考古階段。根據(jù)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發(fā)展的軌跡,再結(jié)合當(dāng)今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界出現(xiàn)的趨勢(shì),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作為科學(xué)的、解釋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將是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發(fā)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國(guó)外理論的影響下成長(zhǎng),我們完全可以直接借鑒國(guó)外最先進(jìn)的理念來(lái)設(shè)計(jì)自己發(fā)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過(guò)程考古學(xué)理論有一定發(fā)展但尚未發(fā)展到外國(guó)五十年代水準(zhǔn)的程度上對(duì)新考古學(xué)的中程理論進(jìn)行嘗試,從而少走彎路,實(shí)現(xiàn)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論上的跨越。要實(shí)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文化歷史考古學(xué)上的超越,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需要從以下四個(gè)方面進(jìn)行完善和改革。
一、概念體系的轉(zhuǎn)變?cè)趥鹘y(tǒng)的分類描述乃至功能過(guò)程的環(huán)境考古研究模式中,對(duì)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學(xué)文化”的概念體系下進(jìn)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認(rèn)為: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是由一個(gè)特定的考古學(xué)文化的考古遺存部分和作為這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環(huán)境的遺存部分組成的,進(jìn)而,他們很容易將考古學(xué)文化作為整體或其分區(qū)與環(huán)境背景進(jìn)行對(duì)接,以探求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最終陷入環(huán)境決定論和可能論,將環(huán)境、人類活動(dòng)與文化三者之間確切關(guān)系簡(jiǎn)單化。我們需要認(rèn)識(shí)到:傳統(tǒng)的“考古學(xué)文化”表示有時(shí)空特征組合的遺存組合,代表一定的“人們共同體”。在這一體系下,遺存,主要是文化遺存,被視為是可以反映“考古學(xué)文化”所代表的人們共同體的發(fā)展脈絡(luò)的,因而可以區(qū)別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態(tài)學(xué)背景下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的“文化”卻與傳統(tǒng)的“考古學(xué)文化”有著本質(zhì)上的不同。在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假設(shè)中,人是適應(yīng)和改造自然環(huán)境的,并且遺存(主要是自然遺存,其中包括純自然遺存,也包括經(jīng)過(guò)人類活動(dòng)這一文化篩篩過(guò)的“自然”遺存)可以反映出人對(duì)自然資源的利用和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所以,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類共同體的發(fā)展脈絡(luò),而是一種人類對(duì)于環(huán)境做出的適應(yīng)性的手段(這一點(diǎn)與新考古學(xué)的理論直接相關(guān))。傳統(tǒng)特定人們共同體文化的變遷即考古學(xué)文化的變遷不一定歸因于環(huán)境的變遷,反過(guò)來(lái),環(huán)境的變遷與考古學(xué)文化的變遷也沒(méi)有直接的相關(guān)性。所以,作為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文化并非是傳統(tǒng)意義上用以區(qū)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學(xué)文化”而是一種在人類群體以不同方式適應(yīng)其環(huán)境背景時(shí)才會(huì)產(chǎn)生的動(dòng)態(tài)的“文化”。明確了文化的概念,環(huán)境考古研究的對(duì)象則也需要發(fā)生轉(zhuǎn)變。首先,我們的研究不能再以一個(gè)文化區(qū)為中心,而應(yīng)該收縮到一個(gè)聚落或者一個(gè)遺址的范圍。因?yàn)橹饕鶕?jù)器物特點(diǎn)劃分出的傳統(tǒng)文化區(qū)的面積一般非常廣闊,內(nèi)部環(huán)境異常復(fù)雜,在同一個(gè)文化區(qū)內(nèi)產(chǎn)生一致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中的適應(yīng)性“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個(gè)聚落或者一個(gè)遺址內(nèi),相對(duì)單純環(huán)境條件則為環(huán)境考古進(jìn)行人地關(guān)系分析和文化變遷研究提供了可能。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對(duì)象不應(yīng)該是主要根據(jù)遺物進(jìn)行區(qū)分的文化區(qū),而是主要根據(jù)遺跡區(qū)分出的聚落或者遺址,相應(yīng)地,環(huán)境考古的分析單位則應(yīng)該從遺物向遺跡上轉(zhuǎn)變。
二、中心問(wèn)題的轉(zhuǎn)變?cè)谥袊?guó)考古學(xué)文化譜系基礎(chǔ)性建設(shè)基本完成,高科技的斷代測(cè)年手段不斷發(fā)展以及環(huán)境考古研究重視聚落遺址而淡化文化區(qū)概念的背景下,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中心問(wèn)題也面臨著從傳統(tǒng)的分期、排隊(duì)和劃分類型到對(duì)考古現(xiàn)象進(jìn)行分析與解釋的轉(zhuǎn)化。中心問(wèn)題的轉(zhuǎn)變,要求考古學(xué)家在傳統(tǒng)的對(duì)于考古材料外觀、質(zhì)地、年代和演變等比較表面化的認(rèn)識(shí)上做出進(jìn)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學(xué)家將材料和環(huán)境聯(lián)系起來(lái),以嚴(yán)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xué)的方法為手段,在充分考慮到人類能動(dòng)性的基礎(chǔ)上解釋考古材料與現(xiàn)象。這個(gè)轉(zhuǎn)變,如俞偉超先生所說(shuō),實(shí)質(zhì)上是為達(dá)到探明歷史文化進(jìn)步規(guī)律這個(gè)最高目標(biāo)而建立中間環(huán)節(jié)的理論。環(huán)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從傳統(tǒng)的歷史唯物概念的直接解釋中跳出,許多現(xiàn)象是過(guò)渡不到普遍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shí)上去的,那么我們對(duì)于過(guò)去的認(rèn)識(shí),將停留在靜態(tài)的文化區(qū)劃分上而止步不前,對(duì)于人地關(guān)系問(wèn)題、物種馴化與農(nóng)業(yè)起源、文明起源的關(guān)系的探索、考古遺址的解釋、文化生態(tài)學(xué)等等問(wèn)題的研究都將成為一紙空談,與此同時(shí),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將沒(méi)有辦法轉(zhuǎn)化為其他學(xué)科可以利用和社會(huì)公眾可以理解的知識(shí)。所以我們需要對(duì)環(huán)境考古研究的中心問(wèn)題進(jìn)行轉(zhuǎn)變,以獲得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鮮活的、發(fā)展的歷史。
三、研究方法的轉(zhuǎn)變理論與研究目標(biāo)的轉(zhuǎn)變相應(yīng)的需要一套與之配套的研究方法。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基本圍繞材料而做,因材料而做,使得許多材料的豐富內(nèi)涵沒(méi)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時(shí)影響了研究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價(jià)值不高的局面,阻礙了我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基于新考古學(xué)理論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應(yīng)該完成從以材料為中心到以問(wèn)題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轉(zhuǎn)變。我們應(yīng)該意識(shí)到,提出問(wèn)題比解決問(wèn)題有著更大的價(jià)值,比起圍繞材料進(jìn)行分析的傳統(tǒng)做法,以推論或者演繹的方法“驗(yàn)證假說(shuō)”將給未來(lái)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研究帶來(lái)更多的課題,同時(shí)也帶來(lái)更旺盛的生命力,為我們探索社會(huì)變遷程序的一般規(guī)律提供更加科學(xué)的支持。另外,新時(shí)期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還應(yīng)該擺脫傳統(tǒng)上孤立的考古學(xué)發(fā)展的模式。在當(dāng)今學(xué)科合流,邊緣交叉學(xué)科不斷涌現(xiàn)的背景下,多學(xué)科的合作已經(jīng)成為不可逆的大趨勢(shì)。環(huán)境考古與生物、地質(zhì)、化學(xué)、民族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學(xué)科的融合與交流勢(shì)必將給環(huán)境考古帶來(lái)更廣闊的學(xué)科視野,給予環(huán)境考古研究課題的提出與解釋更加強(qiáng)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撐。#p#分頁(yè)標(biāo)題#e#
四、走自己的路從上世紀(jì)20年代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萌芽以來(lái),我們就一直在基于國(guó)外發(fā)展的前提下發(fā)展,環(huán)境考古作為一件舶來(lái)品,受到外國(guó)的理論、方法、技術(shù)各方面的影響與制約。國(guó)外的先進(jìn)理念與技術(shù)無(wú)疑為我國(guó)環(huán)境考古的快速發(fā)展帶來(lái)了極大的機(jī)遇,然而,我們還應(yīng)該意識(shí)到地域與文化性差異的存在。國(guó)外的先進(jìn)理論都是在基于國(guó)外大環(huán)境的背景下循序漸進(jìn)地產(chǎn)生的,它們深深依托于自己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論固然先進(jìn),用于我國(guó)也不一定適用。所以,在借鑒外國(guó)的理論與技術(shù)(尤其是理論)時(shí),我們不能全盤照搬,全盤模仿,也應(yīng)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我國(guó)環(huán)境考古指導(dǎo)思想的發(fā)展就無(wú)需照搬國(guó)外逐步進(jìn)行從文化歷史時(shí)期、功能———過(guò)程到過(guò)程考古的過(guò)渡,而可以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將后兩個(gè)理論階段一起發(fā)展,實(shí)現(xiàn)理論上跨越式的進(jìn)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學(xué)理論發(fā)展起來(lái)的現(xiàn)代環(huán)境考古學(xué)也不必拘泥與新考古學(xué)的全部理論,還應(yīng)該認(rèn)識(shí)到新考古學(xué)理論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在重視研究方法科學(xué)性的同時(shí)也應(yīng)該意識(shí)到歷史學(xué)的價(jià)值,正視考古學(xué)在了解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和對(duì)考古材料進(jìn)行歸納和總結(jié)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識(shí)到人類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和人類自身的能動(dòng)性,對(duì)考古學(xué)家的釋讀能力和考古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個(gè)客觀合理的認(rèn)識(shí)。最后,我們還應(yīng)該在不斷地實(shí)踐中形成一套適用于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理論,走出有自己特色的發(fā)展道路。
伍結(jié)論
本文從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以學(xué)科研究理論的變遷為標(biāo)準(zhǔn),將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分為了分類—描述、早期功能—過(guò)程、過(guò)程考古和景觀考古學(xué)四個(gè)階段,詳細(xì)考察了外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從產(chǎn)生到成熟的發(fā)展脈絡(luò)。隨后,作者對(duì)比了中外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把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史分為分類———描述和功能———過(guò)程階段兩期,提出了“中國(guó)的環(huán)境考古學(xué)無(wú)論從理論還是從實(shí)踐上都有加以改革的必要,以加強(qiáng)它的科學(xué)性”的觀點(diǎn),同時(shí)將新考古學(xué)理論看作未來(lái)中國(guó)作為科學(xué)的、解釋的考古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一大歸宿。在全面認(rèn)識(shí)國(guó)外環(huán)境考古發(fā)展歷程以及國(guó)內(nèi)環(huán)境考古的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shì)后,作者認(rèn)為,當(dāng)前的中國(guó)環(huán)境考古學(xué)處于一個(gè)重要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如何在這個(gè)時(shí)期實(shí)現(xiàn)從理論、方法到研究成果上更大的突破則很大程度上依仗于概念體系、中心問(wèn)題、研究方法的轉(zhuǎn)變以及對(duì)自身道路的科學(xué)規(guī)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