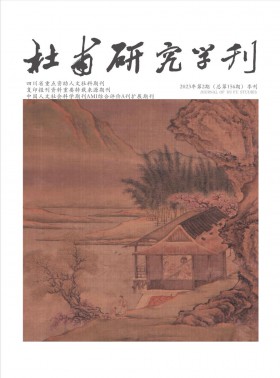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杜甫詩歌的自然寫作,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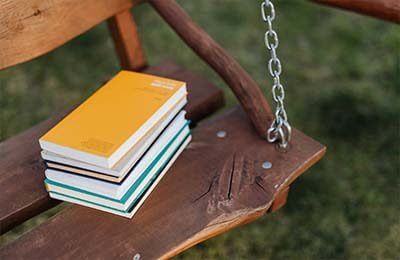
夔州,即今重慶市奉節縣,自古以來是由三峽出入蜀地的必經之地。歷代詩人在夔州留下了多達4484首詩作。其中,杜甫存詩437首[1],從質和量上都可看作歷代夔州詩的巔峰,《秋興八首》《登高》《詠懷古跡五首》等作品更可謂是千古絕唱。 杜甫詩歌中的自然寫作(自然寫作是生態批評最主要的研究對象)始終與道德、政治等嚴肅命題相關聯,體現出與“神韻”山水不同的“風骨”傾向。其中“風”為深沉的道德力量,而“骨”為純粹的審美訴求。旅居夔州后,這一傾向與當地強悍、蠻荒的生態碰撞、耦合,激發出對逆旅、放逐、歸零一類主題的反復考量、書寫。將“介入”的現實性和自然的超功利性統一于詩歌,這是夔州詩之所以“跌宕奇古,自創一格”的原因,也是杜甫對山水詩境的開拓。本文聯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態意義和環境效力,以“山水”為中心來考察杜甫夔州詩中的自然寫作,從而揭示出杜甫夔州詩作“夔州風骨”的內涵和成因。 一、現地視角 在杜甫詩歌研究中,“夔州詩”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學現象,成為文學史上的專名,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于杜甫的夔州詩體現出了強烈的“現地感”。所謂“現地感”即指詩人大量表現當地的特殊景物和地方文化,在自然描寫中構建獨特的“家園宇宙”[2]10。一方面,詩人創造出具有當地特色的意義空間和想象空間;另一方面這種現地感又成為在應對環境“粗糙冷漠”一面的過程中,詩人處理自身位置的反應機制。 不同于王孟山水詩,夔州詩中的自然寫作沒有試圖于本地風物和日常生活外找尋超越性的境界。因而與王維對“辛夷塢”等現地物象所作的泛化和虛化相反,杜甫將夔州的地方風格進行了有意識的強化。杜甫由云安入夔州為大歷元年春晚,時55歲;去夔出川時距離去世僅有2年。可見詩人流寓峽江的時期正值人生晚秋,遭受著身體衰落和心情郁結的雙重折磨。這樣的人生狀態恰好與夔州奇峭險峻的地理風貌和山水品格相契合,使詩人的心境在夔州山水間得以投射。由此,自踏上夔州的江岸起,詩人筆下就呈現出一個奇峭、冷峻、動蕩的江山圖景。如杜甫進入夔州所做的第一首詩《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前期“春色醉仙桃”“紅綻雨肥梅”的春景被飄搖黯淡的峽谷之景所取代。“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曲江對雨》)的清新和“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秦州雜詩二十首》)的平靜變成了“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江梅》)、“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愁》)的動蕩和蕭瑟。這種完全夔州化的自然寫作印證了詩人所謂的“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的詩學主張。通過將景物極大地現地化、具體化,詩人依靠突出峽江特色營造出“吞幾云夢”的審美體驗,也借助物象本身的文化意涵和歷史記憶使詩歌具有“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的意義空間。 首先,杜甫夔州詩的現地視角體現在異常鮮明的地形特征和物種特征上。夔州詩中,以“江”字實指江景的多達167首,提到“山”或“峽”的也超過百首,排除懷人詠古之作,幾乎每一首詩歌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峽江風光進行了描寫和表現;即使對象是尋常之物,詩人也冠之以“江”“峽”等字眼。如: 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天邊常作客,老去一沾巾。(《江月》)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秋興•其三》) 在對其他物象的處理上,杜甫抓住了夔州季節和物產的地方特征加以表現,如酷暑驚雷,白小黃魚:峽中都是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熱三首》) 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解悶十二首》) 同時,詩人這一時期詩歌中尤其偏愛“晚秋”“猿啼”“白雁”等物象,從而利用其當地特征構建起巨大的話語力量和想象空間,在寥寥數語之間營構起值得反復玩味揣摩的意境。如: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九日五首》)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 這2首曠世佳作被譽為“如海底珊瑚,瘦勁難移,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仇注)其中的景物描寫不僅呼應了中國文學深遠的“悲秋”傳統,也借助愁猿啼淚中包含的斷腸之悲的聯想,為流亡和放逐的沉重主題找到詩意化的表達方式。 其次,對于地域特征尚不夠明確的物象,詩人通過對舉或添加形容、描述的方式將其進一步實景化和意象化,既突出地方特色,又訴諸文化背景豐富詩歌的意涵和境界。例如,在提到“城”或“樓”時候,杜甫多冠之以“孤”“危”“高”等形容詞,以此呼應歷史中先主托孤,英雄遲暮的悲劇內涵,抒發孤獨、緊張的情緒: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向夕》)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游。(《白帝城樓》) 而凡涉及“云”“雨”等物象時,詩人則往往將二者對舉,暗示以高唐神女、隔水伊人的傳說,以“空幻”之美隱喻浪跡江湖的人生客夢。如:#p#分頁標題#e# 片片水上云,蕭蕭沙中雨。(《雨二首》) 樓雨沾云幔,山寒著水城。(《西閣雨望》) 再次,杜甫在詩歌中集中地使用了大量地名:白帝城、永安宮、八陣圖、昭君村、赤甲山、明月峽、楚王陽臺等,從表象層面的風景深入到地方景物背后的文化語境。如杜甫的名篇《詠懷古跡五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里,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通過地名的應用,景物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在作者和讀者的知識背景中找到了回應,從而在物象背后建構起一層新的意義空間,為文字賦予多重意境的架構。例如,“白帝城”通過呼應公孫稱帝和蜀主托孤的歷史事件隱含對功業虛妄性的反思;“陽臺楚宮”則通過與當地云霧繚繞的氣候特征相聯系,喚起對宋玉才情的追慕和對理想幻滅的感嘆。 在作者看來,任何地方物象都包含獨特的文化價值:一方面能夠與典故、傳說相呼應;另一方面則可以由族裔、習俗折射出詩人的立場。通過現地化的景物描寫和具體化的地名指示,詩歌中呈現出一個粗糙冷漠而又深刻沉重的“邊地”。在巨量山川形成的狹窄空間里,黯淡、幽閉的風景造成一種緊張壓抑的外部氣氛;而歷史和文學中悲劇性的事件、記憶又不斷喚起詩人傷感、郁結的情緒,因而親切閑適的田園,疏淡開闊的塞外和明媚婉約的庭院這些山水詩的傳統主題都從詩人筆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幽深峻峭的高山峽谷和神秘野性的村莊人群。 從專注地域景物出發,夔州異己性的環境因素在夔州詩中被詩人轉化為了具有特殊生態意義和文化價值的符號。物象的現地化既是詩人與過去文化傳統的系連,又是他與異己力量保持距離的自我保護姿態。這種現地視角的詩意表達運用一種極其溫柔的支配力量,并非對異己性的他者加以把握和征服,而是為其施洗。在荒野中,詩人通過自然寫作將環境引入了詩歌的視野,突破了“獨抒性靈”的桎梏,將冷峻粗糲的物象以一種非人本主義的方式感化,從而渾然無跡地納入詩意的建構。 二、環境自覺 在現地視角建構起的環境空間中,作者對山水的基本態度也凸現出來。在杜甫看來,山水始終作為人的對應物存在,不能被主體簡單地同化或精神化。這決定了杜甫是在以主體為核心的層面上實現對環境的發現的。詩人不是消解,而是“俯視”自然中的異己性因素,返回到生命和文明中去尋找精神的立場,在“無情”的環境中加入自己的靈魂反思和道德關懷。 這種對生命的寬容和尊重,以及對孤獨的承受和認同,貫穿于杜甫一生的詩歌創作,而在夔州詩中,這種物我關系的把握更演變成一種深刻的“環境自覺”。 引發這一自覺的原因之一在于夔州特殊的地域特征。據道光夔州府志(卷十六)記載:“夔在蜀為大郡,與荊襄漢沔相接壤,江山相屬,地廣民稀,然其俗尤為近古。”這一邊地是異質文化交融、過渡的空間,它所具有的生命力量和原始邏輯構成了文明的對立面,是一個具有投射和選擇能力的系統,不斷進行著適應與創制,交流與生存的活動。蠻荒的山水不懂人的參照系,對人最深層的文化規范也不會有任何關心,它只是瞬息萬變,說著難以理解的數十億年的遺傳語言。因此詩人在此意識到的是偶然的恒常性,經受到的是強大的時空對人類規則反復地破壞、僭越。這一經驗使夔州詩中的環境自覺具有以下2個特點: 第一,環境自覺不能使詩人通過“妙悟”或“澄懷”以達到“清靜”“淡遠”。因而,產生于環境自覺的詩歌并非處于“無我之境”的維度,而是處于“有我之境”的維度。 由于夔州詩自然寫作的對象是粗糙冷漠的邊地山水,而詩人又是牢牢立足于腳下的土地,以現地視角呈現山水,這一機制便決定了夔州詩中精神和自然一直處于相互打壓和安慰的狀態,不能簡單地消弭主客體之間的界限,達到“舍筏登岸”的物我兩忘。因此,杜甫夔州詩中的自然寫作并非“禪悅山水”或“玄對山水”。詩人不是一個“觀光客”,而是一個在命運的規劃下“進入”此地并在山水中找到靈魂安放之所的抒情主角。例如杜甫的《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疏燈自照孤帆宿,新月尤懸雙杵鳴。(《夜》) 與類似主題的《滁州西澗》等詩歌相比,杜甫的自然寫作不是山水本身的審美化,而是道德主題的詩意化。詩人拒絕通過排除“人”的氣息和對時光的省略與漠視來掩蓋和彌合此者與他者之間的矛盾及差異,而是始終堅持在山水之外體現人的存在性。因此杜甫的夔州詩保持了完整的時空感,避免了以內在超越的方式將自然徹底地對象化。在這里,自然寫作被用作為一種在安全掩護下追求更加敏感的主題的方法,山水成為了文學的闡釋對象。文字與外物之間建立于視覺觀察和心靈感悟上的直接關系發生了偏移,加入了詩人可塑的精神結構。這使得夔州詩中的山水呈現出雙重的認識論身份,既可由之體驗自然的效力,又可順其領悟詩人的內心。 杜甫寫于夔州的《秋興八首》鮮明地體現出復雜而敏感的道德反思如何在山水的參與下以一種含蓄深沉的方式體現于詩歌。如: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興•其一》) 詩中杜甫將自己與“故園”的系連放置于山水對個體生命強勢的合圍中。“孤舟一系”的脆弱和生命的遲暮與“兼天涌”“接地陰”的壓倒性力量構成了讓人震撼的對比。此者與他者,生命與時光之間的相互衡量、耦合的復雜關系使人與山水的際遇不再是“消遣”的體驗,而是“再造”的體驗,產生的不是“默然相對”,而是一場辯論和撞擊:雙方藉由此達成對真理、價值標準、知識體系等主題新的認定和默契。在杜甫的夔州詩中,自然因素成為了心靈銳感和痛感的表意形式。#p#分頁標題#e# 第二,與神韻派山水詩“獨語”的傾向不同,邊地山水使杜甫反思過去承擔的道德責任和文化使命,近距離審視自然和人性。因而,詩人在自然寫作中打破了內向、封閉的自語狀態,“矛盾”的對話成為詩歌的主題,主客體間形成了一種外向性和發散性的變形交流。 這種矛盾的對話機制使杜甫的夔州詩呈現出“荒野詩歌”的特質:并非單一的觀看,而是在山水背后反復考量被壓縮、逼迫、阻礙的精神狀態,以純粹的自然觀照呈現命運的難題和心靈的力量[2]11。 對于杜甫這一時期的詩歌而言,最為突出的矛盾是出世與遁世的選擇和沖突,是溷身山水的心靈自救和介入世事的仕宦激情之間的斗爭和妥協。如: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蓮房墮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秋興•其七》) 從深處探究,詩中無疑表達了對于“秦中自古帝王洲”的呼應和思念,流露出身阻鳥道,還京無期的傷悼。但同時詩人通過以漁翁為自比,也傳達出對王居之地繁華生活的漠視和對昔日歡游的規避。從“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天地滄浪一釣舟”“獨把釣竿終遠去”這些詩句中,杜甫對冠蓋相交,歡宴終日的無謂生活表達了含蓄而深刻的懷疑。 這種那個漂泊異鄉的放逐被棄之感和對寄身之地的依賴眷戀在杜甫的山水描寫中構成了一種“充滿急迫感的美學”,“來源于互補的多重欲望的糾纏”。這正是環境自覺對矛盾主題的表達方式。夔州詩的自然寫作背后,是被2種強烈而對立的欲望撕扯著的作者[3]。而詩歌深沉的內涵和復雜的情感正脫胎于那種受著折磨的,試圖去調和二者的心靈。詩人不能毫無阻礙地將風景用作表情的工具,無法停留于對風景的流連,只能以邊地山水作為潤滑劑不斷磨合自我與他者,考量生命的矛盾,找尋人生的命意,反復呈現溷身“江湖”的自誓和自傷這一人生悖論。 落落盤據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古柏行》) 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鷗》) 詩人的自比透露出詩人正是力圖通過自然寫作展現棲居于世間的種種可能,讓品味生活和拯救生活的雙重沖動在凌厲的意象、純凈的韻味之中得到一種略帶悲劇性的詩意表達。在山水外物的參與下,杜甫復雜、隱晦地表達了在“高峰寒上日”“郊扉冷未開”的環境打壓下綺夢成塵的惆悵和“落落欲往”的孤憤。“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和“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的人生困境以詩化的方式闡釋了出世與介入、漂泊與還鄉的中心主題,成為了杜甫山水詩開掘詩境的突出表現。 三、荒野審美 杜甫夔州詩中的現地視角和矛盾主題沒有使詩歌狹窄、板滯、直白。其原因在于詩人既俯身于腳下的土地,又將目光投向天際,用“荒野審美”的眼光審視環境。荒野”具有粗糙、神秘、完整和失衡的力量感,“它是一種狀態,關于我們對令人哀傷的情景的洞察”[4]。對于寫作山水的詩人來說,正是荒野充分的“異己性”吸引并愉悅了他們,使他們把解放自己的理性作為反應方式,描述觀念還未形成或確定時的體驗。 “蠻歌犯星起,空覺在天邊”(《夜二首》),這句話可謂此種荒野審美的形象表達。杜甫將蠻荒的山水和野性的民風轉化成詩意的構件,在實地描寫外構建起“興寄無端”的想象空間,既消除了現地視角可能引發的過度寫實化,也避免了沉重的文化意蘊和道德力量傷害詩歌含蓄的美感。憑借開闊的想象維度和成功的語言探索,杜甫突破了高山峽谷壓縮下幽閉的視野,在詩歌中“得千匯萬狀之美”,體現出“想象的陶醉”和純粹的審美訴求。具體而言,這種以地域為中心的荒野審美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 其一,杜甫以異鄉人的身份,不僅試圖觀察、體驗、理解邊地原住民的生活狀態,也從“輕易滛泆,柔弱褊阸”的邊地風氣中突破想象的邊界。“形勝有余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峽中覽物》),當詩人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現在意想不到、難以理解的社會關系中時,平衡中庸的立身哲學被“疏”“怪”一類傾斜感所破壞,而詩人自身也不斷被異質性的“生態群落”改造、影響。在這一過程中,杜甫幾乎檢視了當地原住民“夔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畬田而耕、暴尫瓦卜、男坐女立、人日踏蹟等。如: 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負薪行》) 從這些對異族嚴肅而略帶好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詩人一方面隱含著士大夫文人所代表的儒教文明曖昧而根深蒂固的邏輯,另一方面在他身上也進行著的習俗、異教、方言以及其他偏見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5]當強大的異己力量和未知事物造成了安全感的喪失,人的機械運動被限制在狹小的區域時,夔州凄美的傳說和神秘的信仰卻為詩人內心久已失落的浪漫招魂。詩人對自身性靈的自珍、自憐與當地強悍野性的生命沖動結合,形成了詩歌中飛身超越的遠游情懷: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閣夜》) 夜半歸來沖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夜歸》)#p#分頁標題#e# 伴隨著“野哭”“夷歌”“猿啼”,是詩人一輪輪生命的游歷。詩人將“故園”作為永恒的思念對象,反復以星光、水影等自然景物書寫對它的迷情。“孤槎自客星”(《宿白沙驛》)在動彈不得的羈旅中,詩人卻向天際的誘惑讓步。夔州封閉的環境讓詩人愈加深刻地認識到自身狀態的停滯不前,生命一次次歸零,“故園”這一幻象卻無法靠近,只能從山水景物上尋找和期待著某種無望的回歸。這種復雜深沉的情感通過放縱奇詭的想象排除了散文化,平面化的危險,極大增強了詩歌的容量和深度。 其二,夔州詩中獨特的物象和奇崛的聲律句法體現出“卒音激訐,含思宛轉”[6]147的荒野特色,反映了詩人對“南音巴曲”有意識的模擬,這正是詩人出自單純的審美動機,對“邊地”之美的刻意營造。“吹笛秋山風月情,誰家巧作斷腸聲?”(《吹笛》),歷代評詩家認為杜詩“清麗亦開義山”[7]者,實就杜詩這種唯美傾向而言。如: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搗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舟他夜歸。會將白發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秋風二首》) 巫山秋夜螢火飛,疏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里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發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見螢火》) 這2首詩啟發出李商隱“少傾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聽雨夢后作》)、“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隋宮》)之句,詩人不再著力于協和與工穩,而是用奇詭的意象和兀傲的聲律,反復呼應動蕩、傾斜、失衡的內心世界。試比較夔州登樓詩和成都登樓詩: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拆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八鼉游。扶桑西樹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白帝城最高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登樓》) 同為登樓,寫于夔州的《白帝城最高樓》意象綿密,風格特異,頗具刻畫之功,似乎正印證了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與成都《登樓》的醇厚、工穩相比,夔州《登樓》以古奧、奇譎的文法,對應了高山深谷,江狹路險的自然環境,產生了詩與物在生態意義上渾然一體的意境,達到了如詩人所自況的“老去詩篇渾漫興”(《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高度。 夔州詩這種“思飄云霧動,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的唯美傾向被一些詩評家認為“造語牽率而情不接,結響奏合而意未調”,這亦說法忽視了夔州詩中文字與山水的涵容之趣。評價夔州詩不能離開大維度上的環境背景。夔州這片典型的“荒野”是一個模糊的意象空間,無法用文明世界“溫柔敦厚”的言說方式加以傳達和解釋,只能從“生態”的角度洞察其狀態和情景。杜甫夔州篇章中的“頓挫起伏,可駭可愕”正是山水的錯落險峻在語言中的符號化和象征化。前人已道:“入蜀諸詩,須玩其镵刻山水,于謝康樂外,另辟一境。”[8]。由此可見,杜甫詩歌中的想象和象征實際上是基于環境自覺和生態體驗的藝術探索,使詩歌擺脫了直白俚俗的“直立性”話語,從而“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6]148 總之,杜甫夔州詩的自然寫作隱含著環境、文化、詩歌的多重對話,既包含了嚴肅的反思,也不乏放縱的想象,既有思考也有感悟。相對于神韻山水詩“淡遠”的超功利傾向和“性靈”的私人化表達,杜甫的“風骨山水”討論了嚴肅的道德主題和敏感的心靈矛盾,體現出深刻的生態視域和環境自覺。通過這種方式,詩人從平凡庸俗的當下現實中全身而出,將自己茫然失措情感沉浸到一種真實可靠的超越力量中去,如愛默生所說:“詩人從景色中,特別是在眺望遙遠的地平線時,看到了與他的本性同樣美麗的東西。”[9]夔州的山林皋壤,實可謂杜甫文思之奧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