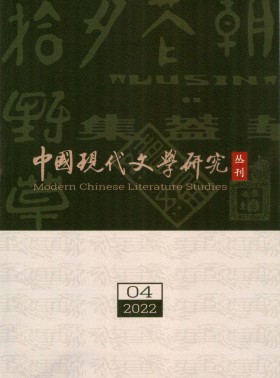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發展的突破,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在當代文化架構下拓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十分焦慮的母題。這種焦慮,或西延與漢學碰撞時炎時涼,或內溯于新國學探求時有執著,或立足當下語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當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問身份于現代漢語中漸成熱點。這些焦慮,十分集中地體現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以下簡稱“年會”)的四個分題中,會議開了四天,時間飽滿,發言密集,時有交鋒,新見疊出,是近年來少有的高質量的現代文學學術盛會。 一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 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是近十年來一直涌動的學術話題,年會圍繞其研究史與當下課題、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等命題進行討論,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新領域的拓展。 年會首先討論了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的歷史與現實課題。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以90年代為界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純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談到當下時,他認為有三大課題值得研究,“一是關于文學語言問題的史實清理與研究,比如晚清白話文運動歷史,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及文學史上關于語言問題的爭論,以及文學現象。二是文學思想語言層面的研究,比如關鍵詞研究,關鍵詞研究是歷史研究,通過研究概念的流變、發展來研究思想的變化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還停留在名詞解釋層面,缺乏意識層面深入。三是語言詩性問題研究,我們現在還沒有對語言詩性問題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說方式。“詩性”問題會對未來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巨大的突破。曹萬生(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有三個歷史邏輯層次,第一層次,對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形式研究以及這個形式歷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第二層次,把現代漢語作為與古代漢語不同的思維方式及思想實踐的研究。第三層次,研究現代漢語詩性與現代漢語文學的關系。”二是關于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關系歷史清理的研究。 年會就總體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晚清時期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當代文學時期與現代漢語及詩體語言、散文語言分別作了討論。 文學語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思路方面,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認為“應系統地梳理五四以來的語言變遷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重要內在根源,即注重文學語言的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進程(尤其是文學形式變化)影響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應著重著手研究,文學語言變化的影響到底是以何種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體裁和文學樣式的形式發展和導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學文體特征的形成”。 進入晚清時期,圍繞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困境與轉化,晚清譯入語與現代文學想象及初期譯詩等問題,代表們發表了不同意見。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一個“認同意識”困境的形成與緩解的過程,“晚清新知識者倡導白話文的初衷是維新啟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語言自覺。白話、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語言觀凸顯了晚清一代所面臨的‘內俗外雅—體用分離’的認同意識困境”,“白話報這一啟蒙形式使新知識者的認同意識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認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之譯入語的斟酌使用,充分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漢語的現代性想像。”因為,“翻譯時的譯入語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體系,而是一個有待生成的語言體系,是劇烈變動和生成中的語言——現代白話文。”圍繞這一點,袁進(上海大學)分析了晚清譯詩與現代新詩的關系,“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他們在運用漢語翻譯基督教詩歌上,已經做過大量的運用白話翻譯新詩的嘗試,這些嘗試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文學史的承認,它們被歷史遮蔽了。”進入現代,年會圍繞現代漢語的產生、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關于新詩語言的論辯、《新青年》標點與橫書、魯迅的語言觀、錢鐘書關于文言白話的觀點等進行了討論。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中國‘現代漢語’是在清末民初之際由報人、作家、政論家、國家共同完成的。”“現代文學對現代漢語起到‘定型’的作用。”陳方競(汕頭大學)認為,錢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終堅持的“‘橫行與標點’,作為《新青年》新文化倡導的一個重要主張”,“每一步微小的變化,都貫穿著同人間的分歧、爭論乃至交鋒,歷時四年多,版式和標點符號才發生整體改變”。黃軼(鄭州大學)以魯迅語言觀談了晚清到五四時期的言文之分與身份之別。 “變與不變的觀念都隱含著民族身份的焦慮。”近現代語言變革乃是為新文學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話化、歐化、拼音化三種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學)認為,錢鐘書對胡適和周作人的批評及對文言與白話的批評,體現了一種重史求實、新舊兼容的學術原則與治學方法。 進入當代,年會就現代漢語共同體形成與方言、孫犁的語言觀、詩體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劉進才(河南大學)認為,1955年相繼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漢語規范化會議,對周立波方言文學的批評,使“文學作品中方言土語的運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規訓。”劉東方(聊城大學)認為孫犁的語言觀具有承現代啟當代的橋梁作用:“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此后的李銳、韓少功、賈平凹、于堅、王家新,陳東東等,共同繼承開拓了中國當代文學語言本體論。 可喜的是,對當代文體語言的研究也成為學者關心的問題。年會圍繞現代漢語與詩趣、科學思潮與詩歌、穆旦到昌耀詩歌語言的質感、語言與當代散文等進行了討論。王書婷、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認為,“對現代詩歌文體的描述,對現代詩歌功過的整理,應該回到‘趣味’、‘游戲’”,研究了現代詩歌文體研究的現狀、趣味和游戲與詩歌的關系,漢語詩歌文體的古今得失比較,以及現代漢詩文體問題的切入視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澤龍(華中師范大學)認為“中國漢語詩歌的現代轉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潮影響的結果”,他從詩歌感性思維方式、語言、外在形式、意象類型擴展、傳播途徑等方面論述了與科學思潮的影響的直接關聯和弊端。易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穆旦時代,古典詩歌美學規范”影響了詩人寫作,但后來的“昌耀有意掘用樸拙的古漢語詞匯或生造詞匯”,承載其情,傳達滯重。“兩人獲得相似的詩學效果:詞匯充滿力度,語言獲具獨特質感。”滲透出對當代詩人現代漢語詩性的焦慮與感受。丁曉原(江蘇常熟理工學院)從語言三維視角觀察中國散文現代轉型,認為“文學的現代性,基礎性的表征當是語言的現代性。”工具層面由白話取代文言,是現代性顯性標志;語義層面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歐化”,顯示內在現代性;新文體的建構與語言關聯,顯示分型建體功能。#p#分頁標題#e# 年會在關注現代漢語與創作、新詩創作與新詩文化、現代漢語文學史學術史研究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顏同林(貴州師范大學)認為“從語言維度進行考察,普通話寫作無疑是當代文學確立的標志。”高玉對普通話語音涵義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作了回應。在新詩創作方面,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認為,“新詩的困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困境”。他認為,建設成熟的新詩文化是新詩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結果。在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近年來這方面的文學史著作開始出現。巫小黎(佛山大學)提出了構建現代漢語文學史芻議,“整合全球漢語文化資源,構建全球漢語文學世界的現代漢語文學史,其意義和價值則超越了文學史建構本身”。趙黎民(重慶師范大學)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研究持疑,認為難度很大。晏紅(四川外國語學院)就表達與應合、文學與學文、文人與文本談了自己對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曉進分別作了相應的回應。 二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當代語文教學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是本屆年會的主要論題,也是最近十多年來現代文學界持續不斷思考的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文學介入當代基礎教育聯系的動向,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界力圖介入當代社會文化建設的思路。圍繞這個論題,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建構及其當代性、經典闡釋與語文教學、魯迅作品新論、其他重要作家新論、流派文體新論等等。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變化,應怎樣評價這一變化,溫儒敏(北京大學)就研究的邊界和價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認為,近年現代文學研究步入平穩,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趨向。一是回到“史學”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學與歷史的內在關聯。”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論著在中國翻譯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三是“選題的對接,將文學領域問題與其它領域問題迅速對接起來。”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學者如何克服‘項目化生存’、彌補過分‘學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研究工作與生活世界的有機聯系。”就社團研究與國家、個人等關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他認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社團流派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化及現代文化主體的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國民“群”的觀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四者關系的形態。與此相聯,楊劍龍(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應該完全打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打破國家、群體、個人對立的思維方式。”冷川(中國社會科學院)對2009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作了系統評述。 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與經典的社會意義,成為年會關注的問題之一。金宏宇(武漢大學)提出了副文本與現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關系。認為,經典的中間層面與副文本有關。“這個經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構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關于其正文本的一種闡釋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學)認為,學院派文學批評“在1920年代承擔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則是護法者”。王方(西華大學)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現代公民意識的培養”的問題,就現代文學經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作了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既有鮮明現代性特征又能夠帶來深刻生命體驗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識形成的精神食糧。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經典的意義上,代曉東、王小平(四川理工學院)試圖用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對現代文學經典進行闡釋。周云鵬(長沙理工大學)認為“經典教學的道路不失為擺脫當前困境的主要途徑”,哈迎飛(廣州大學)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確定現代文學經典的價值標準”,提倡“精”、“深”、“慢”。 魯迅作品的經典闡釋與教學,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主題。陳國恩(武漢大學)簡述了魯迅研究史與當代中國社會、中學選本變化的簡況,主張“中學語文教學對魯迅作品的講解要專注于發掘其更為內在的、更具有久遠的文化意義,要對魯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認為,魯迅從棄礦學醫,再到棄醫從文,不斷走進了他自己。“決定魯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種學科更能滿足自我的內心需要”。張均(中山大學)從農民形象的梳離與啟蒙主義之關系的角度,認為《阿Q正傳》是“啟蒙主義獨斷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學)對魯迅作品看客、戲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討論了魯迅作品與“戲臺文化”的關系。陳偉華(湖南大學)對大學《阿Q正傳》的教學圖示了新的體驗。 不少學者對具體經典篇目進行了新的解釋。吳曉東(北京大學)提出了關注20世紀30年代文學對傳統文學借鑒的思潮問題,他以何其芳《畫夢錄》所寫三個獨立志異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蓮教某》為例,研究了“為什么何其芳的現代散文創作選擇了這三篇古代故事進行改寫?三個故事之間呈現了怎樣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寫之后的散文與原著之間有著什么樣的異同?改寫后的現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詩學屬性?”認為“《畫夢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考察中國現代創作與古典文學之關系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文本。”馬俊山(南京大學)認為過去對丁西林《壓迫》解讀都不能真正揭示《壓迫》的思想特性“,全劇都是圍繞著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開的。這是一場權益之爭,作者探討的是現代人的自由界限問題。”“深層反映的現代中國權利和自由意識的覺醒,這是它超越同時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現代性、經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國興(華南師范大學)研究了“我”在艾蕪《山峽中》的敘述位置選擇與文本價值的關系問題。賈振勇(山東師范大學)認為茅盾《蝕》等早期小說中,“政治創傷體驗激發了茅盾的藝術才情,‘絢爛中的哀傷’之美”“是他藝術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學教材對茅盾作品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規訓的結果”。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認為周作人現代思想根源有一個從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化。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對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讀日偽時期周作人對戰爭、國家、文化、個人際遇的認知和感守約同時,試圖提出那段戰爭期間出現的‘漢奸’現象的歷史性和普遍性問題”。高恒文(天津師范大學)通過“破門”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系沿革及變化,從獨特視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風的另一面。陳希(中山大學)分析了近十年來《雷雨》演出由傳統主題到超越現實的人性探索、傳統表現形式到融入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變化,認為更體現了《雷雨》創作原意。吳曉梅(昆明學院)分析了張愛玲、蘇青小說與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關系和獨立價值。夏中義(同濟大學)認為1949年前的“朱光潛個人學術史”“最具創意”。#p#分頁標題#e# 謝家順(池州學院)對張恨水小說作了民俗學的闡釋。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認為蘇雪林從個人書寫向國家敘事的轉變,體現“國家情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還有學者對整體現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劉勇(北京師范大學)認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和意義不僅僅在于體現出地域文學的某些特質,它們還有新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文化資源的開掘與發現”。邱雪松(西南大學)考察了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系的演變,“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新文化運動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誕生,呈現為古舊書店,大書局,新書業三足鼎立的局面。”黃曉華(湖北大學)分析了寓言型修辭中作為先覺者的癲狂,到詩意化修辭中作為高蹈者的癲狂,再到寫實化修辭中作為毀滅者的癲狂的三種現代癲狂敘事,是“現代人認同境遇的一種隱秘的集體隱喻”。肖向明(惠州學院)研究了清代以來民間信仰與中國小說敘事的演變,追溯有其敘事潛在的“近代性”因素。 詩歌經典研究,體現了學者們不同的關照角度,特別是對現代詩學涉及個人真實等哲學相關命題作了探討,如段從學(四川師范大學)認為馮至《十四行集》是“在個人與世界的關聯中,在個人的變化和豐富中來尋找個人真實性的生存論道路”,與魯迅《墓碣文》“把自我當作客觀認識對象”構成潛在的對話關系。陳茜(江西師范大學)在比較廢名的“渾圓”與朱英誕的“清淺”之差異中,思考朱英誕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原因。陳衛(福建師范大學)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關詩論的影響與貢獻為據,認為“朱自清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奠基人”。馬云(河北師范大學)分析了李金發詩歌與羅丹的關系,認為“《棄婦》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羅的《圣馬德萊娜》和羅丹的《丑之美》的藝術感悟。”“他的詩是象征的,也是寫實的。”在散文研究中,陳嘯(南通學院)從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論言說、創作實踐等方面探討京派文人把純“美文”以及對散文文體本體性回歸為鵠的的一次極具價值的散文文學嘗試的內涵及意義。小說研究方面,羅曉靜(中南財經政大學)對晚清小說《孽海花》“對個體欲望、情感、微觀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異之處作了分析。 陳思廣(四川大學)對1927——1939年間三次長篇小說征文與獲獎小說作了發掘與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長篇小說征文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閻浩崗(河北大學)對近年來《李自成》的評論進行了反思。 三 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近二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界,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關系的思考,一直處于轉型的焦慮之中,并成為多次會議研討的主題,隨著當代文學的延伸,這個問題得到的關注越多,這既關系到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的關系問題,也關系到如何書寫現代文學史。本次年會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問題的研究開始深入。 關于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的命題,關于近代、現代、當代的整體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問題,都繼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學)在大會發言中,更把這個問題提為“新舊文學的分水嶺——尋找被現代文學史刪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學開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誕生;法律保證了言論等現代人權;法律保護對倡白話、開報禁、言論自由、啟蒙產生了巨大作用,使現代文學一直比當代文學質量高;通俗文學得到長足發展。張福貴(吉林大學)繼續他2003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命名的說法,同時主張把當代文學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他從文學的性質和觀念、作品構成因素、形象的置換、作家身份以及文學組織機制的變化四方面論證了這是兩種“本質差異”的文學史。李怡(四川大學)看到了國家形態諸如法律、經濟、教育、宗教、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生產、傳播過程等等“結構”性因素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效應,因而贊同民國文學史的說法,謂為“民國機制”。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題,認為1945后十年,解放區文學“擴展”到大陸和國統區文學“萎縮”至臺灣、以及香港接納現代文學各種傳統,要結合在一起考察。朱棟霖(蘇州大學)在現代與古代的基本差異比較后,提出“現當代中外文學比較史就是現當代中國文學史”,認為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形態,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學術方法與思路”。高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以1894年出現翻譯小說為始,認為1894到1917應稱為“前五四的現代熱身階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雜的現代性與超現代的一元確立”,1949到1979是“超現代的一元模式從僵化到自我解體”。謝昭新(安徽師范大學)從“政治意識的演化”并通過這種演化的具體形態變化,論及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聯”。 在打通現當代文學的角度上,更多學者選擇了從題材、主題、藝術、地域、民族等角度進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這次年會的一個新的動向。段美喬(中國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葉詩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發,探討了現當代文學關聯的一個獨特現象:學界對40年代九葉派的研究,共性的關注大于個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現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們表現出的差異性卻遠遠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學)談到了“當代”建構過程的種種合力,并分析了現代作家在建構中自我更新與認同。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提出重返文學中心,對經典進行重新厘定,對學科進行新的整合,強調經世致用。袁盛勇(重慶師范大學)認為對時代“魯迅現象”的清理,“其實也包含了對于當代知識分子和魯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張要對魯迅采取一種較為古典的學術研究態度。白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西部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曾有兩次作為策動中心的機會。他以延安與當代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負能動力量、以及這種動能的有限、動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學)以晚清以來中國作家的朝鮮題材關聯,認為經歷了認知,亡國鏡鑒、休戚與共、南方缺席、“華風”“韓流”四個階段。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以北京空間敘述為線索,研究了現當代文學的差異,認為“現代文學主要對北京進行古典性敘述”,當代文學“新北京”空間敘述轉向對一些新的城市景觀,其間所體現的,是新舊城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劉永麗(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現代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中“反城市主義”主題“在當代文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20世紀該主題與儒家文化、西方反現代性思潮、殖民主義及民粹主義有關,“當代文學的‘反城市’的內在原因又有新質表現。王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以中西文化碰撞下產生“跨國戀”敘事為題,研究了晚清王韜、周瘦鵑和現代徐?、無名氏的相似相異。俞敏華(浙江師范大學)比較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和汪曾祺《受戒》,認為“這兩位常常被指認為風格迥異的作家,卻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出了趨同的價值觀念”。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以老舍《駱駝祥子》、蘇童《米》和賈平凹《高興》為例,研究了百年農民與城市關系的審美嬗變:即“以善抗惡”、“以惡抗惡”到“以善尋善”。趙凌河(遼寧大學)以施蟄存到余華為例,描述了“現代走向后現代,從‘內在現實’的追求走向‘不確定’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表述”。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提出要以魯迅“立人”主張的思想在當代網絡文化中“立網民”。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認為“書法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是被忽略的領域,“可以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錢曉宇(華北科技學院)提出中國當代幻想文學的傳承與新變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汪衛東(蘇州大學)認為“從五四到80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言說都只能是到人為止”,“無法生成真正擺脫非人存在的新資源,也無法拓展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劉殿祥(大同大學)以聞一多學術研究為例,提出在國學熱背景下“現代作家的學術經典之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羅紱文(貴州大學)從新詩對舊詩借鑒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詩之“舊路”,研究了“中國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關系的幾種模式”。 張瑩(四川師范大學)認為,王朔、劉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網絡小說等,表現出文學的影視轉向。 在打通的學術背景下,本次年會出現了專門把注意力轉向當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國(華中科技大學)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學里面呈現出四大“癥候”:簡單的“日常”與慵懶的“審美”、墮落的“身體”與貨幣化的“欲望”、價值誤置的“戲謔”與審美倒錯的“狂歡”、溫馨復制的“底層”與精神撤退的“民間”。耿傳明(南開大學)認為,在“掊精神而張物質”的當下,正顯示“《紅旗譜》的文學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義”。劉海軍(重慶大學)從鄉村脫序的全貌、城鄉沖突的文學表征與農民底層身份的焦慮這三個方面著重探討新世紀鄉村小說的特征與變化。 四 現代文學與成都 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學研究日漸與地方文化研究相滲透,拓展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域,本次年會圍繞現代文學與成都的主題,對現代文學與成都形象成都書寫、對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蕪等與成都以及抗戰時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過的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進行了研究,描繪出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幾位大家的淵源關系,同時探討對地域與文學的獨特關系與美學意義。 在總體概括現代文學與成都作家的關系時,吳定宇(中山大學)用多元構成的“西蜀文化之氣”加以概括,認為郭沫若樂山沙灣的“匪氣”、李?人成都的“市井氣”、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書卷氣尤為突出。譚桂林(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抗戰時期向大后方遷移的眾多佛教期刊,“對發掘新文學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現代佛教文學的發展趨勢”有重要意義。李永東(西南大學)認為,外省作家的成都書寫,能讓我們領略“他者”文學視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審美風格:傾向選擇陰柔、靜穆、低沉格調的意象來摹寫成都,發現北平情調或江南風味,“舊中國都市的風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圍。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以四川現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東北和四川抗戰小說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質論的偏差與學術界評價同一,認為“需要還原,以呈現文學史的多元面貌和聲音。”郝明工(重慶師范大學)描述了抗戰時期“雙城書寫”現象:縱向歷時性成渝書寫、橫向共時性京渝書寫、縱橫交錯整合性蘇渝書寫,體現出“以趨向民族史詩的藝術高度”。秦方奇(平頂山學院)以南陽《前鋒副鐫》為例,認為“在關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對為數眾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學報刊給予足夠的重視。 年會對巴金創作關注最多。陳思和(復旦大學)對新近刊發的巴金1928年計劃寫的中篇小說《春夢》殘稿作了闡釋,認為“《春夢》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后開始創作的未完稿”。“《春夢》殘稿的發表構成了對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個挑戰。”他認為“目前我們看到的《春夢》殘稿并非是原來巴金回憶中的《春夢》,而是一部已經走樣了的書稿的片段,它與巴金曾經告訴我們的創作設想中的《春夢》并非是一回事”。吳雙(西華師范大學)認為《憩園》、《第四病室》、《寒夜》里“來自故土被反復強化的記憶在深層無意識中形成文化象征符號”,匯聚成了巴金筆下獨特的“川渝意象”。金進(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認為《家》通過巴金及其信仰變化透視了30年代的文學視界:高老太爺、覺新形象“人性善惡的揭示”的體現,覺新、覺民和覺慧的象征反映(分別代表傳統性格、五四余緒、社會主義)。魏建(山東師范大學)對《沫若詩詞選》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詩詞選》何以出現版本問題,并依據所得校勘數據糾正對單行本《沫若詩詞選》與《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詩詞選》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張全之(重慶師范大學)據1923年《國家的與超國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創作中的“超國家”意識的問題“來自于當時泛濫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鄧偉(重慶工商大學)認為“李?人的文學選擇與新文學主流明顯有著某種的距離感與疏遠感”、“其小說有著某種明顯‘舊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師范大學)認為李?人、沙汀筆下的成都茶館敘事“以介于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樣貌體現了現代性與傳統之間對抗消匿、變異融合或因勢而上等多種樣態。”除了對四川籍特別是在成都出生、成長的作家進行與成都風情關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戰時期旅蓉作家的創作。李琴(四川師范大學)以清末民初四川報刊出現的首個專門文藝副刊《娛閑錄》為例,考察了主筆李?人及吳虞等人創作的百余篇小說,并論及《娛閑錄》并入《四川群報》副刊后李?人成為《四川群報》首任主筆及副刊編輯的史料及意義。在對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師范大學)認為朱光潛在成都的經歷表明朱光潛并不是一般讀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審美的學者,而是一個積極介入現實斗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王曉冬(西南大學)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張恨水抗戰小說特有的空間意識,以及這種意識在社會化小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溫儒敏,在大會閉幕式上,對大會取得的成功作了總結,他認為,“年會開得很好”,有三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一個年輕的會,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輕人。這個學科已經有五代學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這次會很多第五代參加進來了,很踴躍。#p#分頁標題#e#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個特點,這個會有很大投入、論文有120多篇,都很認真。現在這樣認真的會很少了。第三個特點,有生長的態勢和新的生長點。現代文學與語言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實的著作。研究文學語言要進入它很深的機理,必然要觸及到個性的問題。這次會議問題提得很好,還有些問題像漢語文學史的問題,像曹萬生老師那個書,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漢語文學史跟國別文學史怎么說。這個可以討論。我提幾個希望。第一,我希望我們這個學科能夠參與現實,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個持重的風格。第二,希望更年輕的學者把現當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輕一代應該從我們的教訓中走出來,做更大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