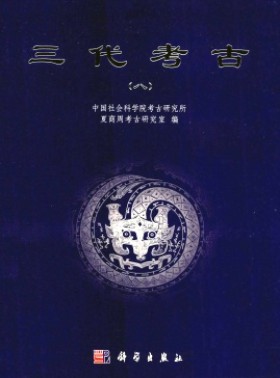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三代作者群體的文學理念,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翻閱80年代的《讀書》,我們可以發現其中討論文學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章數量眾多、比例甚大,而且精品甚多、反響也大。 這道亮麗的“風景線”的出現,與其時學術界格局息息相關:伴隨著80年代政治的全面復蘇,文學(包括創作和研究)又一次無可避免地充當了“沖鋒號”的角色,在這段文學與政治的“蜜月期”中,現當代文學因為最容易與現實掛鉤,而成為這一時代的“顯學”①。鑒于《讀書》從創刊之初就與學術研究有著千頭萬緒的聯系,考察其中所展現的現當代文學圖景的流變,對于我們今天的回顧,無疑是最佳的切入角度之一。 一、從作者群體說起 現在大家提起80年代《讀書》,最津津樂道的莫過于其時的作者名單。因為這張名單無論在當時還是如今都可算是一個“超豪華”的陣容。事實上,《讀書》從創刊伊始就有著比較明確的自我定位,即在創刊號上的《編者的話》中所言:“我們這個月刊是以書為主題的思想評論刊物。”②它從此時起就采取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因此是與整個80年代的思想氛圍互為呼應的;也正是從此出發,它依托三聯書店的出版網絡和官方背景,網羅了一批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機構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主的作者陣容。 但是在這個作者陣容里,我們可以很明顯發現它至少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三四十年代嶄露頭角卻在建國后被壓抑被埋沒的作家、詩人以及編輯等,以卞之琳、柯靈、錢鐘書、袁可嘉、綠原為代表;第二個群體是50年代出現過后來再次出現于80年代的“重放的鮮花”,以王蒙、錢谷融、王元化為代表;第三個群體是當時還在高校里就讀的大學生或剛開始進入體制的知識分子,以劉再復、陳平原、張頤武為代表。這個群體的文章是當時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其他作者雖有零散的其他文章,但是這三個群體無疑是當時刊物的核心作者。 我的這個劃分受到了洪子誠和許紀霖的啟發③,但在他們的類似劃分的基礎上也有所調整。我在這里的劃分標準主要是他們初次“發言”的時期,同時適當兼及其人的知識背景、社會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面對歷史的態度之不同、文風之差別。當然,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在其中再作適當的分疏。例如,劉再復和陳平原在知識背景和發言姿態上就有明顯差別,但是考慮到他們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們的代表性觀點,從這個角度出發,還是將他們歸入一個群體。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在80年代的《讀書》上,他們零零散散的談了那些話題?是否具有對話的姿態?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和評論都備受關注。但是就在這種背景下,他們是否也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些話題?在這一幅“眾聲喧嘩”的圖景中,我們可以傾聽到三種主流的音調,但是這三種音調是否完全是協奏,而沒有變奏?二、兩種“異曲同工”的追憶與8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科的“復蘇”相關聯,《讀書》所呈現的現當代文學圖景是以挖掘文學史上的被淹沒的作家、作品為主。這些挖掘“出土文物”的努力主要以序跋、回憶性散文、書評為主,同時也初步出現了一些研究論文。 這次挖掘為時甚久而且范圍廣闊,據我的粗略統計,按照相關文章發表的順序,涉及到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葉圣陶、聞一多、朱湘、徐志摩、沈從文、林語堂、梁宗岱、鴛蝴作家群、張愛玲、郁達夫、九葉詩人、胡風、錢鐘書等。但是我們注意到,其實很多作家作品的談論只是短暫的,似乎與刊物約稿的偶然性有很大關系。 因此,很多話題在當時并無很大反響。 但是,“九葉詩人”完全是一個例外。198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葉集》,按照九葉詩人之一的唐?的說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第一冊新詩的流派選集”①。這部詩集出版之前,袁可嘉為它作的序言就提前發表在1980年第7期的《讀書》上。這是一個普通的現象:這種行為在當時更多的是一種對讀者的閱讀引導,而非對于作品的自我吹捧。特別之處就在于,圍繞著《九葉集》和“九葉詩人”,《讀書》陸續發表的文章竟然有6篇之多②,這是少見的例子;加上袁可嘉、王佐良在當時發表的造成很大影響的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③,完全是“九葉詩人”的一次集體亮相。它呈現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九葉詩人”的形象序列,并且由于大多是九葉詩人自己現身說法,對于我們的研究來說,這個群體無疑是最合適的研究對象。 從時間與敘述的關系出發,我們完全可以把九葉詩人的大多數文章看成是一種“追憶”。 但是有必要略作分疏的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兩種追憶。 第一類追憶主要可以概括為“追憶逝水年華”。這些文章包括袁可嘉《〈九葉集〉序》,杜運燮《懷穆旦》,辛笛《〈辛笛詩稿〉自序》,曹辛之《面對嚴肅的時辰———憶〈詩創造〉和〈中國新詩〉》。這一類文章都是以當事人的身份對于當年的“九葉派”的詩歌活動的追憶,其中涉及到很多不為外人所知的詩歌史實。這在后來的詩歌史研究者那里自是極好的史料,但是在80年代的“九葉詩人”那里,卻完全是一種面對過去的追憶。看看他們的文章,我們很容易發現他們難以掩飾的面對一個新時代的喜悅。 第二類追憶可以理解為九葉詩人對自己的理解和剖析。這一類文章與前一類文章有交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可嘉的《西方現代派與中國新詩》。加上袁可嘉和王佐良等人所寫的介紹西方現代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說,袁可嘉等人在這里向他們的師承資源和詩歌史先驅一一點明并予以致敬。這一類文章大都理論性較強,深具洞見;后來的研究者都樂于引用。因此,我們也可看出,在這些文章中,袁可嘉等人所提煉的一條詩歌史的線索已經逐漸“浮出歷史地表”。 我們可以將這兩類文章還原到當時的學術史背景中去。當時,圍繞著九葉詩人的歷史回憶和重新評價問題,出現了若干重要的學術論文①。這些論文與《讀書》上的相關文章構成互動,共同促成了當時的重新認識和評價“九葉詩人”的熱潮。#p#分頁標題#e#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在80年代的《讀書》之上,相對于后世,以袁可嘉為首的九葉詩人的兩種追憶,加上兩位研究者巫寧坤和藍棣之所寫的重評文章,實際上構成了一項“文學史形象自塑”的工程。我的論斷主要是針對他們的文章的效果而發;而在他們,當時未必有很明顯的自我形象建構意識。但是后來的研究者大都從此出發來理解整個九葉詩派乃至整個中國新詩史上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謂予不信,請看三個證據即可:其一:20余年來出現的九葉詩人研究著作②,在關于九葉詩人的師承淵源、九葉之各人詩歌風格、九葉在詩歌創作之外的其他貢獻的評價等問題上都沒有超出袁可嘉等人的系列文章的論述范圍和深度;其二,由袁可嘉在《西方現代派與中國新詩》這篇文章提出的詩歌史線索,在后來的研究者孫玉石的著作《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③中得到更加精彩的發揮,但是基本的框架一仍其舊;其三,涉及到九葉詩派的外圍詩人問題,由于當時袁可嘉等人的團隊意識較強抑或是格于其他條件限制,對于自己群體之外的同類型詩人根本毫不提及,于是后來的研究者除了少數目光敏銳者之外,都不提及九葉詩派的外圍詩人④。其實,就在九葉詩人80年代集中亮相于《讀書》的同時,在此刊上接連發表《讀詩隨筆》的王佐良,其實就是九葉詩人的重要盟友和外圍詩人之一。 九葉詩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這一系列行動,實際上是在為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爭一席之地。當然,九葉詩人在當代是在繼續生長當中的。不能說他們在新時期的創作一無可觀,只是當他們過度沉湎于對過去時代的追憶當中時,我們這個越來越快的時代也就開始慢慢地將他們拋在后面了。 三、面對歷史的“暗河” 與九葉詩人的歡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輕的兩代人所體現的卻是更加自信豪邁的氣度。在面對歷史和今天的態度上,他們其實可以簡約歸并為一類人。 考慮到80年代學術研究(盡管在今天看來是草率空疏的)和文學創作之間的親密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讀書》上發表的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通信。這些文章很少涉及理論,但對于創作來說,極具指導意義。這里體現了一種良好的互動氛圍。但是請注意,這種互動僅限于后兩代作者群體之間。 與80年代的文學創作相關連的,《讀書》上的新時期詩歌和戲劇的命運就悲慘得多。 出于官方背景,《讀書》沒有登載過關于當時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朦朧詩運動”的任何文章。在我們今天面對著日益被經典化的“朦朧詩”的讀者的眼里,這是不可思議的。然而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面對著代表著民間的、青年全體性的、反思的朦朧詩詩歌浪潮,《讀書》的無語是一個巨大的有意味的行動。而這個行動加上當時的九葉詩派對于當前詩歌的有意無意的不以為然,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空缺點。 散文的命運也是如此。當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繼續著30年代周作人的風格寫作那些學者散文時,他們對于當前的散文創作一律是不加置評的。他們不停的重復自己和對當代繼續生長的其他被壓抑的散文類型的忽視,同樣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對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體的逐漸占據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漸退出版面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讀書》的作者群體在無形中發生著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種分化其實正是其后的學術界出現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預兆和契機之一。 體現在《讀書》中的80年代的嬗變,迄今為止,其實都不能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對歷史,我們其實都是那幾個摸索大象身軀的瞎子。 現當代文學的溝通即是最佳例證之一。 在論述五四以來的散文與中國古代散文的聯系時,周作人曾經用了一個很妙的比喻:“現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條被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①與此相類,當代的很多文學現象都可以從現代文學中找到源頭。因此,從《讀書》的三代作者群體的分類中,我所著眼的其實還有一個現當代文學的交接與溝通的問題。雖然當時的研究者和評論者很少有明顯的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意識,但是在各類文章的追憶和重評中,我們卻看到了論者的溝通現當代文學的努力。 然而太多的事實證明,這種努力在很多時候其實是徒勞,我們在很多時候面對著歷史的“暗河”時還是沒有跨越。還是回到九葉詩人出土后的遭遇上來。他們在出土之后的形象,非常符合“活化石”這一字眼。雖然鄭敏等人的詩作和詩歌理論在當代依然在不斷的出現,卻已經邊緣化了。更年輕的詩歌寫作者與他們缺少接觸和理解。因此,談起九葉詩派在80年代之后的創作,雖然九葉之一的詩人唐?曾有九葉詩人“與出色的一代代年輕的詩人們,如朦朧派、第三代、后現代主義者一起奔突向前”的樂觀之語②,但我們所看到的悲哀事實卻是,無論是當代詩歌的評論家還是創作者都已經將他們忽視了。他們的影響已經停留在文學史研究的層面,而與當下的詩歌寫作主潮不發生關系。 這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歷史回旋。80年代的文學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時,再一次重頭做起,以致于現在我們又出現了與前人類似的困境。 是什么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單純歸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負責任的輕率之論。倒是,更應該值得指出的,是整個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越來越急迫的以西方為標桿的現代化渴望。這種深層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實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讀書》作者群體的分裂,以及由此導致《讀書》風格的漸變。 因此,我們從80年代的《讀書》中看到的是這樣一幅互動和封閉并存不悖的圖景。關于現當代文學,三代作者大致分為兩個陣營,無論是寫作、評論還是研究,無論從話題還是文體,其間的“斷裂”都已無可避免地隱隱呈現。因此,雖然大多數論者強調“政治風波”對于80年代的學術轉向的重大意義,我卻認為,時代的轉折在此之前早已出現。#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