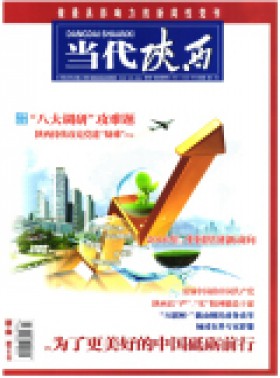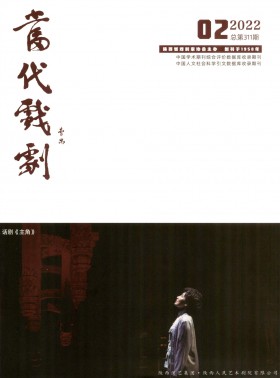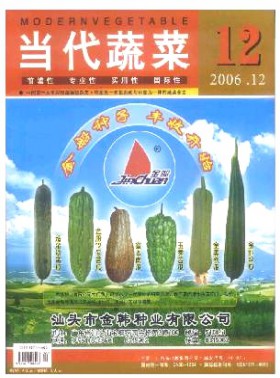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當代文學創作風格,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比喻是人類語言中一種重要的表達手段。在人類文化初始階段,隱喻即是語言的一個突出特征。在文學創作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比喻是文學語言的靈魂,是衡量一個作家語言駕馭能力高低的一把標尺,沒有比喻就沒有真正的文學。 古往今來,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人們都對這種辭格格外垂青。 在我國,自《詩經》始,比喻就在各類文學創作實踐中大量運用,并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荀子在《正名》中就有“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的認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守約名以相期也”。這里,荀子探討了“比喻”這種辭格賴以建立的心理機制。在荀子看來,同為人類具有同樣的感覺,人們的感官接觸萬物所抽象概括出來的特征自然也相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互相通曉,于是相約形成共同的概念,人類的概念就可以對應。 關于比喻在語言藝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外學者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比喻是天才的標志”;錢鐘書先生說“比喻是文學語言的根本”;秦牧稱之為“語言藝術中的藝術”;西方哲學家維柯、盧梭等人甚至認為“整個人類語言都是比喻性的”。 比喻是把陌生的東西變為熟悉的東西,把深奧的道理淺顯化,把抽象的事理具體化、形象化。 傳統的比喻喻旨與喻體之間更多地呈現為一種簡單的類比與替代,喻體承載的是一種說明性、解釋性或修飾性的功能。如《詩經•碩人》對碩人之美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這些比喻通過喻旨與喻體之間的“相似性”來完成兩者的連接,對應關系簡單明了,語言形象具體鮮明。然而這種比喻的建構模式是以犧牲文學語言的模糊性、變異性、暗示性、獨創性等深層特征為代價的。 現當代文學創作中比喻的使用,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對這種古老的辭格進行了許多改良與創新。主要表現在選用喻體時,不再拘泥于喻旨與喻體外在的、客觀的“相似性”,不再刻意關注喻體本身的審美屬性,而是賦予了喻體更廣泛的取像空間。 一、喻體時代生活化 海德格爾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意思是語言對于每個人來說,就像他所棲息的、不可或棄的家園。“鄉音不改鬢毛衰”,作家所使用的語言必然帶有“家園”與“時代”的印痕。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也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即謂文學作品的語言必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傳統文學創作中,我們雖不能說寫作主體在選用喻體時都忽視時代生活特點,但在這方面不是刻意追求卻是事實。如喻“愁”,李后主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賀方回是“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比喻十分精妙,但喻體的時代生活特征并不是十分明顯。而現當代許多作家在選擇喻體時特別注重“取譬于近”,揉進時代與生活的背景因子,時代特征十分鮮明,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例如:①鴻漸也每見她一次面,自卑心理就像戰時物價又高漲一次。(錢鐘書《圍城》)②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幾部,就好比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門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處去。(《楊絳作品集》二卷)③一個頭頂棉被的婦女上了車,車上響起了嬰兒的哭聲。小伙子用手挽著馬嚼鐵,小心翼翼地,像拉著一車玻璃器皿。(莫言《金發嬰兒》)④村頭站滿參差不齊的人,他們像土里突然冒出的竹筍,一根一根又一根。(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例①時局動蕩,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錢先生信手拈來這個喻體,看似不經意,實則含義深刻。一方面包含著對鴻漸處境的同情和對孫柔嘉姑母勢利心態的諷刺,另一方面又是對無能反動當局的一種調侃。貼切風趣,時代氣息濃郁而又耐人尋味。例②由拆一只床聯想到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失散后再難相聚,看似平淡的語言卻蘊含著無限的憂愁和難以言傳的愁懷,比喻帶有動亂時代鮮明清晰的烙印。例③作者說小伙子拉車“像拉著一車玻璃器皿”,傳神地刻畫出了小伙子對妻兒的珍惜、疼愛而小心翼翼呵護的情形。“玻璃器皿”是日常生活用品,以此為喻,生活氣息濃厚。例④是一個十分濃郁的生活化場景。作者就地取材,以村邊山上竹筍陸續拱出地面的情態為喻,活靈活現地描摹出了當一個漂亮姑娘出現在村莊時,村民們三三兩兩從山頭地里前來看稀奇的落后閉塞的農村生活場景。 二、喻體遠距異質化 比喻的力量來源于何處呢?新批評概括出了“遠距”和“異質”原則。所謂“異質”指的是喻旨和喻體兩者的本質特征迥然相異,不具備“同類”的屬性;“遠距”指喻旨和喻體缺乏顯著的“交集”,“相似”的屬性十分模糊、隱晦。 美國學者維姆薩特曾說過:“在理解想象的隱喻時,常要求我們考慮的不是喻體如何說明喻旨,而是當兩者被放在一起并相互對照相互說明時能產生什么意義。強調之點可能在相似之處,也可能在相反之處,在于某種對比或矛盾。”他在解釋這個“遠距”原則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狗像野獸般嗥叫/人像野獸般嗥叫/大海像野獸般嗥叫。他認為這三個比喻句若論藝術表達的效果最好的是第三句,“大海”與“野獸”的距離與性質最遠。所以按新批評的看法,比喻的兩級越遠越好。 把“遠距”、“異質”的兩種事物串聯于同一語境中,形成信息阻滯,從而能延緩認知與解讀的時間,使文學語言的彈性與張力得以充分伸展。 #p#分頁標題#e# 當然這種“遠距”與“異質”的比喻原則究其根本不是人為的標新立異,而應該是詩意表達的需要。 現當代文學創作中,一些作家在運用比喻這種辭格時,特別注重喻旨與喻體的“遠距異質化”。諸如“天空遼遠得像寫在書本上的自由”、“雨后的青山像淚洗過的良心”等都是令人擊節贊嘆的妙喻。從形式上看,大多數作家喜歡以抽象的事物來比喻具體的事物,且喻體不是指向某一對象的整體,而是有所修飾或限制的部分。例如:①然而就在你悠悠然陶醉其中時,一聲雄獅的怒吼忽然從草原的深處響起,貼著草皮飛快地向你撲來,像個驚嘆號一樣撞得你坐立不穩,這吼聲深沉、沙啞、奔放,威嚴得讓人不寒而栗。(陳曉潔《野性之美》)②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張愛玲《童言無忌》)③沈太太……嘴唇涂的胭脂給唾沫帶進了嘴,把暗黃崎嶇的牙齒染道紅印,血淋淋的,像偵探小說里謀殺案的線索。(錢鐘書《圍城》)④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 仿佛舉行某種拯救靈魂的宗教儀式一般,我們專心致志地大走特走。(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例①用抽象的“驚嘆號”來比喻“雄獅的怒吼”這一具體的事物,聯想奇特,并且用一個極具沖擊力的動詞“撞”來描述,寫出了那種撼人心魄的感覺。例②童年歲月的感覺難以言說,十分抽象,作者以“老棉鞋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喻之,恰切地寫出那種暖暖的、柔柔的、慵懶散漫的感覺。例③錢先生用“謀殺案的線索”這個抽象的事物來比喻“牙齒染道紅印”這個具體事物,令人倍感新奇,并給人以“血淋淋”、“觸目驚心”的視覺沖擊。例④“走路”與舉行“宗教儀式”之間的差異性、異質性是巨大的。一對戀人一路無話,只顧“走路”,走得那樣“虔誠”、走得那樣“莊嚴”!經過村上春樹一番巧妙的整合和點化,我們非但感覺不到牽強附會,甚至會漾出一絲會心的微笑。一般的比喻是“似是而非”,而村上的比喻則是“似非而是”。 三、喻體主觀感覺化 喻體與喻旨不是強調“形”似,即客觀上的相似性,而看重的是“神”似,即言說者主觀感覺上的相似性。如大家熟悉的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一個句子“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從使用的辭格看,既是通感,也是比喻,強調的是作者主觀感覺上的“神”似。 強調主觀感覺的比喻句,其喻體與喻旨的連接方式從形式看是一種“暴力組合”,有時完全漠視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客觀相同或相似的屬性。如日本新感覺主義代表作家橫光利一《多與腹》中的比喻名句:“白天,特別快車滿載著乘客全速奔馳,沿線的小站像一塊塊石頭被抹殺了。”用“石頭”喻“被抹殺”的“小站”,本是一種“暴力組合”,再加上一個充滿力度與速度的“串味”動詞“抹殺”,令讀者在閱讀時產生強烈的“瞬息”的感覺,完成了寫作主體期待的強烈的心理效應。 文學語言是一種“內指性”的“偽陳述”,它關乎的是文本本身的世界,無所謂真假與對錯,遵循的是藝術世界的詩意邏輯,訴諸的是讀者的直覺,因而在使用比喻這種辭格時強化寫作主體的主觀感覺,運用變異性的語言,并非有悖文學語言的本質與規律。下面再看幾個例子:①蔡玉珍看見那些學生一邊喊一邊跳,污濁的聲音像石頭、破鞋砸在王家寬的身上。 (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②可憐的賓館!可憐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濕的三條腿的狗……(村上春樹《舞》)③父親叛逃之后,我們就開始了素食,素得就像送葬的隊伍或是山頂上的白雪。(莫言《四十一炮》)④街上賣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東方的歌,一扭一扭出來了,像繡像小說插圖里的夢……(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例①以“石頭、破鞋”喻“污濁的聲音”,讓縹緲的聲音有了重量,讓讀者感覺到王家寬不僅受到了精神上的侮辱,同時也受到了肉體上的傷害。喻旨與喻體之間雖然缺乏“形”似點,但在感覺上卻具有一致性。例②中的“賓館”和“三條腿的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事物,村上春樹把它們硬接在一起,這大概是他個人在獨特心理狀態下的一種獨特主觀感覺吧。在讀者眼中,此賓館是多么的孤零、冷清與衰敗!例③“素食”非指顏色,意謂沒有葷腥,與“送葬的隊伍”、“山頂上的白雪”之間毫無相似之處,但我們仔細一咀嚼便會明白:渾身披白的“送葬的隊伍”中彌漫的是一種“傷悲”的情緒,“山頂上的白雪”帶給人的是“寒冷”的感覺,而喻旨“素食”恐怕不僅僅是指食物,而是指代一種生活。這樣解讀我們就明白了:父親叛逃之后,留給我們的是悲傷,我們的生活從此進入寒冬!“素“字在這里僅僅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例④“東方的歌”像“繡像小說插圖里的夢”,喻體是那樣虛無縹緲,卻又拿捏得那樣細膩而準確,古色古香不乏文化的內涵。張愛玲不愧為感覺化描寫的高手。 四、喻體風趣幽默化 什么是幽默?《辭海》上是這樣解釋的:“通過影射、諷喻、雙關等修辭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的訛謬和不通情理之處。”幽默的特性在于微妙的常識和智慧、哲學的輕逸和思想的簡樸,它不是以嚴肅、復雜和深刻的面目出現,而是善于在通常以為正常的行為中察覺出細微的差別和異常,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揭示出虛偽做作。 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幽默語言風格的有林語堂、魯迅、老舍、趙樹理、錢鐘書、王蒙、曹文軒、高曉聲等一批作家。目前一些網絡作家更是把幽默的語言風格發揮到了極致。這些作家在幽默的表達方式、幽默的品味方面盡管存在差異,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是運用風趣幽默化比喻的高手。#p#分頁標題#e# 幽默的比喻是以追求喻旨與喻體之間的強烈反差性或對比的荒謬性為目的、以讀者豐富的“聯想”為紐帶,通過兩種事物間屬性的移植而形成的。例如:①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的真理。(錢鐘書《圍城》)②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魯迅全集》卷六,275頁)③過了一會兒,買買提處長的鼻孔和牙花都被打出了血,鼻青臉腫,眼睛象核桃,沒有核桃夾子是開不開縫了。(王蒙《買買提處長軼事》)④咱們倆的感情就跟人民幣一樣堅挺。 (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例①中“局部的真理”,既是“陌生化”的新造詞語,又是一個化具體為抽象的比喻,新穎絕妙,讀來令人噴飯。例②把“譯書”比作“訂婚”,喻旨嚴謹莊重,喻體輕松喜慶,兩者在語體色彩上形成強烈反差,從而取得幽默的意趣和譏諷的鋒芒。例③一位黨的好干部被無緣無故地打得遍體鱗傷,作者不是以憤怒和同情的筆調來敘寫,而是由“核桃”再聯想到“核桃夾子”,以調侃的口吻“幽了一默”,表現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的無奈心情。例④以“堅挺”的“人民幣”喻“感情”,既有時代感,又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 與傳統比喻相比,現當代文學中比喻取材的視域要廣泛得多,對人的主觀世界投射的目光也更多。喻體的時代生活化,一方面“近取諸身”,使比喻的外延得以大力擴張,另一方面能有效地揭示文本的社會背景,為寫作受體正確解讀文本留下明晰的線索。 喻體的“遠距異質”化和主觀感覺化,是對傳統比喻強調“相似性”的詞語轉移和替換一個有效的突破,同時也與現當代文學創作由傳統重點關注客觀世界轉向重點審視人的心靈世界的潮流相契合。追求喻體的風趣幽默化,則與現代人外在的生存環境壓力增大有關,人們渴望閱讀文學作品時能在一種輕松的狀態下進行,為生活的壓力尋找一個情緒宣泄的窗口。 從審美的角度看,現當代文學創作在比喻的運用過程中,還有一種負面傾向值得我們警覺,那就是喻體取材惡俗化、下流化。如莫言小說中的一些比喻就頗受人詬病,比如“嫉妒中的女人嘴基本上就是個肛門,嫉妒中的女人話基本上就是臭屁。”(《四十一炮》)、“馬洛亞牧師躥出鐘樓,像一只折斷翅膀的大鳥,倒栽在堅硬的街道上。 他的腦漿迸濺在路面上,宛若一灘新鮮的鳥糞。”(《豐乳肥臀》)、“繼續扇下去,連麻酥酥也消失了,只剩下‘呱唧呱唧’的瘆人聲響,好像不是在扇自己的臉,而是在扇著一個褪毛豬的尸體,或是一個死女人的腚。”(《酩酊國》)……喻體毫無美感可言,無一不給人一種骯臟、丑惡甚至惡心的感覺。個別打著“前衛”“先鋒”旗號的作家、詩人更是樂此不疲地圍繞著人的性器官和性心理來設喻。 文學的主要功能是審美。傳統文學語言中的比喻大多形象、傳神、典雅,無不給人以藝術美的享受。作為現代人,如果我們在創設比喻時,為了追求新奇、獨創、另類而不惜庸俗、媚俗、惡俗,如是則矮化了文學的審美功能,也失卻了比喻在文學語言中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