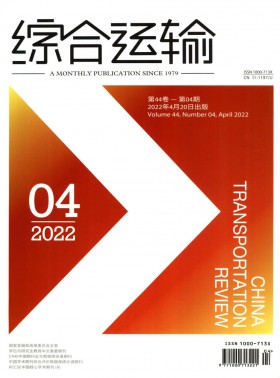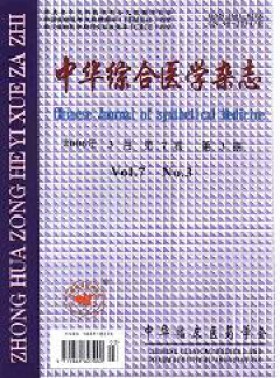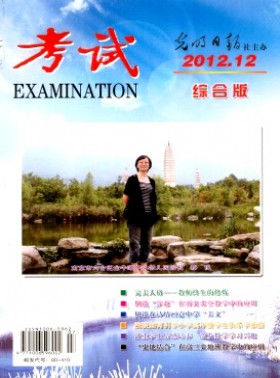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綜合材料繪畫的語言形態淺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自從杜尚將一個簽有自己名字的小便器送到博物館展出后,整個繪畫藝術發展的軌跡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用這種奇特的卻具有強化效果的方式使作為物質材料的小便器轉化成了一種藝術符號,讓物質的特性轉化為了一種藝術語言,藝術創作自此便打開了現成物質材料與藝術品的界限,材料本身在繪畫領域開始發生了一種“質”的轉變,這種變化給繪畫藝術帶來了語言性的本質轉化,材料開始成為了畫面的主體語言并具備了自己的語言體系,尋求著自身的一種表達與述說方式。隨著沙子、鐵屑、稻草、樹枝、大理石粉、油彩、瀝青、土質材料等等眾多的物質材料及現成物品開始運用到畫面,繪畫者的創作方式也開始呈現多樣化,混合材料、拼貼、影像媒體、裝置等藝術形式成為了綜合材料藝術創作者的主要表現手段。劉驍純在為張國龍所撰寫的《當代•藝術•材料•空間》一書的序言中寫到:“在古典藝術中,比如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顏料、水、膠、筆、墻壁乃至涂色、勾線的工具、材料、色、線、點、面、體、光、空間、結構又是塑造人和物的手段、人與物有是為組成故事服務的,故事又是為宗教教義服務的。媒介物質在這里是手段的手段,‘仆從’的‘仆從’。經過近現代藝術的一系列變革,‘主人’的‘主人’一層層退位,‘仆從’的‘仆從’一步步升格。媒介物質終于在當代藝術中從‘仆從’上升為‘主人’。”,“在材料的利用中,隨著混入的材料越來越復雜和新材料越來越多地被起用,媒介物質一步步自主自立,從藝術語言的輔助手段上升為藝術語言本身,這里最重要的是生命與物質材料的對話,思想與材料物質的交流,這種對話和交流最終留下的是注入了生命和思想的物質痕跡。”道破了物質材料在綜合材料繪畫中“物”的語言特性和地位的轉變。當物質材料完成了這種從“仆”到主體語言的角色轉換時,其所形成的語言內涵便出現了多義性,形成的秩序體系就開始變得廣泛和多變。
那么綜合材料繪畫在其語言體系上呈現出哪些形態呢?
首先,綜合材料繪畫在語言上首先體現出來的是對“物”的形態、屬性及語義的理解認識和重新建構,是對各種物質材料在進行藝術創作中功能和價值的再認識。任何的物質材料其本身都是具備兩種內質的。一個是物質本身具備其作為物的形態和屬性,這種形態和屬性也就是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表情”,即它的材質感。這是它作主體語言參與到畫面組構上的最重要特性。二是物質所具備的物的語義,也就是其作為材料存在而具備的文化積淀。物質在存在的過程會被其所存在的文化環境賦予的相應文化內涵和精神指向。我們單純地看木頭、土、乳蠟、油脂、鋼鐵、水泥、玻璃等物質材料時,會因為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區分開這些物質材料具有的冷暖特性。在綜合材料的藝術創作中,物質材料正是依托其本身的“物”性和所承載的文化內質與繪畫者賦予的精神相結合,來實現著物質與精神的對話。在這過程中,藝術家對材料的物質材料的敏感度和對物質材料的屬性性能的把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藝術家克拉斯和布羅克邁爾就是選取了金屬鐵板材料進行創作,他們利用鐵板材料的不透明、可腐蝕、色澤突出等特性,通過鐵板的自然銹斑和制作出的畫面痕跡相結合,表達出了他們的一種莊重、深沉的生命體驗。而博伊斯在作品《動物脂》中,則用毛氈和油脂材料進行藝術創作,他正是利用這種材料毛氈和油脂本身就具有暖性的物性特征來完成他的藝術構想的。畫家朱進在他的《時光》系列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不斷的運用黃色土、五色土和褐色土等土質性材料來完成他的藝術作品。他利用土質材料具備的與人天生就有親和力的物質屬性來實現著自己的藝術訴求,畫面上,“土”所獨具的材料屬性和文化內質成了畫面的主體語匯,觀看者面對畫面所產生的內心觸動幾乎都來自于這些涂抹、堆徹、龜裂在畫面上黃褐色土料。
其次是綜合材料繪畫的藝術語言呈現為一種媒介的綜合運用狀態。不同媒介的綜合使用為綜合材料語言體系的拓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由于不同的物質材料之間是無法融合的,正是由于多種媒介的參與結合,才使各種材料在碰撞沖擊之后產生了流動進而變得親和起來,達到了一種不同材料沖撞后的平衡,我們才會感覺到材料所形成的藝術張力和精神的升華。藝術創作者們正是通過使用眾多的特定媒介,來完成其內心特有的生命關注與體驗,我們可以從眾多藝術家的創作中得到體會。法國畫家簡•杜布菲在材料的使用上可謂是多種多樣,他把泥土、沙子和其他材料做成厚厚的有顏色的基底,并且一改用色彩進行繪畫的形態,使用沙礫、海綿屑、木板等材料進行制作,通過在這樣的畫面上作畫,畫面上經常出現的是斑駁的色痕,各種奇特的形象就是在這樣的基底上浮現出來的;作為西班牙非定型繪畫大師,安東尼•塔皮埃斯在大量的藝術創作中把抽象表現主義和材料語言進行了結合,在畫面上,他大量使用大理石粉、沙子、粘土、纖維等材料進行各種綜合材料創作,在具有浮雕感和豐富肌理的畫面上采用刮、割等手段創造出了完全屬于他自己的語言面貌;而作為二戰后的德國藝術家基弗具有深深的悲劇意識和憂患意識,他把現成的物質材料和媒介進行整合,并保留材料的符號屬性,在作品中完成了物質材料在視覺上的解讀和喻示。干裂的泥土、殘破的廢墟、荒蕪的大地充滿著他那巨大的作品中。他把鋼鐵、鉛、瀝青、灰燼、紙、石頭、植物、油彩、油墨、沙土、丙烯、水泥等等綜合物質和綜合材料運用的畫面,畫面上材料與媒介不斷的進行著反復堆砌,觀者在視覺上就能感覺到作品上物質的重量感和可觸摸感。在作品《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中,兩個高大的書架上陳列著用腐蝕制作過的鉛皮作成的一部部敞開的巨大線裝書,強大的視覺震撼力撞擊著人們的眼睛和內心,來描述著德國的歷史和磨難。德國的另一位藝術家伊米爾•蘇荷馬則是從物質的無形狀態中尋求另一種表現手段,他把濃稠的黑色瀝青直接鋪撒在經過制作的厚實畫面上,在他那泥土般的背景下,黑色的線條深沉奔放,在畫面上形成了極具生命感的張力,從而脫離了材料的制作性轉而進入到一種寫意的境界。
再次,綜合材料的語言運用經常表現為一種對文化的借用與轉換。文化的資源是藝術賴以發展的土壤。在整個文化資源中,既囊括著自然資源也包括著精神資源,當自然資源和精神資源能夠在藝術家的創作中找到對應時,材料與精神就會形成了一種互動和互通,從而完成了藝術創作者與畫面、觀看者的一種對話。對傳統文化進行借取和轉換是很多材料藝術創作者的共同取向。在藝術家蔡國強的一系列的火藥爆炸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藝術家本人對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這種借取和轉換。他將火藥和顏料鋪設在畫布上點燃,畫布在爆炸后形成了痕跡,在整個作品的制作過程中,他尋求火藥這種媒材的材料屬性和這種媒材的中國文化性的融合,在點燃火藥同時,他也在點燃一種博大恢宏的文化力量,作品在此時成為了將這種中國傳統材料轉換成了一個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開展對話交流的符號客體,讓觀看者能在畫面上感受到來自中國古老文化的震撼。在藝術家徐冰的作品《天書》中,我們感受到的更是藝術家對傳統的文化資源的巧妙的借用。作品《天書》可以算是對我國漢字進行的最徹底最激進的解構,他所書寫的“漢字”中,所有的文字都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在經過傳統木板印刷技術進行印刷和裝訂,真可算是一次對中國最有力的書寫漢字的徹底顛覆。而與徐冰的天書相對應的另一個代表藝術家呂勝中,則是對中國傳統民間技藝“剪紙藝術”進行了借取。他將民間傳統的剪紙語匯加以提煉,創作并利用一個“小紅人”的符號形象進行藝術創作,呂勝中通過剪紙這項技藝把自己的藝術創作回歸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將這項古老的民間技藝轉變為了一種能夠進行深層溝通的媒介,成為了其與社會、與觀看者對話的載體,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取之不盡的東方文化精神積淀,從傳統文化入手,尋求傳統媒介材料與當代精神的融合交流,成為綜合材料藝術創作的一個有效手段。
另外綜合材料繪畫在自身語言體系的建構上則更加強調語言的偶然性和實驗性、觀念性和精神性。綜合材料繪畫本身就是一門以實驗性為主要創作方法的視覺藝術,它對所有物質材料認識和運用都是一種實驗性的探索。因此作為綜合材料藝術的創作者,為了有效利用物質材料,傳達自己的藝術訴求,就要對不同物質材料的語言屬性進行反復梳理、歸納、再認識,通過不斷的實驗運用,才會使物質材料能夠形成具有獨特個性的藝術語言。因此這種不斷的藝術實驗性就成為了綜合材料繪畫藝術在技術探索和實現上的一個重要特征。同時物質材料應用的無限可能性為其藝術語言的形成與建立提供了無限發展的可能,這也就使其語言的形成具有了極大的偶然性特征,偶然性便成為了綜合繪畫材料語言形成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征。“激發大腦的各種發明,是讓人們觀察斷壁殘桓,未息的余燼,以及斑石、云朵和土塊,因為這些不規則的“偶然性”形態中能使人產生奇妙的發現,使藝術家進入一種夢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想象力就開始在那些墨點和不規則的形狀中施展魔術,而同時這些形態又反過來幫助他進入一種朦朧的虛幻狀態,使藝術家的內在視覺得以投射到存在的事物上。”(達芬奇語)[2]在綜合材料繪畫創作過程中,正是依托這種給人充滿想象空間的偶然特性才會使創作者能夠把握住畫面形成的那些具有美感和抽象意味的“跡象”,并對這種“偶然之象”進行重新的選擇組構,把那些具有視覺美感和沖擊力的痕跡保留下來,形成新的視覺審美趣味。實驗性和偶然性相互依存而成為了綜合材料繪畫藝術的一種最為重要的品質。其次,在材料的運用上,繪畫者更加強調材料所具有的觀念性和精神性,更加注重這種精神觀念同物質材料的結合與對話。其實物質材料其本身是不具備精神性和觀念性的,是繪畫者在藝術創作的實驗過程中,對物質材料進行了分析、梳理、認識、運用和轉化,并在畫面上賦予其一定的精神內涵,從而使物質材料成為了創作者精神訴說的載體。創作者是把材料在經歷過時間和特定文化沉積后所形成的那種神秘“物質”不斷進行挖掘,并把這種“物質”當作傳達精神與觀念的載體在畫面上直接呈現,這時的物質材料便因為精神的存在而具有了全新和獨立的審美價值,物質材料所蘊涵的特定文化暗示便穿透材料而傳達出來,材料的精神便在畫面上得以提升和彰顯。
綜合材料繪畫的語言體系是有著無限的發展空間的,對其語言秩序的探索也不會簡單的停留在以上這幾個小范圍之內,這需要藝術創作者和研究者們在其不斷的藝術實踐中進行總結歸納,才會為這門視覺藝術的發展填充更多的給養。
本文作者:張天佐 單位:海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