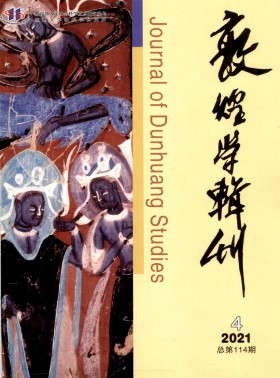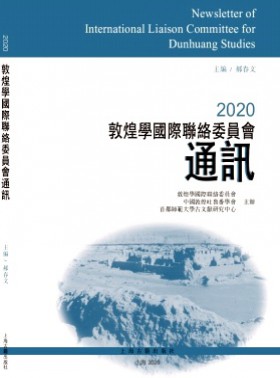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敦煌藝術理論探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法國的丹納、中國的馬奇、美國的奧爾德里奇等藝術批評家或美學家,都曾以“藝術哲學”為名寫過很好的書;一些藝術批評家如司空圖、道濟、劉勰、朗格、科林伍德等也寫過很好的書,這些書雖未貫以哲學的名字,但確是藝術哲學的上稱之作。①他們都以自己對藝術的獨特見解,構造了各自龐大的藝術哲學體系。什么是藝術哲學?這往往取決于藝術家各自對什么是藝術的體認。 藝術是人表達自己的存在的特殊方式。人通過藝術對時空進行自由地切割,從而構造一個同人的現實存在相對應、但又同人的現實存在性質不同的虛擬的世界;人需要這個世界,因為人不滿足、甚至厭惡自己的現實存在,人在自己創造的這個虛擬世界里為自己的精神、理想尋找寄托和解放。人不可能只待在這個虛擬的世界里,除非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因為,人需要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生存滿足,需要處理實實在在發生在自己周圍的各種現實關系,需要對既定的各種精神規范負責;但是,一當人創造了自己的虛擬的世界,人的一切現實的經驗都會經受一種極為復雜的、超驗的洗禮,現存世界的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關系,即會放出新的光彩。人所特有的這種來往于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用現實世界的經驗和教訓構筑虛擬世界、用虛擬世界的光彩映照現實的能力和活動,并非為個別藝術家所獨有,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這種能力和活動,只不過有強和弱、自覺和不自覺、執著和不經意之分罷了。有沒有無此能力和活動的人?有沒有只死心塌地生活在功利的現實世界的人?可能有,如果有,這種人當是很出類拔萃的,亦是很令人畏忄瞿的。 2.藝術哲學同通常的藝術理論不同。它不把如下問題作為專門研究的對象:如各類藝術形式的形成歷史和社會條件;藝術形式本身的結構、規律、特點;藝術形式的制作者稟賦的風格、技法;形式之間的橫向關系、縱向承傳等。藝術哲學是藝術的形而上學;藝術哲學不排斥對上述問題的研究,而是把上述問題所揭示的關系當成既定的資料,通過對它們的分析,了解藝術形式是如何表達人的存在狀況的。 一般藝術哲學(這里暫不專講宗教藝術哲學)所要探討的人的存在狀況有三個層次:藝術是怎樣表達人對現實世界的反抗意緒的;藝術是怎樣表達人對現實世界轉化意緒的;藝術是怎樣表達人對現實世界的空靈意緒的。這實際上是人的三種審美境界。 以《竇娥冤》為例,先說說第一種境界。竇娥蒙冤,將在惡勢力的屠刀下喪生,她立誓:若自己無罪,行刑后,血濺旌旗,六月飛雪。這本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她真的被冤枉了。但當她被砍頭后,她的誓言果然實現了。她(當然首先是藝術家關漢卿)用殷血、白雪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的激烈的反抗和控訴。個體的肉體毀滅了,但它的精神高揚了。這是一種藝術的審美境界,它內涵著善同惡的永不妥協的對立,標示著個體肉體存在的脆弱性同個體精神存在的堅忍性之間難以調和的對立。這種境界的主調是不和諧,而這里,不和諧正是一種美:漫天大雪,一片銀白,但它卻掩不住從冤尸潺潺流出的殷血。第二種境界,我用歷史上有名的“藍獄”中一個被殺的人的一首詩來說明。 明時,太祖誅戮功臣,曾在洪武時被封為大將軍的藍玉以謀反罪就刑,為掃除黨羽,受牽連的一萬五千人先后被推向刑場。其中有個叫朱壽的,當開斬的鼓聲已響,劊子手手中映著落日余霞的屠刀就要舉起時,他竟占詩一首:“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已斜。黃泉無故人,今夜宿誰家?”現實如此殘酷,受牽連無端被砍頭是這等不公平,心中沒有一點憤恚、一點怨恨、一點不平?從詩看,確無。現世界沒有是非,他也就不分辨是非了,現世界沒有公正,他也就不計較公正了,現世界無處伸冤,他也就不考慮伸冤的事了,現世界已不容他再活下去,他也就不再留戀塵世那些斬不斷的情緣了。他這會兒只想著黃泉道上如何趕路的事了。這黃泉沒有陰風慘慘,沒有厲鬼擋道,而仿佛是一條供他旅游的路徑,雖然有些陌生,但卻饒有興味。現在需要考慮的是,走累了在哪家店鋪歇腳啊?這是一種把可怕的死轉化為平淡的回家的境界,一種把生存的無奈境況轉化成可供陶醉的狀況的境界。夕陽、鼉鼓、屠刀、含冤難訴、身首異處——這些令人心肝具裂的景象,被一句“今夜宿誰家”一下子改變了。人們立即轉而對受刑人面臨生存極端處境,卻能以平常心淡然處之的心態,表示由衷的贊佩。第三種境界,就是莊子在幾千年前描繪的,后來又融進儒、釋的思想,在中國人的生存中和中國人的藝術觀念中綿延不絕的禪的空靈的境界,一種引導人進入齊生死、等高下、游無窮、無憂、無礙、無待、無己的境界。面臨生存的極端狀況,改變心態,視死如歸雖不易,但若要在整個活著的時候超越生存的一切感性和理性的判定,將是非、曲直、善惡、貴賤、否泰、喜怒、哀樂、生死、有無等等,一樣對待,就是更難的事了。這是一種需要終生修煉,同一切感性體驗始終背道而馳方能達到的境界。這里我舉丹霞子淳禪師(1064~1117)的一首《無題》詩為例:“長江澄澈即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②也是一首寫歸宿的詩。浩瀚的長江水面上映射著月亮的光華,微波漣漣,銀光萬點,靜極,廣極,美極,這景象映入人的眼瞼,有一種入歸的感覺嗎?還沒有,因為這時現象和感覺還是兩分的;只有駕著小舟,輕輕劃過江面,沒入銀色的月光、銀色的水光和銀色的蘆花融為一體,一切都分不出彼此的葦叢中去,才算找到了真正的歸宿。在這種境界中,沒有生的歡樂,亦無死的恐懼。在這種境界中,無須將生存的無奈轉化為生存的陶醉。在這種境界中,有生命的(如人、如蘆花),和無生命的(如月、如水、如船)是和諧為一體的。在這種境界中,人與萬事萬物,自我與流動的現象,都在宇宙的永恒的靜謐和神秘中融解了:宇審就是自我,自我就是宇宙,生存的永恒的真諦就在于此。 3.如果說,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表現,那么,藝術哲學就是探究形式中融化著的“意味”的。這是借用別人的概念的一種說法。“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國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的用語。他把意味解釋為同現象事物不同的東西,解釋為“終極的實在”,說:“當我們把任何一件物品本身看做它的目的的時刻,正是我們開始認識到從這個物品中可以獲得比把它看作一件與人類利害相關的物品更多的審美性質的時候。……我現在談的是隱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并賦予不同事物不同意味的某種東西,這種東西就是終極實在本身。”③這個“終極實在”亦被他稱作“一切物品中的主宰”、“特殊中的一般”、“充斥于一切事物中的節奏”。中國古代的藝術理論,不太集中談“意味”。而是談“氣韻”(如畫論),氣韻似乎更動蕩些;談“神韻”(如詩論),神韻似乎更生動些;談“太極”、“道”、“天地之心”(如文論),這些似乎更樸素,更自然些。這里的自然同貝爾說的“終極實在”有共通處(都指人心之外的一種存在),但不同處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藝術家對人之外的絕對獨立的存在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總喜歡通過藝術在這樣的存在與心靈之間架起橋梁,表現人的精神同自然的精神的共鳴、諧振。在中國藝術家那里,自然,是被人的精神“軟化”了的自然,而精神,又是被自然的氣韻充盈著的精神。因此,在中國藝術家的多數作品中,人同自然是很諧和的。#p#分頁標題#e# 4.在這里,藝術與宗教有了相通的性質。宗教同藝術一樣,也是人為自己構造的虛幻的世界,宗教亦用這個虛幻的世界表達人在現實世界實現不了的理想和意愿,亦借助虛幻的形式或關系,將人在現實世界充滿沖突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關系予以重構,使它變得和諧。天國里的物質供應總是很豐富的,天國里的人和人(神與神)的關系也是非常和諧的,固然這關系極為等級森嚴。 5.但是,宗教畢竟是宗教,藝術同它有著本質的區別。藝術的時空觀同宗教的時空觀是根本對立的。其一,藝術并不宣稱自己構造的虛幻世界是一種客體的、乃至占據實在空間的世界。構造藝術虛幻世界的材料是占據一定空間的,但這個空間并不是藝術向人的精神展示的那個虛幻的空間。藝術構造的虛幻世界是主體性的、精神性的、不占據物理空間的,在人看到的地方不占,也不告訴人它存在于某個看不見的地方。而宗教則宣揚自己構造的虛幻世界是一種客體的、同現實世界一樣占據著廣大乃至無垠空間的世界,一種現在觸摸不到、但今后可生活于其間的彼岸世界;其二,藝術構造的虛幻世界,相對構造者和欣賞者,在時間上以瞬間方式存在。它既不存在于人的現實存在之前,也不存在于人的現實存在之后,既不是人的現實存在的前因,也不是人的現實存在的結果。它是間于人的現實存在之中的一個個、一次次美麗的閃光。宗教構造的實際上是虛幻的世界卻宣稱,相對它的構造者和膜拜者,它在時間上以永恒的方式存在。它既存在于個體人的現實存在之前,也存在于個體人的現實存在毀滅之后,既是人的現實存在的前緣,也是人的現實存在的歸宿。它宣稱:相對人的短暫的現實生活,人的宗教的、與神同在的生活是永恒的;其三,宗教的虛幻世界,除過是人的一種精神需要外,還帶有一種由外部力量(如宗教宣傳、政治權力)強加于人的性質,所以,對于膜拜者,宗教是自由的,也是不自由的。宗教宣稱的秩序多是凝固的,對規定這種秩序的教義的稍許變動,往往要經過艱難的斗爭甚至血腥的博斗。藝術構造的虛幻世界一般說來,對人沒有強迫性,你可以進入這個世界,也可以不進入這個世界。進入這個世界后,你可以自由地、不須要以任何教條作準則,來對這個世界作新的自由創造,因此,就藝術世界對不同個體的寬容態度而言(或反過來,就任何個體都可以對藝術世界進行隨心所欲地創造而言),它是超時空的存在,是無規范、無邊無垠的存在,多樣性的存在。其四,宗教構造的虛幻世界作用于人的“思惟空洞”:人作為個體,依戀自己的生命,因而對它最終將無可挽回地走向寂滅難以理解,難以作出令個人樂于接受的理性的解釋,思惟在這個對個體來說非常重大的問題上處于空白、空虛、空洞狀態。宗教用信仰來填補這個空白。它給個體描述感性生命走在盡頭時的境界。藝術對虛幻世界的構造,是個體自主選擇的一種“精神自由”。它不回答個體熱愛生命、但又無法改變它最終歸于寂滅這個背謬的問題。它是個體在存在歷程的無數個瞬間,將生命從現實生活中升騰起來的自由活動。 6.宗教藝術把宗教的虛幻世界和藝術的虛幻世界結合起來,構成一種奇特的虛幻世界。藝術世界不論它多么虛幻,人總會覺得它是人的世界,是人參與其中的世界,即便其中沒有勾出人的形象,人也不會覺得它是異己的,人同它有一種親和感。宗教世界則不然,它愈是虛幻,則人愈覺得它遙遠。它是神的世界,人的異己的世界,人對它有一種敬畏感、恐懼感。宗教,比如佛教,最早是不允許人把佛陀繪成具象的形象的,教徒為了崇拜佛,便面對一個被塑成柱子形狀的東西誦經禮拜。這時候,那根抽象的柱子主要只是一個崇拜的對象(當然,由于崇敬,那柱子在教徒的心中肯定會引起某種審美的感覺)。后來,人不滿意于自己對著一根抽象的柱子的膜拜了,于是便叛離教規,為佛塑出了具體的人的形象。這時,佛的超時空的、神秘莫測的、難以親近的性質在人的心里不自覺地發生了變化:佛同我們畢竟還是有共通的地方啊。隨后,佛啊,菩薩啊等等便被塑得越來越美,人有多美,他們就有多美,甚至比人還美。就這樣,一個崇拜的對象,同時成了審美的對象。可以說,宗教,一旦同藝術結緣,它的神性便被人性的光暈所衍射。人面對宗教藝術,是面對神,還是面對人?是崇拜神的威力,還是欣賞人的美麗?是向一種同自己截然不同的力量曲膝膜拜,還是同一個有力量有智慧有善心、但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同類進行對話?這些,在此時都顯得界線不太分明了。宗教藝術是宗教向人墮落(亦可以說是向人提升)的一種感性表達。 7.在這方面,敦煌藝術是最為典型的例證。我們經常把敦煌藝術的這種活動稱作敦煌藝術的世俗化。對敦煌藝術的世俗化解釋,是對敦煌藝術作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當然,與世俗化傾向相對應的,敦煌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變化與特點,它同一般世俗藝術的聯系與區別等等,也就成為對敦煌藝術作哲學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內容了。 8.敦煌莫高窟的眾多雕塑和壁畫中,有數不盡的表達禪境的作品。禪是中國人融會儒、道、釋的精義而創造的體驗生存意義的宗教的、藝術的境界。儒學作為一種政治倫理學說,給中國人展示的境界太冷峻。人被網在森嚴的倫理等級秩序中,被要求主要考慮怎么對別人、對社會負責任。但個人存在的許多事,如饑寒溫飽、孤苦無援、生老病死、等等,儒學一般是不予解答的。即使是對這些問題有所觸及,也是用冷漠的口吻給予訓導。比如,要作在生年過半時達到“不惑”(大概也包括對生死問題不惑),生年將盡時要你“從心所欲不逾矩”等等,都是應該這樣應該那樣,而如何做到?就不知道了,你自己去考慮吧。殊知,處在迷惑中的人要不惑,須有人指引迷津才成,被生存重負壓得氣也難喘的人要從心所欲,談何容易?道學藐視儒家,討厭那張網人的網,所以,它教人棄仁絕義,棄學從愚,無己,無待,無礙,融于自然,游弋無窮,以此求得精神的解放。但是道學過于玄虛,對于習慣由外部可感力量來支配自己生活的多數中國人,這種實現自由的方式不易被接受。中國的士大夫以及搞學問、作詩、繪畫的人,在自己的藝術想象中,多少掌握了這種方式,為自己在現實生活的羅網之外造出一個新的宇宙——一個“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惲南田《題潔庵圖》語)的宇宙,一個“于天地之外,別構一種靈奇”(方士庶《天慵庵隨筆》語)的宇宙。但是,為生存疲于奔命的多數中國人很難做這種精神功夫。他們最容易接受的還是那個外于自己的佛。這個佛不象儒那樣漠視他們生活中的瑣事,那樣對他們的終極思慮置而不論。也不象道那樣要他們在自己心中構造自由世界。這個佛賜給他們一個在他們之外“早已”存在的神的世界,而這些神(尤其是在神與人之間互傳信息的觀世音菩薩)既關心他們的來世,也不責備他們對現世(如兒女情長、追名逐利、種谷收麥、升官發財)的眷戀,確立了一個在憧憬來世與善待今生之間實現平衡的原則。中國人是樂于接受佛的。同時,他們也不排斥儒的教導和道的境界。固然,作禪的功夫的多是中國的士大夫和古代知識分子;但是,信佛的中國老百姓也改造佛,創造融會儒與道的佛的完美形象。研究敦煌藝術,可以理會中國的禪在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百姓那里的聯系與區別。#p#分頁標題#e# 9.儒、釋、道都拿出了一套用來教導人如何剪裁生活的準則。都在告誡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你應該喜歡的,什么是你應該厭惡的。比如,儒要人積極用世,知其不可而為之;道則把追名逐利的世人看成同大鵬不可比擬的,只能是在蓬草間、屋檐下低飛的麻雀;釋教人善待今生,而主要還是教人修行來世。這三種對待生存的準則,在中國人的眼中,都有它們存在的必要,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都有它們實踐的影子。而在中國人的心里,他們在這三者之間,不斷地進行著艱難的選擇,因此,生存對中國人來說,是既豐富又貧乏的(不知實踐那個信條時就感到無比空虛),亦是既輝煌又暗淡的(徘徊往往使他們感到頹喪)。敦煌藝術以特有的歷史性的畫卷,向人們展示了中國人上述的生存徘徊狀況。 10.敦煌莫高窟處在一片廣袤的沙漠和戈壁的包圍之中。這是一種有寓意的現象。中國人在無垠的焦渴的包圍中找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樂土,在那里建造了一個類似“總非人間所有”的奇境、一個讓生命得到憩息的“家園”。那是佛的世界,也是人從焦渴的生存走向綠蔭遮崖、清泉潤石的仙境的所在。它在地理上同外界是隔絕的,但在中國人的心理上,它同外界又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它的雕塑、壁畫,那樣地揚溢著飛動的旋律,那樣地充滿著同佛的冷靜的冥想形成巨大張力的感性熱力,那樣地表現著人對于同這個存在家園相對應的現實世界的批判和肯定,怨恨和眷戀,想割舍又急切地要投入其懷抱的矛盾心理。它實際是中國人依戀世俗、改造世俗、從而使自己能夠親近世俗的熱情創造。她歷經滄桑仍然活生生地活動在我們面前,是她千年來不斷同她的創造者、膜拜者與欣賞者進行情感上的交流和有關生命真諦的對話的結果。 11.在敦煌藝術中有許多可以理出系統的世俗存在的符號(包括儒和道的概念、范疇)、藝術的符號以及佛的符號。這些符號是如何在敦煌藝術這個統一的系統中相互對立、相互轉換、又相互融和的?這是對敦煌藝術進行哲學研究的非常復雜和細致的工程。 12.可以把敦煌藝術寶庫看成中國人創造的希望人從中體驗生存形而上意義的“學校”。上述幾個符號系統轉換的奧秘,正是這個學校要教導“學生”從事破譯的主要課題。有多少去敦煌朝覲的人(無論是朝覲神,還是朝覲藝術),就有多少破譯這個奧秘的方法和答案,在這方面,藝術家,教徒,旅游者,都是平等的。用哲學的觀點看,敦煌藝術永遠是一種開放的藝術。有人用語言同她對話,有人寫出文章同她對話,有人不說也不寫,只是把對她的印象和理解輕輕地、深深地藏入心底,用心同她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