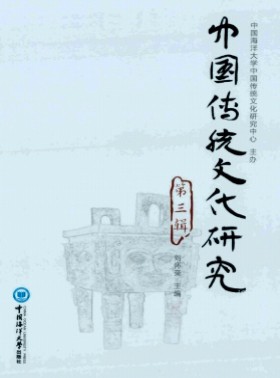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傳統繪畫的鬼形象,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鬼作為宗教中常見的形象之一,伴隨著宗教的產生而出現。從考古學研究來看,原始宗教產生于生產力和人類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舊石器時代后期。原始人的基本著眼點是食、繁殖和死亡,由此形成一系列與原始宗教有關的崇拜和習俗。原始崇拜歸納起來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自然力和自然物的直接崇拜,即以直接感覺到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當作崇拜對象;另一類是靈物和鬼魂的崇拜,即崇拜對象純系幻想出來的某種超自然物[1]。鬼魂崇拜隨著宗法制度一直相當完整地保存到民國時期,它們曾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宗教的核心,其他宗教和外來宗教只能與它調適。事實上道教依傍于它,佛教與它相融攝,民間宗教和信仰更是與它親和交融,即便是儒家也不能與它斷然絕裂[2]。所以,傳統繪畫作品中鬼形象屢見不鮮,首先是宗教直接影響的結果。 一、形象的宗教性 有關鬼的記載,早在《禮記•祭義》載孔子向宰我解釋講:“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論衡•論死》中講:“鬼者,歸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中國人認為,人死后可以存在兩個東西,一個是上揚的“神”,另一個是歸下的“鬼”,二者合稱之為“鬼神”。人類發展始終對自身的生死存有神秘感,于是有了魂魄鬼神的種種神秘說法和有關行為。人都有畏死求安的本能,“人之所以畏神者,以畏死耳”[3]。對死亡的恐懼而產生對鬼的畏懼。東漢以后,佛教的傳入,人們對鬼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佛教的因果輪回、三世在中國傳播,鬼和地獄便在人們觀念中占據相當的地位。佛教地獄中極為繁復,種種酷刑繁雜慘酷,遠勝人間牢獄,這加深了人們對鬼在地獄中慘狀的認知。因果報應是佛教的基本思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長期中國封建社會已形成一種普遍道德準則。 “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藝術來使人們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圖像說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4]由此可見,在宗教的作用下,畫“鬼”是以宣揚勸誡為目的,可以說,為宗教服務一直是中國早期傳統繪畫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國歷史上畫鬼的傳統源遠流長。早在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中就有相關的記載:“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意思是說要畫犬馬一類的題材最難,因為每天都能看到,畫得像不像人人都知道,而鬼魅一類的東西因為無人見過,即使畫得奇異古怪,也不會有人指責畫得不像。《后漢書•張衡傳》云:“畫工惡圖犬馬,好作鬼魅,誠以事實難作,而虛偽無窮也。”自漢代以來,畫鬼的畫家可以說史不絕書。南北朝隋唐五代宗教畫盛行,凡畫宗教畫的,除了畫神仙、菩薩外,無不兼能畫鬼。隋朝畫家孫尚子,專攻畫鬼,史稱“魑魅魍魎,參靈酌妙”[5],可見其畫鬼精彩多樣。唐朝張孝師善畫地獄,氣象陰慘。據說他曾死而復生,到過地獄,故善畫。吳道子就是看了張孝師的畫,創作了著名的《地獄變相圖》。唐代畫家吳道子,史稱“畫圣”,少孤貧,初為民間畫工,年輕時即有畫名,曾任兗州瑕丘(今山東滋陽)縣尉,不久即辭職,后流落洛陽,從事壁畫創作,開元年間,以善畫被詔入宮廷,歷任供奉。他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鳥獸、草木、樓閣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長于壁畫創作,據載他曾于長安、洛陽兩地寺觀中繪制壁畫多達三百余堵,奇蹤怪狀,無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獄變相圖》聞名于時。吳道子的《地獄變相圖》在宋代仍能見到,且有多種摹作、傳刻。宋黃伯思說道子所畫“變狀陰森,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這說明吳道子善于塑造富有特征和容易感染人們的鬼的形象,并以整個氣勢、氛圍給人以深刻印象。蘇東坡在《跋吳道子“地獄變相”》文中也說:“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這里說出了他看此圖的感受。 后人有《道子墨寶》,是宋時民間畫工畫稿,二十世紀60年代重印,笫27至40圖為地獄變相圖,觀其圖可略知吳畫原貌,如:第27圖畫一官被捉,將被執送叛罪;第36圖畫一老官被扭送;第37圖畫一官送判,并有挖眼、鋸殺之刑。這些畫面指向達官貴人,意指活著時他們作了孽,死后也同樣要入地獄受罪,這是吳畫很獨特的表現。就是在宋代官修的《宣和畫譜》中,也不能不提到這是一種別出心栽的創作。這里反映出吳道子有一定的平等思想,認為不論貴賤,善惡分明。據《歷代名畫記》記載,趙景公寺老僧講,吳道子《地獄變相》畫成后,“都人咸觀,皆俱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說的是長安眾人都去觀看,懼怕下地獄受苦,齊心向善,街市的魚肉都賣不出去了,因為佛教戒殺生。《道子墨寶》第31圖就畫一人,因屠牛在閻羅殿受審,圖中一鏡現出生前擊牛之狀,這就有警世之意。因此,《唐朝名畫錄》云:“京都屠沽、魚罟之輩見之俱罪改業者,往往有之。”說的是屠夫、漁夫見畫后都紛紛改業,惟恐殺生造孽,來世會遭惡報,進地獄受到制裁。地獄變相是宣揚宗教的,一幅作品能產生如此感染力,讓凡夫俗子領會佛教精義,其形象的釋意可謂是出神入化。元代畫家朱玉善畫佛經引首,他曾作《鬼子母揭缽圖卷》、《地獄變相圖軸》等,都是一幅幅佛教意義的棄惡從善的說教圖。《鬼子母揭缽圖卷》是描寫佛降服吃人鬼子母的故事。鬼子母是佛經中的女惡鬼,自己生有五百個孩子,但每天還要食王舍城中的幼兒。釋迦佛將鬼子母的一個孩子隱于佛缽,鬼子母悲泣求之,受釋迦教化而改惡從善。畫中鬼子母的孩子被鎮缽中,鬼子母神情憂傷,眾妖魔搖旗吶喊,奮力搶救,佛穩坐蓮花臺上,神態安祥,靜觀事態,一動一靜、一邪一正,將畫中各種人物的心理神態表現得淋漓盡致。線條挺拔,古樸工細,墨色沉著,筆筆遒勁,體現出畫家精湛的繪畫技巧。繪畫依附于宗教,既有了宗教意義,同時又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縱觀藝術史、宗教史乃至文化史,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宗教的刺激,人類的藝術史和文化史才能發展,這正是藝術產生的重要途徑和發展的動力之一。 #p#分頁標題#e#
二、形象的隱喻性 鬼在傳統文學藝術中的地位和作用,實在是顯而易見的。文學作品中說鬼論鬼,其意義遠遠超過宗教的目的。在《太平廣記》、《瑩窗異草》、《子不語》、《聊齋志異》等著作中,都賦予了鬼更多的含意。同樣,在中國繪畫史上也有眾多畫家畫鬼的目的并非真正意義上敘述鬼的本意,而是借畫鬼傾吐對社會的認識,更多意義上是借鬼諷今。 宋末元初是中國歷史上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時期,蒙古統治者恣意踐踏中原文化,廢除科舉制度,文人在生活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摧殘,于是他們或隱跡山林,或縱情聲色,或寄情于文藝作品,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氣。元初文人畫家龔開便是當時的一位杰出的畫家代表,他以古拙沉厚的畫風和寓意深刻的內容在中國繪畫史占有一席之地。他亦從學習吳道子入手,但筆法粗放,喜歡畫“墨鬼”,尤其以畫鐘馗而負盛名,《中山出游圖》是其代表作品。《中山出游圖》描繪的是鐘馗及其眷屬乘肩輿出行,眾鬼抬轎,鬼氣森森卻又趣味盎然。他的畫帶有辛辣的諷刺意味,元代的評論家認為不可“以清玩目之”。根據他的身世,可能出身于寒士之家。 龔開生性沉靜、澹泊,身高八尺,年長時雪髯及腹,行走如飛,能食五鼎肉,“頎身逸氣,如古圖畫中仙人劍客”。他的精神特征集中了文人的飄逸和劍俠的豪爽。宋末時期,正當龔開的青壯年時代,這個階段正是南宋被蒙古勢力逐口鯨吞的時期。龔開的生長地淮陰是歷代兵家的必爭之地,“少負才氣”的龔開銳意以建功立業來“贏得金創臥帝閑”。南宋滅亡后,龔開深隱不仕,賣畫為生,真正展現他的抗爭力是借繪畫宣泄對元朝統治的憤慨,鐘馗擊鬼是他的主要繪畫題材。《中山出游圖》卷,畫鐘馗與小妹各坐一肩輿,在鬼卒的簇擁下乘興出游。全圖可分三段,卷首的鐘馗回首與妹相互呼應,將卷首與卷中銜接起來,馗妹身后的一侍女回眸尾隨而來的鬼隊,最后把讀者的視線引向卷尾。作品的構圖似不經意,雜亂的隊列全憑相互間的內在聯系統一起來,兩乘肩輿呈八字排開,打破了因橫線過多而產生的呆板。人物在平中見奇的構圖里更是奇中見奇,鐘馗豹鼻環眼,髯須叢生,猛氣橫發,在炯炯的目光里顯示了文人的智慧和瀟灑的氣度。鐘馗妹和兩侍女以濃墨代胭脂,自目下到頸根由深變淺,嘴唇留白,面部的內輪廓以白線空出,人稱“墨妝”,鬼分男女,大多牛頭馬面,卷末的鬼卒們扛著卷席、酒壇,挑著書擔和待烹的小鬼,他們瞠目凝視、舉止痙攣,急行的鬼隊與緩行的肩輿不僅在節奏上產生變化,而且反襯出鐘馗氣吞萬夫的威力。怪異荒誕的造型與作者奇譎的表現手法合璧。鬼卒的用筆短促簡勁,頓挫有致,勾畫的肌肉頗合人體解剖,作者以墨畫鬼,手法多樣,鬼態各異:有的勾勒后以干筆皴擦出鬼毛和陰陽,也有雙勾后用淡墨渲染出鬼骨,還有以焦墨作沒骨鬼。龔開把這些面目猙獰、形態怪異的牛頭馬面比作異族的統治者,鐘馗比作自己,顯然蘊涵了掃除幫兇反元復宋的愿望。此畫被不少名人題詠,點破其畫意。有人題道:“世之奇形異狀。暴戾詭譎,強弱知啖,變詐百出,甚與妖魅者不少。髯翁之畫,深有旨哉?”另一名文士周耘更進一步指出龔開畫意“:寫中山出游圖,髯者顧盼,氣吞萬夫,與從詭異雜沓,魅魑束縛以待烹。使剛正睹之心快,奸佞見之膽落,故知先生之志,在掃蕩兇邪耳,豈徒以清玩目之?”[6]以上幾段題詠都明確點出畫中所蘊含風骨,這種寓意手法,是元初失意畫家們抒胸達意的重要手段。清代畫鬼者甚多,“揚州八怪”中的畫家黃慎、金農、羅聘和后期畫家錢慧安等都畫過鬼。黃慎畫過《有錢能使鬼推磨》,金農也畫了一組《雜畫冊》,其中的一幅便是《山魅林憩圖》,畫面上一片濃蔭,樹叢間隱隱探出幾個淡淡的鬼影。羅聘畫過《鬼趣圖》,錢慧安也畫過《有錢能使鬼推磨》等,都是借畫鬼來諷刺人間不平。 黃慎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是幅諷刺黑暗世態的作品。著重刻劃了一個推磨的似人而鬼的東西,見錢眼開、垂涎三尺的丑態,而不僅僅表面化在“鬼”字上做文章,單純把它畫成一副猙獰可怕或奇形怪狀的樣子。清末畫家錢慧安畫過《有錢能使鬼推磨》、《鐘馗殺鬼圖》、《鐘馗役鬼圖》等作品,其中的小鬼多是西裝革履或洋人軍服,形象也多是高鼻子卷頭發的洋相,以發泄對當時入侵中國的形形色色的洋鬼子的無比仇恨和憤慨。羅聘的《鬼趣圖》作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后世也多以此八幅作為羅聘的代表作之一,甚至誤認為羅聘只會畫鬼,羅聘通過這個作品很好地表現了他的“怪”。羅聘具有很好的藝術創作功底,他自己也在道釋人物畫、神佛方面有所見長,但羅聘獨獨畫“鬼”。一方面,這與中國傳統的鬼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另一方面,羅聘畫鬼也受到了其它幾個方面的影響。前面提到了中國傳統的鬼文化,那么具體在羅聘所處的時代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發現鬼之所以成為當時畫家筆下的常見題材是與清初的諷刺文學思潮不無關系的,就在沈大成為《鬼趣圖》題跋的乾隆三十一年,中國文學史上不朽名著《聊齋志異》開雕付印,可以說羅聘畫鬼或多或少受了《聊齋志異》的影響。 在郭祥伯題《鬼趣圖序》中記:“圖凡八幅。其一,澹墨黯昧,隱隱有面目肢體,諦視始可辨。其二,一鬼短衣僂而趣,一鬼奴而從,裸上體,以手拄腰,骨節可數。其三鬼衣冠甚都,手折蘭花,攬女袂;女鬼紅衣豐鬋,昵昵語;傍鬼搖扇耳聽。其四,一矮鬼扶杖據地,紅衣;一小鬼捧酒殘,就矮鬼吻,吻哆張。其五,唯一鬼,瘦而長,垂綠發至腰,左手作攫拿狀,右手揗其發,手長與身等,足布武越數丈,腰腹云氣蒙之,身純作青色。其六,長頭而僂者一鬼,身不及頭之半;頭之前鬼二,一銳上,一混沌然若避、若指、且顧。其七,風雨如漆,一鬼俯首疾走,一鬼張傘,其前一鬼導,其后一鬼,頭出傘上,若依倚疾走者。昏黑淋漓,極惶遽奔忙之狀。第八,楓林古冢,兩髑髏齒齒對語,白骨支節,巉巉然也。”[7]這些看了使人恐懼又發笑的《鬼趣圖》,刻畫的到底是誰?是不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有人說羅聘畫鬼是因他能親眼見鬼,吳谷人說他“眼有慧光,洞知鬼物沉冤地下。”蔣子延說:“生具異相,碧眼雙晴,洞見鬼物,白晝不驚。”[8]而羅聘在《香葉草堂詩存》中《寄別紀半魚》七絕二首之一云:“莫管人間有別離,君真褦襶我真癡;定知后夜呼燈起,忽憶狂夫說鬼時。”又《秋夜集黃瘦石齋中說鬼》五古云:“秋室昏孤燈,書棚墮饑鼠,狂鬼若無人,挪揄來三五,我豈具慧眼,惡趣偏能睹。”從這兩首詩來體會,羅聘并非由于生理上的特殊,所謂“我豈具慧眼”。只要“君真褦襶我真癡”,就會“忽憶狂夫說鬼時”,也會“惡趣偏能睹”的[9]。#p#分頁標題#e# 羅聘處于乾嘉時期,滿漢官僚結黨爭權,趨炎附勢,貪污罔法,欺壓百姓。百姓民不聊生,羅聘本人妻死而無錢下葬,于京返揚州而無盤纏,“空有千秋業,曾無十日資,欲歸歸未得,何以慰兒癡”,“一身道長,半世饑驅”[10]。所謂“乾隆盛世”,對老百姓來說,卻變成了撲朔迷離,陰氣森森的鬼世界。蔣仕銓在《鬼趣圖》系列的第二幅畫上題詩如下:“餓鬼啾啾啼鬼窟,不及豪家廝養卒。但能倚勢得紙錢,鼻涕何妨長一尺。”[11]蔣仕銓把羅聘的畫闡釋為對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貧富關系的批判,這一觀點今天仍受到一些中國評論家的贊同。羅聘的《鬼趣圖》同時也是對官僚腐朽的一種極隱晦、曲折的諷刺。如第四幅、第七幅、第八幅畫面中可看出,是對那些“蠅營狗茍”的官僚士大夫荒淫無恥、惶遽奔忙諸丑相的揭露。身處于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時代里,正直的文人們如蒲松齡、羅聘等人,雖然對這種社會現狀不滿,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不可能認識到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本原因,更不能把這種不滿情緒表現為正面的、公開的反對,只能通過文藝作品曲折地反映丑惡的現狀,表現他們的“孤憤絕俗”,或者借題發揮,諷刺這個丑惡的社會。 《鬼趣圖》一出,羅聘果然在京城博得了不小的名聲。用現在的話說,《鬼趣圖》可謂是羅聘投向社會腐朽的一柄匕首。當然,這自然會招來一些人的嫉恨,所以,當時就有一位羅聘的老鄉、大鹽商出身的程晉芳勸他:“斯圖即奇特,洗手勿輕試。”但掩飾得再巧妙,終究還會弄出麻煩來,于是勸羅聘金盆洗手,趕緊回家。“鬼”形象作為中國傳統繪畫中的重要題材,由早期的宣揚宗教思想為宗教服務,強調宗教性,發展到后期的通過隱喻手法達到感時傷世、諷喻時事的目的,具有社會性,使“鬼”形象得到進一步的提升,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性,拓展了繪畫藝術的題材和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