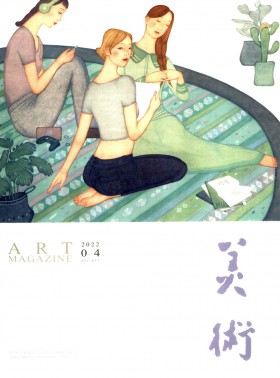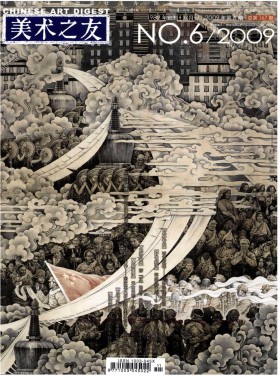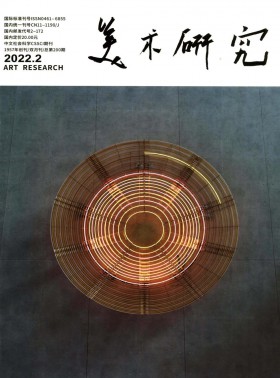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美術史學理論管理發展,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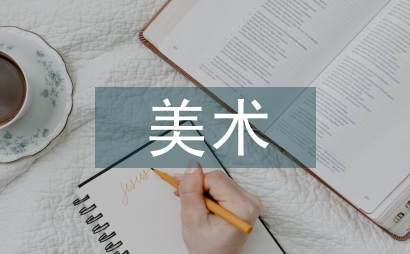
“”與民間美術———從明清補服圖案及制作工藝看民間美術與上層美術的相互影響 美術史學作為史學的一門類學科,正越來越為美術學界所關注。對于美術史與美術史學的關系、美術史學與美術史料的關系、美術史學研究方法論等一系列問題的探討,美術學家見解不一。 一、史料與史學關系的歷史溯源 史料與史學的關系隨著史學研究的發展,也經歷了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以史料作為歷史證據的學術風氣一直沿續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司馬光、歐陽修、顧炎武、錢大昕、龔自珍……歷代史學家無不對文字與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證有著獨到的看法。 顧炎武在批判明學空談的學術思想的基礎上,提倡“治經”,并總結了一整套治學思想與方法,如資料搜集、音韻訓詁、考據等等,開清代求真求實之學風。龔自珍本著其廣闊的史學視野,不僅重視已整理的文字資料,同時還提出要對尚未整理的文字記錄、社會制度和風俗、文化等加以重視,為近代史學奠定了基礎。清代的乾嘉考據學即是史料與史學關系密切之明證。 19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工業化浪潮的涌進、科技革命的巨大進步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不斷世俗化,自然科學中的理論和成果豐富并充實了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促使史學不斷尋求史學研究的科學化和學科化,實證史學應運而生。19世紀是西方史學高度發展的時期。以德國著名史學大師蘭克為代表的“科學”與“實證”的史學開西方近代史學之先河,成為19世紀西方史學的主流。蘭克以其對原始資料的執著追求,及對之進行嚴格的考訂與辨析,奠定了其史學方法論的基礎。正是他,把歷史學當作一門通過搜集與辨析文獻證據,并依靠這種經過辨析的文獻證據使客觀歷史在文字上還其真相的學問,因而獲得“近代科學歷史學之父”的聲譽。雖然蘭克一方面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十分注重具體的、深入的史實,即真實不謬的個體;同時他又是一位歷史理論家,致力于從個體之中揭橥出一般(或整體),即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中尋求歷史發展的統一性。 “這才是他作為西方歷史主義最偉大的實踐者的全部形象,也是他的史學方法論的全部內容。”[1](P24)受到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發展的影響,國人中的開明之士力求從知己知彼、師夷以制夷的角度和目的去認識西方科技,力求從觀念、知識上借鑒與趕超西方文明。史學界提倡科學的史學,正是適應了這一渴望進步、慕求西化的思潮,以科學態度和實證精神窮究自然,從而也就促成了史料學派的產生。 20世紀初,蘭克史學風行于中國史壇,而為引蘭克及其學派進入中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當屬“中國的蘭克”———傅斯年先生,同時由他為主要代表并出現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史料學派,在史學界影響長達半個多世紀。傅斯年先生曾于1923年至1926年就學于德國柏林大學哲學院,深受當時德國的學術空氣和語言考據學派、蘭克學派的治史理論與方法論的影響,服膺于蘭克學派“崇尚史料,如實直書”的主張。回國后,他立即在“史學便是史料學”、“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宗旨下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并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闡明自己的思想:“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2](P276)傅斯年的史學思想繼承并吸收了近代西方實證主義的史學思想和我國清代考據學客觀求實的理論方法。 20世紀以降特別是二戰結束后,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由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史學”即“搜集和整理史料或權威的陳述來構造歷史”從而“放棄自身的批判精神”的治學方法被指責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3],并受到西方新史學派的猛烈抨擊。新史學提倡重視理論概括和解釋、提高歷史認識與解釋的準確性,反對只局限于科學實證和重視文字資料。在中國,隨著西方新史學的引進,“史學便是史料學”的理論也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周谷城曾談到:“‘史學便是史料學’這話于史學界有益,但不正確。治史的人往往輕視史料;其實離開史料,歷史簡直無從研究起。歷史自身雖不是史料,但只能從史料中尋找而發現出來。謂‘史學本是史料學’,至少有糾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學界有益。但有益的話往往也有不正確的,謂‘史學本是史料學’,同時自不能不承認史料就等于歷史。其實史料只可視為尋找歷史之指路碑,只可視為歷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跡,卻并不是歷史之自身”。[4](P2)還有的學者認為史料只是一切關于歷史的材料,是在過去的社會中人類各種活動的記載;而史學卻是從對這些材料的研究中,去考察人類一切活動的規律,并指出可以為現在的人類社會進行指導與參考的地方。不僅史料不是史學,就是整理史料也不是史學。而且,除了史料之外,還有史觀、史論、史學研究方法都應該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以美術史料為美術史研究的歷史回顧把美術史料作為研究美術史的方法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早已盛行。美術史料大致可劃分為圖像史料與文獻史料。圖像史料主要包括美術作品和遺跡實物,文獻史料主要包括有文字記載的美術類著述。 在西方,很早就注意到對美術史料的運用。文藝復興時代,人們更多地是注重對文字文獻的利用。 18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學者認識到圖像在歷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19世紀西方史學的高度發展為美術史學的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美術史學的發展主流或許可以說是實證主義的。科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對美術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解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美術史學家布克哈特曾作為蘭克的門徒、里格爾則師從蘭克的高足,他們都在處理史料方法方面受到過嚴格的訓練。 西方學者一致承認圖像是歷史文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比文字資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歷史原貌。“只有當一位史學家開始真正地意識到視覺藝術也屬于歷史資料,并能夠有系統地利用它們時,他才能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更加穩固的基礎之上,從而更加深入地調查和研究曾經發生過的事件,”[5]19世紀德國哲學家德羅伊申看來,“遺跡”和“資料”是我們可借以了解并認知歷史的兩種材料。#p#分頁標題#e# 所謂“遺跡”是指各類藝術作品、銘文、紋章和錢幣等遺物,而“資料”則包括了所有人類可以理解的并由此形成、流傳下來的、為人類記憶服務的一切。“遺跡”是第一手的材料;而“資料”是觀點的觀點,它可以是第三手、甚至是第四手的材料,因而“遺跡”比“資料”更值得信賴。總的說來,西方對美術史料的使用還是重圖像輕文獻。當然,許多學者雖然強調美術史料的重要作用,但他們利用美術史料作為美術史研究的方法,也只是作為眾多研究方法之一種。 中國早在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就有“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像,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也,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此之謂也,善哉。……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樂事”[6](P10)。這段話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傳統美術史學觀念中美術之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正說明圖畫(圖像)比記傳、賦頌(文字)更具有教化和揚善抑惡之功用。鄭樵《通志?圖略》一書里指出:“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圖像)與書(文獻)互為印證;同時又指出“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矣”[7],強調對圖像的重視,把“圖像證史”作為一種實學。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也極為重視資料建設,將資料建設看作建設本國藝術史之‘學術獨立’的重要前提[8](P40),提倡利用本國畫史、畫論、圖像等學術資源,建設本國藝術史的系統。王國維先生提出了將充足的地上與地下資料結合起來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謝稚柳先生曾說過:“我們搞美術史,首先要看實物,而后才能從實物、資料再到文字。我研究美術史,要從實物到文字,因此,有資料、實物才自己寫文字,結合實物”。他認為,美術史研究要根據圖像實物的畫風、畫格,即它的筆墨、表現形式、風格及其所屬時代、流派和格調,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果沒有一定的實物作為依據,就要靠歷史上的記載、書本上說明的東西。 這就是文獻史料。事實上,中國歷代的書畫著述史籍,大多也是根據實物作品編錄、撰寫而成的。在童書業先生看來,研究繪畫史,自然應當以文獻為主,實物只能作參證之用。因為“我們不能依據偽造的古畫來亂說繪畫史,文獻是有流傳淵源的,作偽的可能性當然比較少”。[9](P112)他所重視的更多是文獻史料而非圖像史料。其實,文獻史料和圖像史料在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中同樣具有很高的價值。但是美術史料終究還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從文獻史料看,中國古代美術文獻數量之多,種類之廣,在世界上堪為首屈一指。 各類畫學著述、藝術理論等歷史文獻中不乏經典之作,有精到的見解,但同時在不少著錄中也存在著誤收偽造或真謬雜處之作,使史料的真實性與學術價值大打折扣。而對文獻史料的利用,也是美術史研究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古代歷史文獻常以簡單的陳述句和簡潔的文字表達并摻以著錄者的主觀意念,時有語言多義且語意不清,而且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內涵,如“氣韻”之“氣”在南北朝時期與唐朝就有不同的涵義,讀者對作品的感受很難從理論上得到引導和支持,常常依靠自己的經驗積累和主觀判斷;藝術評論中多使用比喻句、排比句和華麗的形容詞藻,評論語言相差很大。如果研究者不明其義、另有他解或把著錄者的主觀思想當作美術作品風格表現的創作基礎,就無法對作品形式準確把握,進而會影響到對美術作品的正確和深層次的認識。此外,文獻史料是否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是美術史研究中需要對之進行鑒別的。從圖像實物史料看,“以圖證史”對美術史研究的意義是無可非議的。然而當西方學者把它作為研究美術史的可靠資料并加以充分利用的同時,這一方法也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評。荷蘭文化史思想家赫伊津哈就指出:“過分強調視覺圖像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會導致歷史科學的毀滅。……史學家不應該一味地把視覺圖像當作嚴肅的歷史分析的基礎,這類材料不能代替真正的歷史思考。當今歷史寫作水平的下降,原因就在于濫用圖像”。[10](P64)在中國,從古到今傳世的許多千古名作中大有贗品與模本,如果不加甄別地一律當作真實的圖像史料來使用,只會給美術史研究帶來不利的結果。總之,史料的真實與否、全面與否、有否學術價值,都直接影響到美術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因此,對文獻本身的真偽及流傳需要做詳細的考證,并廣泛借鑒前人已有的成果和結論;對各時代文獻的語言表述要做正確、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臆斷的分析,并結合同時代的藝術主張、藝術思潮和作品來進行探討。這就需要既重視文字的文獻,又要重視作品和器物。研究無文字文獻的史前史,主要依靠對實物的分析,同時對古代的史論著作也要結合實物和作品本身。 三、中國美術史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 中國美術史學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伴隨著繪畫實踐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繪畫理論。它包括畫史、畫傳、畫學、畫法、繪畫品評、繪畫鑒藏及畫家傳記年譜、箋注疏證等各種形式,而以專著、隨筆札記、畫跋、題畫詩等為主要體裁;以品級品評、畫錄等為主要研究形式;并重以批評的方法。內容之豐富,題材之廣泛,形成有民族特色的繪畫理論體系。最早可追至東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論畫》、《畫云臺山記》、宗炳《畫山水序》,到南朝謝赫《古畫品錄》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品評繪畫的重要著作;唐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宋《宣和畫譜》、明董其昌之《畫禪室隨筆》、清石濤之《畫語錄》等都是古代極具學術價值的繪畫論著。繪畫史方面,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不僅是一部重要的繪畫理論著作,也是中國最早的繪畫史著作。唐以后,繪畫史著作日趨增多,宋代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明陳繼儒《書畫史》、姜紹書《無聲詩史》……有清一代,繪畫史著作更是數不勝數。這些理論著述的作者們多偏重于主觀感悟性、經驗性、寫意性、品評性、鑒賞性和陳述性,從創作體驗的角度論者多,而從美術史角度勘察者少缺乏學術的獨立性、思維的深度性、邏輯的思辨性以及抽象的表達、系統的闡述、嚴密的論證和客觀的分析。畫著往往成為畫家實踐經驗的記錄,使得繪畫理論依附于繪畫實踐。#p#分頁標題#e# 在古代的畫史中雖然已經有了“史”的內容,但仍被涵蓋在“文論”、“畫論”之中,“在古代文藝理論中還沒有清晰的‘史’作為學科分類的意識”[11]。 20世紀初西方新史學作為“關于歷史的性質及其發展的一種學說”、“對史學家所著意研究的對象本身的一種看法”、“關于人類歷史研究與其他人文學科研究(有時涉及到自然科學)之間關系的一種見解”[12](P38),對中國社會思想與人文環境產生極大影響。其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的不斷創新,使得傳統史學、文學不得不進行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國美術史學隨著現代史學理念、美術觀念的引進也邁入現代史學的門檻。“美術改良”的呼聲漸漲,繪畫的西洋化與傳統的國粹主義之間論戰紛起、矛盾激烈。康有為對歐美繪畫心悅誠服、大加贊賞,曾用“抬槍與五十三升大炮”來比喻中國畫與西洋畫之優劣,還得出“吾國畫疏淺,遠不如之(意大利)。此事亦當變法”之結論;陳獨秀感嘆于“中國畫學至國朝衰弊極矣,豈止衰弊,至今郡邑無聞畫人者。其遺余二三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數筆,味同嚼蠟,豈復能傳后,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國人豈無英雄之士應運而興,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13],力倡“美術革命”,以復古為更新,尊唐宋繪畫為正宗,旁取歐西之法,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以洋畫寫實精神改造中國畫。徐悲鴻、林風眠、傅抱石、陳之佛、潘天壽、吳冠中等現代中國畫變革的先行者,在西方藝術的氛圍中,則認識到東方藝術的精華,獨立體悟到中西藝術相通的境界。他們融合中西方藝術,傾一生之心力從事美術理論與實踐的探索。 西方美術史學借助自然科學中的進化論、生理學、心理學等理論和社會科學中的史學、考古學、哲學、美學等理論,充實并豐富了美術史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中國美術史研究依托于西洋美術史研究的思維與方法,掌握了近現代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利用人類學、考古學、文獻學資料加以討論。自陳師曾的《中國繪畫史》、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傅抱石的《中國美術年表》、滕固的《中國美術小史》等著作始,開始出現不同于古代文論、畫論的現代意義上的“史”的體例和觀念。由于較明顯地受到日本美術史的影響,這些史著基本上套用了日本繪畫史的敘述模式,甚至在有的史作中“克隆”了日本版繪畫史的基本內容。當然,鄭昶的《中國畫學全史》或許是一個不受日本影響的例外,它以具有開創性的分期意識、新穎獨特的體系和體例及系統的闡述被譽為民國時期的不朽之作。但直至建國以前,這一“日本模式”[14](P10)一直存在于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并影響著中國美術史學的發展。 建國后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美術史研究一方面仿效蘇俄的美術體制,接受蘇俄文藝理論和美術思想,在這一時期特別是20世紀50、60年代,斯大林時期的美術思想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概論》及一些雜志成為中國美術理論者的基本讀物。另一方面,繪畫史學已有比較的成分;同時,提倡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反映社會、反映時代、反映政治,使美術史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都帶有較為濃厚的社會政治斗爭色彩和階級色彩。繪畫的意識形態性質成為美術史研究的主體內容。 20世紀80年代以后,修史立論,述古論今,以繪畫評論和批評來反對繪畫常識性、知識性的研究,美術史研究、美術理論、美術批評迅速發展,中國美術史學界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隨著國際間文化交流的廣泛開展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現代化的要求,中國傳統美術史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美術史研究的方法也發生了多方位的變化。美術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及其研究方法論越來越受到美術史學界的重視,如何從“美術史”的觀念進入到“美術史學”的觀念從而進入到一個學理的高度,是當代中國美術史學工作者關注的重點。“史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舶來品,它是對歷史研究本身進行的研究,是一種理論框架、方法研究;美術史學則是對美術史研究的學理分析和哲學思考以及對美術史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從中國美術史學發展的現狀看,國外學者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果,而國內美術史的研究卻極為薄弱;比照歷史學學科的發展仍有很大的差距;至今已出版的真正有學術價值的美術史著作也少覽其蹤。 中國美術史學要更好地發展,就應當站在學術的高度思考問題,進行創造性工作,以建設美術史學的學術與理論構架。美術史學家既要具備廣博的本學科及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和考據、述史的功夫,同時也要具備較強的邏輯思辨和理論闡釋的能力。歷史學研究的方法眾多,美術史學研究可以借鑒歷史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借鑒國外研究中國美術史的方法與成果,“參用一二,亦其醒法”;也可以借鑒姊妹藝術史研究的方法。 其一,中國傳統的史學方法曾經為史學的發展 做出過重大的貢獻,然而在當代的文化藝術語境下,中國美術史學應該更多地吸收現代美術理論和西方美術史學的研究方法,從而與國際接軌:從傳統的經驗性的感覺描述上升為較系統的理論分析;從史實的陳述走向史實意義的理性認識與解釋。將作為傳統美術史學基本方法之一的利用文獻或文物考異或考證方法與現代科學技術和研究方法相結合。 其二,美術史學要有一定的美學思想為基礎。 將美學基本原理運用于美術史研究中,可以豐富美術史研究的方法和內容。美學不能代替美術史學,但二者的關系又十分密切。美術的歷史包含了人類審美活動、審美趣味和審美意識發展的歷史,美術史的研究就是對具有審美意識的人與其審美活動即認識具有審美價值的客觀對象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而美學正是滲透在這種關系之中。黑格爾的《美學》、丹納的《藝術哲學》等美學著作無不對藝術的歷史與理論進行了闡述;而在中國古今的藝術理論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學思想,顧愷之、謝赫的形神論,宗炳的暢神論,蘇軾的文人畫理論,傅山的美丑巧拙論……因此,要從美學的高度探索藝術的特征與規律,在美術史學界開創一種新的學術風氣。#p#分頁標題#e# 其三,美術史學不是孤立的,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它需要在歷史的、文化的、學術的大背景與環境下,以歷史、哲學、美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為參照,建立起自己科學、獨特的研究方法論。同時,還應當跨越國界,建立起世界的、比較的美術史學觀念。 四、余論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史料的運用是史學生存的必要條件,并以其科學性在史學研究中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同樣,美術史料永遠只能是美術史學的基礎,而代替不了美術史學研究本身。胡適先生曾經指出,“史學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目前對美術史料的利用已不僅限于單純地對圖像實物與一般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對社會史、文化史、風俗史等各類歷史材料以及早些時間的報刊雜志、文人筆記等其他學科領域的資料的研究都有助于美術史學研究。史料不是史學研究的充分條件,它僅僅只能作為“一種素材的存在而不具有絕對的意義”[15]。以圖像實物證史、以文獻史籍證史,只是美術史研究的一種方法,不但不能涵蓋歷史研究方法的全部,而且美術史料永遠也不是美術史學。從理論和學術的立場,加強美術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指導,才是中國美術史學發展的必然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