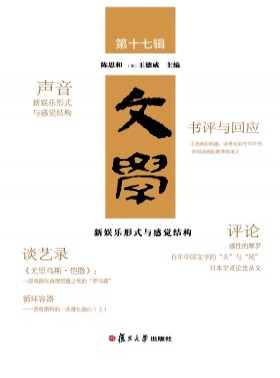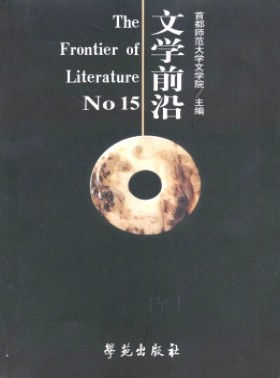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學與電影整合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 中國電影在改編文學作品中起步和發展 在中國電影的創建過程中,劇本問題首當其沖,文學在中國電影發展各階段的關鍵節點上,皆施以援手。我國首部自拍電影《定軍山》為京劇劇目,而且1905年至1908年所出品的8部電影,如《長坂坡》、《金錢豹》等,全部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我國首部彩色電影《生死恨》由梅蘭芳、齊如山改編自明代傳奇《易鞋記》;新中國拍攝的第一部彩色電影是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改編自魯迅同名作品《祝福》。并且,每當新電影樣式出現之時,電影公司和電影制片廠大多喜歡選擇改編文學作品,1910年代、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文學作品電影改編熱都體現了這一取向。 檢索《中國影片大典》及《中國無聲電影劇本》可知,1913年以前的電影大多為舞臺劇的實錄,如《定軍山》、《長坂坡》等作品。正如周曉明在《中國現代電影文學史》中所指出的:1920年前,中國電影沒有事先寫好的腳本。《定軍山》只記錄了京劇演員譚鑫培在該劇中幾個動作性較強的場面,不需腳本。《難夫難妻》具有明顯的紀錄性質,可以推論至多有一個事先想好的故事或簡單幕表。另據包天笑回憶,鄭正秋曾告訴他,寫電影劇本簡單得很,只要想好一個故事,把情節寫出來,曲折一點,且有離合悲歡的主旨就行。篇幅如短篇小說。他們再自行把故事擴充,加以點綴,分場分幕,就成了劇本。這表明,早期電影無正式的電影劇本,其腳本幾乎就是文學作品本身。 按通行的分期法,1896至1931年間是黑白無聲電影階段,也可稱為中國電影的萌芽和發展期。1931到1949年間,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成熟期,其中1948年出現彩色電影。1949年以后為中國電影的進一步發展期。考察上述三個階段的電影,以《中國影片大典》所錄電影為統計數據,可以發現,1905至1931年,共出品了600多部電影,其中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在150部以上。1931年至1949年,共出品900余部電影,其中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有180余部。1949至1976年共出品電影800余部,其中,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有400余部。1976至2010年,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在比例上已下降,但在數量上仍有增加的趨勢。這些數據表明,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電影在中國電影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中國電影在改編文學作品中起步和發展。 改編成電影的文學作品有多種類型,既有長篇、短篇小說,也有戲劇和散文;既有新文學作品,也有古代文學作品;既有中國作品,也有外國作品。 不少現代長篇小說被改編成系列電影,影響較大者有《荒江女俠》(顧明道原著,1930至1936年出品)《、啼笑因緣》(張恨水原著,1932年出品)等。 被改編成電影的新文學作品也不少,如《春蠶》(茅盾原著,1933年出品),《雷雨》(曹禺原著,1938年出品),《家》(巴金原著,1941年出品),《祝福》(魯迅原著,電影名《祥林嫂》,1948年出品)。古典文學名著不但被改編成電影,而且還不斷被重拍,《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即如此。還有少數外國文學作品也被改編成了中國電影。如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1920出品的《車中盜》改編自林紓翻譯的《焦頭爛額》(該小說為商務印書館出版,有1914、1920年等多個版本),明星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的《空谷蘭》改編自日本黑巖淚香的小說《野之花》。這些現象表明,文學對電影的援助并不限于特定文學類型,它所蘊含的電影資源是立體而全方位的。 中國電影在改編文學作品中起步和發展有多方面的原因。1895年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成功公映《火車到站》、《水澆園丁》等影片,標志著世界電影正式誕生。與世界電影相比,中國電影的發展晚了10余年。所以當中國開始自制電影時,如《火車到站》般的簡單實錄社會場景的電影,顯然已不能滿足觀影的需要。而當時,中國電影專業人員奇缺,電影制度也是一片空白。這迫使它不得不從其它藝術中尋求資源。于是,同樣具有表演藝術特質的舞臺劇成為首要的借鑒對象。 事實上,1940年代以前出品的電影,除了戲曲電影,很多影片都帶有戲劇表演的痕跡,這從《少奶奶的扇子》(1928)《、啼笑因緣》(1932)《、神女》(1934)等影片中都可看出。 電影制作成本巨大,為使其持續發展,就必須考慮消費市場。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單單改編作品的作家名字就足以在廣告上確保電影的質量。正因為文學名著可以為電影提供盈利的保障,因此,電影公司偏愛文學名著,《西游記》、《三國演義》等名著的改編一直長盛不衰,甚至至今仍活躍在電影銀幕上。朱瘦菊在1926年推薦將《西廂記》改編成電影時即表現出了這種見識,他說,《西廂記》文字之茂美、情節之委婉有如春花秋實各擅勝場,大中華百合公司擬將其搬上銀幕,拍成之后必將令讀者驚喜不已。 此外,對創建中的中國電影而言,作為新生的藝術樣式,它在表現社會和民族方面力道相對較淺,而體制完備的文學恰好可以彌補其缺。作家們的筆力也很可能在長時期內都普遍超過電影編劇們。 再者,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還可以引領電影潮流甚至反過來引領文學潮流,因此也備受電影公司青睞。如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火燒紅蓮寺》系列電影改編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該電影不但拯救了明星影片公司,而且還引發了武俠神怪電影熱潮。當時,《火燒紅蓮寺》一直拍到第19集。1929年出品的電影以“火燒”命名者有《火燒劍峰寨》、《火燒青龍寺》等4部,后又有《火燒白雀寺》、《火燒平陽城》等“火燒”類電影出現。其它類似的電影如《江湖情俠》、《荒村怪俠》等有200余部。更意外的收獲是:借助電影的聲勢,武俠小說的創作和閱讀也形成熱潮,武俠小說由此成為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重要品種。 二 文學助電影完善語言符號系統 在中國電影發展的各階段中,電影都積極主動地使用了文學符號。甚至可以說,帶有文學性的文字已成為電影的固定結構元素,文學幫助電影完善了它的語言符號系統。#p#分頁標題#e# 對文學符號的使用一直伴隨著電影的發展,無聲電影、有聲電影、彩色電影皆如此。無聲電影如吳永剛導演的《神女》(1934)、程步高導演的《春蠶》(1933)、孫瑜導演的《體育皇后》(1934)等電影中都可見明顯的文學符號。《體育皇后》的開頭即為文字:“一艘從浙江開來的船到了它長途賽跑的終點。”結尾也有字幕:“一切不合理的貴族的,個人的錦標賽,新時代是都要拋棄它們的! 為著體育的真精神,我們只有奮斗,只有向前!”這些文字,不僅結構了整部電影,而且抒情意味深厚,寓意深刻,帶有非常明顯的文學色彩。顯然,這種高度抽象的表達是聲音和色彩以及圖像所不能及的。 電影有了聲音元素之后,也同樣經常借助于文學性的文字拓展表現力。在《馬路天使》(1937)中,文字與圖像以及聲音結合,效果頗佳。其文字類型主要有:環境說明,如影片開頭有文字:“一九三五年秋,上海地下層”;歌詞,如多次出現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 彩色電影取代黑白電影之后,其文學符號依然存在,觀眾可見電影《祝福》(1956)的開篇即出自魯迅1918年7月所作《我之節烈觀》的文字: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嘗玩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電影語言及符號的構成元素主要有影像、色彩、聲音、文字。文學語言的構成元素主要是文字,也包括少量圖像。電影與文學在文字方面發生了交集。文學語言有其特性,正如美國的雷•韋勒克和奧•沃倫所指出的,文學語言要與日常各種語言用法區別開來。理想的科學語言純然是“直指式的”,它要求語言符號與指稱對象(signandreferent)一一吻合。而文學語言是高度“內涵”的(connotative)。文學語言還有表現情意的一面,可以傳達說話者和作者的語調和態度。它強調文字符號本身的意義,強調語詞的聲音象征。表面看來,電影語言與文學語言差別巨大。表現在:1.聲音、色彩、圖像都可以稱為電影獨有的元素。2.電影語言有其專門語法,正如烏拉圭的丹尼艾爾阿里洪所指出的,當電影制作者開始意識到,把各種不同狀態下活動的小畫格隨意接到一起,和把這一系列畫面彼此有機地接到一起的作法,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時候,電影語言就這樣誕生了。3.電影語言還有其特殊的表現手段,例如蒙太奇、造型、景深、音響音樂等。的確,電影即便是去掉文字,單憑聲音、色彩和圖像,也同樣是完整的。但正如法國的馬賽爾•馬爾丹所指出的那樣:話語乃是畫面的特殊的重要組成元素。因此,也可以說,如果電影語言符號摒棄了文學性,則無異切斷了一條與觀眾溝通的重要渠道。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電影都盡可能地運用了文學語言。電影中的對白既不同于科學語言,也不同于日常用語,而是具有豐富內涵的、高度抽象和凝煉的文學語言。同時,為了補充電影畫面,很多電影都使用了具有文學性的畫外音。而且,為了使電影能夠跨越民族和國界,超越語言障礙,幾乎所有的當代電影都配置了字幕,有的甚至達到六七種文字之多。以前所攝制的電影,包括無聲電影,也被添加字幕重新包裝。可以說,電影能否恰當地把握和運用文學性語言和文學符號,關系到其品質的優劣。 電影語言需要文學的援助有其必然性。文學性語言有助于增強電影的表現力和親和力,因為文學語言歷史悠久,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同時,文學語言高度凝煉,富有內涵,適當運用可以事半功倍。字幕不僅是電影打破語言障礙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進一步揭示電影畫面含義的重要手段。觀影時,人們借助于字幕可以充分地調動視角和聽覺來理解電影。對中國電影而言,很多編劇同時也是小說家或者戲劇家,他們在創作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小說或者戲劇寫作的經驗,文學性的語言自然或隱或現地融入了電影中。 隨著電影技術的發展,電影的表現手段會越來越多。但是,電影語言符號系統中若缺少文學要素則將是不完整的。原因很多,不妨略舉一二。首先,歷史題材電影的拍攝,需要還原歷史,文學作品恰是很好的資源庫。如谷劍塵在《一九二六年之國產電影》中所說的,拍古裝戲如宋朝戲在服飾、表演動作方面需要下功夫去考據。至于對話,只要模仿宋人小說的筆法就行了。其次,電影如果要跨越民族和國境進行傳播,就必須跨越語言的障礙。使用字幕可以可以較好地解決這一難題,當然,字幕及譯文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文學語言有關。再次,電影類型的多樣化,有助于滿足不同的需要。電影可以借鑒并運用不同類型的文學符號,形成不同的電影類型。此外,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電影將持續出現,這一類電影,不大可能消除其中固有的文學性,原著中的對白、修辭等很可能會在電影中再出現。 三 文學為電影解專業人才缺乏之困 與歐美電影業一樣,中國電影自發端之始即充滿商業氣息,正如陳白塵所說,中國電影不過是歐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抬頭后的一種成果。它從誕生起,就是徹頭徹尾的以商品姿態出現的,最初的中國電影導演者與其說是被視為藝術家,不如說被視為買辦更確切些。陳白塵的批評或許過于嚴厲了,但他的確指出了中國電影在創建期的特點:出于商業價值而得到資本家的關注。非專業的資本家而非電影藝術家成為中國電影企業的主導者,這其實就意味著必然要面臨專業人才缺乏的困境。 由于電影產業是知識密集型行業,因此,無論是電影的制作,還是發行和放映,都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員參與。正如有人指出的,外國人是因為發明了攝影機,才有了電影;而我們則是先放映了電影,看了電影,學習了放映技術,才開始了解電影,進而想到自己去拍攝電影。這句話很形象地說明了我國電影在初創階段專業人才缺乏的內在原因。電影作品的生命系統貫穿著電影的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和消費領域。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有可能導致電影企業在經濟上的損失,甚至破產。由于電影是一種大眾傳媒,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故有較多禁區。因此,與文學、美術等藝術種類相比,它對專業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有更高的要求。#p#分頁標題#e# 史實表明,中國早期的主要電影公司如北京豐泰照館、亞細亞影戲公司、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明星影片公司等,都與文學界人士有密切的關系。開中國自拍電影先河的是北京豐泰照館,它運用自己的照相技術和戲曲藝術家譚鑫培的表演藝術,拍攝了《定軍山》、《長坂坡》等多部戲曲電影。跟文學有深厚淵源的商務印書館于1919年試制影片,從1919至1927年,梅蘭芳為它導演了《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等戲曲電影。在中國電影的最初30年里,大小電影公司有50家以上。以《中國影片大典》和《中國電影發展史》為考察數據庫,可以發現,影響較大的影片公司如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及聯華影業公司、藝華影業公司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公司決策成員跟文學,特別是戲劇關系密切;擁有許多作家作為骨干力量;作家為它們創造了大量的、著名的電影劇本。 張石川、鄭正秋和周劍云是明星影片公司的創辦者,他們都對戲劇有深厚興趣,并且有過經營劇場或演劇的經歷。張石川曾在1935年的《明星》雜志上發表《自我導演以來》一文。他自述道,為了一點興趣,一點好奇的心理,差不多連電影都沒有看過幾場的他,卻居然不加思索地答允下來參與電影的拍攝了……鄭正秋先生則“一切興趣正集中在戲劇上面,每天出入劇場,每天在報上發表劇評,并且和當時的名伶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毛韻珂、周鳳文等人混得極熟。自然,這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該公司中具有文學創作或演劇經歷的部分編劇及作品有:洪深(1928,《少奶奶的扇子》等)、包天笑(1926,《多情的女伶》等)、田漢(1927,《湖邊春夢》)、嚴獨鶴(1932,《啼笑因緣》)、夏衍(1933《,春蠶》等)、沈西苓(1937,《十字街頭》等)、陽翰笙(1936,《生死同心》等)、鄭伯奇(1933《,到西北去》等)、阿英(1933《,豐年》等)、徐卓呆(1935,《兄弟行》)、歐陽予倩(1936,《清明時節》等)、劉吶鷗(1937,《永遠的微笑》)。 天一影片公司的老板邵醉翁也是由戲劇轉入電影行業的。他曾經營“笑舞臺”,排演文明戲,并以此為基礎和班底創建天一影片公司。該公司重要成員蔡楚生曾組織進業白話劇社,張恨水于1934年任《似水流年》的編劇,洪深則于1936年擔任《花花草草》的編劇。聯華影業公司也有不少來自文學界的編劇,如鄭逸梅(1932,《南海美人》)、田漢(1933,《三個摩登女性》)、夏衍(1937,《搖錢樹》)、歐陽予倩(1937,編導《如此繁華》)、洪深(1937《,鍍金的城》)等。藝華影業公司同樣如此,田漢(1933,編導《民族生存》等)、陽翰笙(1933,《中國海的怒潮》等)、洪深(1935,《時勢英雄》)、徐蘇靈(1936,編導《小姊妹》等)、吳村(1937,《女財神》)、劉吶鷗(1937,編導《初戀》)等作家都曾為該公司效力。其它許多電影公司也都有從文學領域轉來的專職或兼職從業人員。如上海影戲公司有朱瘦菊、鄭逸梅等,天心影片公司有徐卓呆等,新人影片公司有包天笑等。陳大悲為三一影片公司編寫了《到上海去》(1933),徐志摩和陸小曼為龍馬影片公司編寫了《卞昆岡》(1934)。 上述僅為略舉數例,還有李健吾、周貽白、柯靈、張愛玲、曹禺等許多作家也寫過電影劇本。 有些作家不但做編劇,而且做導演,如田漢、洪深等。田漢還曾創辦南國電影劇社,并于1926組織拍攝影電影《到民間去》,因故未完成,參演該劇的演員有葉鼎洛、蔣光赤、李金發等文學界人士。 大量文學界人士涌向電影界甚至還引起了有關人士的擔憂和不滿。許幸之1948年曾在《論電影的躍?與話劇的降落》中指出,話劇本身直線地往下降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戰后的國產電影實際上成了話劇的強大勁敵。一方面,昔日投資話劇的商人,轉而投資電影,以致劇團紛紛解體,劇人離散。另一方面,離散了的劇團與劇人紛紛加入電影公司,以致話劇無人過問。而且,話劇觀眾也紛紛涌向電影院。 如前文所述,出于贏利等方面的考慮,電影公司也很愿意聘用作家擔任編劇,故田漢、夏衍、洪深、歐陽予倩等文學名家都曾在多家電影公司擔任編劇。需要指出的是,田漢、夏衍、洪深等人進入電影界,跟左聯和黨的電影領導小組有關。 夏衍在《從事左翼電影工作中的一些回憶》中對此有較詳細的敘述。陳荒煤也曾指出過:黨的電影小組所做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就是動員新文藝工作者轉入電影界,陳波兒、袁牧之、鄭君里、趙丹等都是從戲劇轉到電影崗位的。還有許多作家雖然沒有直接做電影編劇,但也非常關注電影,并撰寫了影評,如魯迅曾翻譯日本巖崎昶著的《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撰寫《電影的教訓》。郁達夫在《銀星》1927年第13期發表過《如何救度中國的電影》。 老舍在《論語》1933年第29期發表了《有聲電影》。 余上沅在1938年9月25日重慶《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戰時戲劇與電影的題材》,這些影評在不同階段為推動電影發展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總之,作家為電影提供劇本,戲劇為電影提供演員,劇社劇團劇院為電影企業提供管理經營等方面的人才。正是在眾多來自文學界人才的支持之下,中國電影得以渡過初創期人才缺乏的難關,慢慢走向了成熟。 四 電影制度建設取法文學 電影制度既包括外部制度,如電影相關規章和制度,也包括內部制度,如電影分類、電影創作等本體方面的制度。電影作為一種綜合藝術,為自身發展前途起見,更需要一張獨立的身份證,需要彰顯自己的獨特性。因此,在電影制度的建設過程中,它警惕地與文學保持著距離,并且經常表現出欲在制度層面去掉文學色彩的姿態。但是,史實表明,中國電影無論在外部制度還是在內部制度的創建上,都曾取法于文學,從文學中獲取滋養。 “虛構性”、“創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學具有本質意味的特征,但電影同樣也具有這些特征。 從構成因素來看,電影劇本(屬于文學者)是電影的必備要素(早期電影除外)。這些情況表明電影內部制度本身包含著文學要素。中國電影的得名,也曾以文學為參照。周劍云、汪煦昌1924年在《影戲概論》中提到,“影戲”或“電影”的命名較為簡潔了當,因為覺得扮演影戲之動作與表情,較舞臺劇更為細膩自然,但又需顧及戲Drama的重要使命。為統一名稱,顧名思義起見,徑名“影戲”。#p#分頁標題#e# 在電影體式發展過程中,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文學樣式為它提供了許多借鑒。正如美國的溫斯頓所指出的那樣,小說對電影的敘事形式有極大影響。他認為,小說的側重點是故事,正是這一點給予了電影這一藝術形式的發展以最大的影響。中國也有類似的觀點,1921年,顧肯夫在《〈影戲雜志〉發刊詞》中將影戲(電影)看成是戲劇的一種。認為影戲的原質是技術、文學和科學三樣。他還指出影戲是居文學之上最高位置的,最有文學價值的。影戲的編制法,都含著小說的意味。除去小說,戲曲、話劇、歌劇、舞劇、詩歌、散文等也給了電影借鑒,并由此形成了戲劇電影、詩化電影、散文電影、歌舞電影等各式電影類型。如早期的黑白電影和大部分由戲劇改編而來的電影都具有明顯的戲劇意味:強調矛盾沖突和機緣巧合;對白有明顯的腔調修飾,類似戲劇語言;環境比較簡單,場景變化少。如李萍倩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1939)、方沛霖導演的《雷雨》(1938)等。而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1948),則既有散文的味道,又有詩歌的味道。 在中國電影外部制度的創建過程中,也滲透著文學因素,甚至可以說有著文學制度建設的思路和理念。其原因在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文學家掌握著電影制度建設的話語權。如在20世紀30年代,以田漢、夏衍、陽翰笙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家投身中國的電影事業,為中國電影制度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后,很多文學家成為了電影指導委員會、電影家協會等專門電影機構和團體的領導,繼續主導著電影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工作。 1933年2月9日,電影文化協會召開了成立大會,《出版消息》作了相關的報導,并開列了一份到會名單。其中,有不少來自文學界的人士,如陳瑜(即田漢)、洪深、黃子布(即夏衍)、席耐芳(即鄭伯奇)、沈西苓等。與創辦文學刊物相似,自1921年以后,一批電影期刊相繼創刊,較早者有《影戲叢報》、《影戲雜志》、《明珠》、《電影雜志》、《晨星》、《電影雜志》、《電影周刊》等。 1922年,鄭正秋在《明星公司發行月刊的必要》中開篇指出,惟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創造生氣勃勃的空氣,改造中國死氣沉沉的現象的能力。創造生氣勃勃的空氣,改造中國死氣沉沉的現象是文學家、藝術家的責任。文學對電影及其期刊發展的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電影制度的建設繼續進行。1949年以后,《大眾電影》(1950)、《電影藝術譯叢》(1952)《、中國電影》(1956)《、電影文學》(1958)等電影專門刊物陸續創刊。國家還特設了百花獎、金雞獎和華表獎等電影獎項。1996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還特設“夏衍電影文學獎”,在全國范圍內征集優秀電影劇本。 電影劇本(文學元素)方面的制度建設被置于重要位置,作家在其中起著領導作用。如1952年,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時,夏衍兼任所長,柯靈任副所長。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加強電影制片工作的決定》指出:中央文化部電影局的電影劇本創作所應成為廣泛聯系和組織全國作家進行電影劇本創作的有效機構。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通過了《關于加強電影文學劇本創作的決定》,同年,文化部與中國作協聯合發出《征求電影文學劇本啟事》。1961年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總理在會上作了題為《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重要報告。 新中國成立之際,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期間成立了中華全國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該會委員中文學家約占三分之一,夏衍、陳白塵等人均在其中。陽翰笙任主席。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成立,該會委員中有不少是作家,如丁玲、艾青、老舍、趙樹理、陽翰笙、田漢、洪深、歐陽予倩等,主任委員為沈雁冰。1957年4月11日,全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4月16日成立了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蔡楚生任主席。1979年11月,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國電影家協會(原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選出了新的領導,夏衍當選為主席。種種史實表明,文學家們除了在電影劇本的創作、電影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之外,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的時期內,文學家們還在電影工作機構和團體中擔任要職。參與甚至主導著更廣泛、更深層次的電影制度的創建。 相對于世界電影的創建和發展,中國電影有其特殊的生存語境,即它的創建是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轉型中進行的。國民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國民經濟落后、生產力低下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創建過程中的中國電影明顯營養不良,迫切需要文藝兄弟的援助。于是,與它有親緣關系的文學自然地充當了救火員的角色,部分小說家、戲劇家和戲劇演員甚至改行進入電影界。而近現代中國社會中人們對文學的特別推崇,以及政府對文學的高度重視,使得文學在中國電影的創建過程中擁有了十分重要的話語權。 這兩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國電影染上了十分濃郁的文學色彩。因為中國電影特殊的生存與發展語境,文學對中國電影發展的貢獻和影響顯得尤其突出和巨大。文學與中國電影的這種關系,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其中的特殊性特別值得關注和研究。 在中國電影的創建過程中,文學對其提供了全方位的,不可缺少的援助。這種援助伴著著它的萌芽、發展和成熟的全過程。文學也由此滲入到電影的器物層、制度層和精神層等各個層面之中。當前,電影越發顯出獨立的姿態,電影界與文學界似乎慢慢有了越來越多的隔膜,這與二者原初的關系其實是相背離的,對二者的發展很可能也是不利的。 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會給文學藝術的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并沖擊著原有的格局。例如出版業的興起促使長篇小說的興盛,近代報章的出現,促使大量新的文學樣式產生。電影技術的發明也同樣如此。從文學在中國電影創建過程中的巨大貢獻可以看出,新的文藝樣式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總是在原有的文藝樣式的幫助下發展和成熟。而且新的文藝樣式出現之后,也并不意味著原有的東西就一定立即會消亡,它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可以共存,可以共同發展。故此,對待文藝界的新生事物,需以寬容的眼光待之,以合作而非對抗的心態處之,并積極地尋找恰當的共贏方式。#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