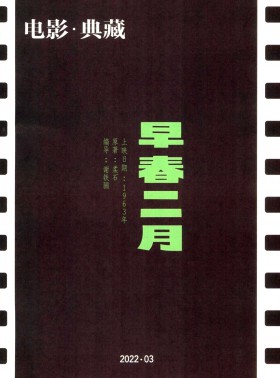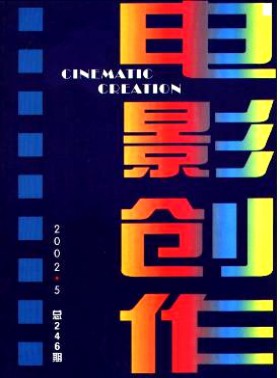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電影中的生態(tài)情懷透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工業(yè)革命、技術(shù)革命在帶給人類社會巨大成就的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日益嚴(yán)重的生態(tài)問題。越發(fā)頻繁的災(zāi)難不斷地警告著人類反思發(fā)展中的行為。文藝界以不同的方式回應(yīng)著人類生態(tài)環(huán)境面臨的問題,電影業(yè)也不例外。近年來,包括好萊塢在內(nèi)的越來越多的電影人將目光聚集到了人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上。雅克•貝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光影之美記錄著人類環(huán)境中的美、善、丑、惡,贊美生命的偉大,呼吁人類本性的回歸。本文以雅克•貝漢“天•地•人”三部曲及2011年的《海洋》為例,探析雅克•貝漢的生態(tài)情懷及電影表達(dá)。 一、生態(tài)電影概念與雅克•貝漢的生態(tài)電影 (一)生態(tài)電影界定 生態(tài)電影的興起源于20世紀(jì)人類對生態(tài)的反思,1982年捷克舉辦了第一次以生態(tài)電影為專題的國際電影展,此后成為傳統(tǒng),每年一屆,參加的影人、作品、影片的類型、風(fēng)格等日益增多。實(shí)際上以動物、植物或自然界為題材的電影很多,但并不是每部都可稱為生態(tài)電影。作為電影類型的一種,生態(tài)電影關(guān)鍵詞在“生態(tài)”,其電影思想核心是生態(tài),著重表現(xiàn)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有著一種憂慮、反思,有著強(qiáng)烈的生態(tài)意識、生態(tài)責(zé)任、生態(tài)倫理,呼喚人與自然的和諧,指向人類心靈的轉(zhuǎn)向。[1] (二)雅克•貝漢的生態(tài)電影 雅克•貝漢是拍攝生態(tài)電影的老手、大師,這位法國著名的影人曾主演、制片過多部著名影片,如《天堂電影院》《Z》《勝利歡歌》《特殊地帶》《放牛班的春天》等,其影片有著強(qiáng)烈的人文意識,獲獎眾多。從20世紀(jì)80年代末,雅克•貝漢把目光轉(zhuǎn)向了自然,憑著興趣和激情,不惜巨資,陸續(xù)拍攝了《猴族》《遷徙的鳥》《微觀世界》《喜瑪拉雅》“天•地•人”三部曲、《大自然的翅膀》《海洋》等關(guān)注自然的生態(tài)電影,影響巨大。他也因此獲得了第18屆法國梅尼古特國際動物影片電影節(jié)“終身成就獎”。 這些影片從陸地到海洋,從天空到大地,從動物到人類,核心都在生態(tài)。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雅克•貝漢強(qiáng)烈的生態(tài)意識,他對抽象的生態(tài)情感的詮釋極具票房吸引力。 二、雅克•貝漢電影的生態(tài)情懷 (一)贊美自然、生命、天性之愛的偉大 電影打動人心的關(guān)鍵在“情”,以情動人,雅克•貝漢認(rèn)為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事情,情感能帶給人們回憶。具體說來,其生態(tài)情感是“愛”,對生命之愛,并由此歌頌生命創(chuàng)造者———自然生靈的偉大,敬畏生命。[2] 《微觀世界》中千姿百態(tài)的昆蟲,蚊子、蝴蝶、蜘蛛、蜜蜂等毫不起眼的小昆蟲,細(xì)節(jié)地展示了一個(gè)非常幼小、肉眼甚至可忽略的生命如何一步步地誕生,最終羽化成蝶。 晶瑩剔透的肉身中孕育著小小的生命,它們破殼而出,在潔凈的天地間,充滿了圣潔美麗的光芒。讓觀眾忘記了日常生活中避之唯恐不及的蚊子等昆蟲的奇形怪狀,而沉浸在對生命的禮贊之中。 《遷徙的鳥》中候鳥歷經(jīng)千辛萬苦,穿越2500公里的行程,聚集到北極孕育新生命,小天鵝從天鵝媽媽的羽毛下鉆出小腦袋,新奇地看著周圍的世界,并開始步履蹣跚地跟著媽媽學(xué)習(xí)游泳、覓食、飛行。肉紅色的知更鳥艱難地破殼而出,用清脆的啾啾聲宣告自己的誕生。鳥兒們在遷徙中會遇到種種困難,新生命的降臨與成長讓每個(gè)見證者都為之激動,也感慨其中的不易,由此更加珍惜。 《喜馬拉雅》中環(huán)境嚴(yán)酷,一片貧瘠,植物都很少見到,藏民雖然在物質(zhì)上很貧困,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生命力蓬勃旺盛地成長著。他們在世界的屋脊,帶著樸素而忠貞的信仰,長途跋涉在用鹽換糧食的征程中,養(yǎng)活了子子孫孫,一代代傳承,不禁讓人感慨生命的頑強(qiáng)。在寺院當(dāng)喇嘛的諾布回到家鄉(xiāng)后,與母親輕觸額頭,母親手把手地教諾布如何綁繩子,雖然母子之間沒有很多的語言交流,但一切的愛、思念、關(guān)心都融在了其間。 “天•地•人”三部曲中,兩只螞蟻同飲一滴水;兩只蝸牛的纏綿愛情;鳥兒在遷徙中的不離不棄,互相照顧,用各種方式表達(dá)愛慕之情;企鵝爸爸將嘴中僅存的食物喂給小企鵝等等無不展現(xiàn)了自然、生命、愛之力量的偉大與崇高。這種自然、生命的愛之情在新片《海洋》中同樣得到了延續(xù)。絢爛多姿的海洋世界,北冰洋海象媽媽在水中溫情脈脈地抱著自己的孩子;夕陽下的海面上,小海豚跟著海豚媽媽以優(yōu)美的曲線跳躍;在海底,水母“張牙舞爪”。攝制組跟著海洋生物一起行走、游泳,關(guān)注著海洋生物的情緒和情感,以此表達(dá)對自然的禮贊。 (二)描述人類對生態(tài)的“惡行” 自然界中雖然也有弱肉強(qiáng)食的自然法則,也充滿了你吃我,我吃它的現(xiàn)實(shí),但這種自然法則的運(yùn)行一環(huán)扣著一環(huán),相互依存,處于和諧共生的狀態(tài)。比如《微觀世界》中瓢蟲吞食蚜蟲,螞蟻則吸食蚜蟲釋放出來的蜜汁,所以螞蟻將會與蚜蟲達(dá)成同盟、互惠互利,螞蟻視瓢蟲為敵人,遇到時(shí),不惜血拼一場。這是自然界特定的生態(tài)鏈或者秩序,每個(gè)個(gè)體都是這條生態(tài)鏈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各自的天敵,誰也沒有生殺予奪的權(quán)力。正是這種生物鏈讓自然保持平衡狀態(tài)。然而人類卻打破了這種平衡,以自我為中心,隨意地對其他物種進(jìn)行生殺予奪,破壞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原有的完整性。《遷徙的鳥》中候鳥在征程中經(jīng)常遇到人類制造的障礙,甚至是災(zāi)難,比如夜空中的星星原本可以幫助鳥兒導(dǎo)航,現(xiàn)在夜空變成了燈光閃爍的不夜城。 在鳥兒俯瞰下的城市煙霧彌漫,污水橫流,鳥兒不時(shí)地被汽車嚇得魂飛魄散、掉隊(duì);紅胸黑雁被泄漏的石油粘住;灰雁被布滿的漁網(wǎng)纏住,不能動彈;天鵝在獵人的槍口下喪命……影片《海洋》的開頭,滿頭白發(fā)的雅克•貝漢帶著小兒子徜徉在空蕩蕩的滅絕動物博物館里。“海洋是什么?”孩子問,父親無語。接下來影片用一個(gè)多小時(shí)的時(shí)間,近距離闡述了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的情緒和生活,寧靜、和諧。回溯式地在告訴孩子海洋原本的狀態(tài)。但在60多分鐘后,漁網(wǎng)悄悄地張開,鯊魚入網(wǎng),被拖上船,魚鰭、魚翅、魚尾被迅速割下來,冒著血的鯊魚被重新推入大海,身體殘缺的鯊魚失去了自由游動的能力,像一塊重物,掙扎著慢慢沉入海底,原本蔚藍(lán)干凈的海水瞬間被鮮血染紅了。#p#分頁標(biāo)題#e# 觸目驚心的一幕跟前面的美好多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盡管片中沒有出現(xiàn)人類的身影,沒有人類的聲音,但人的殘酷性不言而喻。這一幕也就在曲折地回答孩子沒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海洋沒了?孩子的疑問實(shí)際上是看不到豐富多彩的海洋的后代子孫對前輩的發(fā)問與責(zé)問,這不僅是對雅克•貝漢的提問,也是在對全人類進(jìn)行提問。我們?nèi)绻俜趴v下去,肆無忌憚地侵吞著自然的資源,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海洋將以空蕩蕩的博物館的形式殘留在老一輩人的記憶中。我們的子孫將不知道海洋為何物,到時(shí)我們該如何面對后代,如何回答他們的詢問。這是雅克•貝漢對人類破壞自然和諧之美的發(fā)問與譴責(zé)。影片特意在片尾告訴觀眾:“影片中的任何一個(gè)動物,都沒有因?yàn)橛捌臄z的需要被虐待或被捕殺”,以此來審視人類的行為,包括以生態(tài)保護(hù)名義下的行為。 (三)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呼吁人類的回歸 雅克•貝漢希望通過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呼吁人類的回歸,尋求和自然的和解。他認(rèn)為,只有表現(xiàn)自然的美好,讓觀眾愛上海洋,才能讓他們懂得保護(hù)海洋。 [3]生態(tài)電影不是為批判而批判,最終目的是倡導(dǎo)人們注意人與自然的平衡,跟自然和諧相處。雅克•貝漢堅(jiān)守著這個(gè)信念,其生態(tài)電影盡管也有人類殘酷行為的敘述,但只是點(diǎn)到即止,不去渲染,將更多的篇幅留給了那些美麗的生靈,讓大家去思考,因此整個(gè)影片始終有一種和諧的美感。《喜馬拉雅》中環(huán)境嚴(yán)酷,藏民的生活方式與現(xiàn)代文明有很大距離,新老藏民之間有著矛盾與沖突,但這并不妨礙藏民虔誠地崇敬天地、大自然天人合一、循環(huán)相生的信念。他們用原始、本能的狀態(tài)聽從上天的安排,很自然地面對人的離去。老藏民雷霆在為救村民葬身雪山后留下的遺言:“我們始終都在一起,我們的愿望相同。”這種相同的愿望即人與自然歸一,讓子孫后代安全幸福地生活在這片干凈的土地上。 在雅克•貝漢的生態(tài)影片下,人與自然是統(tǒng)一的,人在自然中孕育,也將回歸自然,有著一種回歸的本能,呼吁偏離軌道的人類回歸。《遷徙的鳥》中各地的候鳥從世界各地往北極圈聚集,飛往他們的出生地,孕育新的生命,新的候鳥在父母的帶領(lǐng)下,穿越千山萬水,回到世界各地生活,以后它們也將跟父輩一樣,回到北極這個(gè)祖籍地。 這是鳥兒的生命回歸。《喜馬拉雅》中的老族長雷霆一生都生活在雪山中,最終的歸宿也在雪山。藏民的死者將在親人的念經(jīng)超度中進(jìn)行天葬,這也是對自然的一種回歸。人原本是自然生靈之一,跟其他的生命同屬兄弟姐妹,都是大自然的偉大生命創(chuàng)造。然而在發(fā)展過程中,原本的自然之子逐漸以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對待自然,在自然“美而不言”的大愛面前,也需要這種回歸。 三、雅克•貝漢電影的生態(tài)美感 雅克•貝漢除了在內(nèi)容上倡導(dǎo)生態(tài)意識,在拍攝技巧、角度、視覺、聽覺等方面也注重生態(tài)美感。其生態(tài)影片畫面干凈、質(zhì)樸,色調(diào)自然,沒有太多人工的痕跡,敘述語調(diào)的浪漫柔和與生態(tài)主題相適宜。在拍攝角度上,采取與生物平行、平視的視角,雅克•貝漢說:“我們把它當(dāng)成一個(gè)‘人物’,一個(gè)‘角色’,試圖用最近的距離拍攝它,你會發(fā)現(xiàn),我們的攝影機(jī)總是在捕捉它的目光,它的表情,它的每一個(gè)動作。”其生態(tài)電影均采用顯微攝像機(jī)拍攝,《海洋》中水母吹彈可破的柔軟、藍(lán)鯨像褥墊般的腹部展露無遺,動物顯得有智商、有情商。并用適宜的音樂配合生物的各種情緒,比如《微觀世界》的開頭,兒童唱詩班干凈圣潔的唱誦聲音與昆蟲世界的美妙融為一體。《遷徙的鳥》中伴隨鳥兒在海洋上飛翔的是有節(jié)奏的低音合唱,而飛越城市上方時(shí)則是緊張的管弦樂。 四、結(jié)語 雅克•貝漢倡導(dǎo)生態(tài),但并非以道德法官的姿態(tài)控訴人類,如同《海洋》的導(dǎo)演之一雅克•克魯索說:“我們反對的是工業(yè)化的掠奪,一網(wǎng)打盡的捕撈。我們對自然界抱樂觀的態(tài)度,我們相信海洋的修復(fù)性。正如影片所說,海洋幾百萬年的進(jìn)化,被人類短短的幾步給毀壞了。但現(xiàn)在,人類保護(hù)它的愿望也前所未有的強(qiáng)烈,就像兩者在和解。”[4]《遷徙的鳥》中小男孩割破了漁網(wǎng),救出了灰雁,目送著它飛往遠(yuǎn)方,鄉(xiāng)村老婦人看著灰鶴從面前騰空而起,久久佇立凝視。從這些姿態(tài)中我們看到了雅克•貝漢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