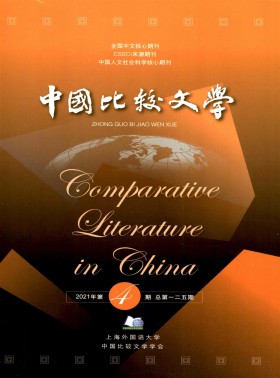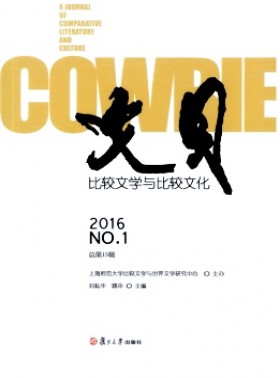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比較文學(xué)的內(nèi)外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國外比較文學(xué)是一種真“外部”、偽“內(nèi)部”的文學(xué)研究
文學(xué)研究的內(nèi)外問題已經(jīng)不是一個(gè)新鮮的話題。在比較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所謂的美國學(xué)派與法國學(xué)派之爭的一個(gè)重要議題就是內(nèi)部關(guān)系和外部關(guān)系之爭。在法國學(xué)派的比較文學(xué)理念中,基本原則就是去尋找和實(shí)證確實(shí)存在過的“事實(shí)聯(lián)系”,能夠?qū)嵶C的事實(shí)聯(lián)系是法國比較文學(xué)的基石。如卡雷對比較文學(xué)下的定義為:“比較文學(xué)是文學(xué)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guān)系,研究拜倫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萊爾、司各特和維尼之間的事實(shí)聯(lián)系,研究不同文學(xué)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shí)聯(lián)系。”卡雷的定義對法國學(xué)派影響深遠(yuǎn),他基本奠定了法國比較文學(xué)注重文學(xué)外部關(guān)系的基調(diào)。其后梵•第根的定義更突出了法國學(xué)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點(diǎn)。梵•第根指出:“比較文學(xué)的目的實(shí)質(zhì)上是研究不同文學(xué)相互間的關(guān)系。”顯然,“國際間”“不同文學(xué)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學(xué)”“事實(shí)聯(lián)系”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國學(xué)派注重的是文學(xué)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實(shí)關(guān)系,探討的是不同文學(xué)現(xiàn)象間的影響與傳承。或者說,體現(xiàn)在量上,法國學(xué)派研究的是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不同文學(xué)現(xiàn)象之間的事實(shí)關(guān)系。
美國學(xué)派針對法國學(xué)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們反對法國學(xué)派重視外部聯(lián)系,忽略文學(xué)內(nèi)部關(guān)系的做法。但美國比較文學(xué)并不僅僅就是后來的美國學(xué)派,在美國學(xué)派嶄露頭角之前,美國已經(jīng)有不少學(xué)者從事相關(guān)研究。真正把美國比較文學(xué)推到世界學(xué)術(shù)前臺(tái)的是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xué)的概念》中對法國學(xué)派提出批評,認(rèn)為“他們過于重視‘事實(shí)關(guān)系’,對比較文學(xué)定義的解釋比較狹隘,忽略了對藝術(shù)作品的美學(xué)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美國學(xué)者著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沒有事實(shí)關(guān)系的兩種或兩種文學(xué)現(xiàn)象以及進(jìn)行平行的跨學(xué)科研究。從此,美國學(xué)派開始發(fā)出自己的最強(qiáng)音,這其中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人物正是韋勒克。而韋勒克作為“新批評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學(xué)術(shù)界公認(rèn)的二十世紀(jì)最博學(xué)的文藝批評家之一”,“是一個(gè)執(zhí)著于對文學(xué)進(jìn)行內(nèi)部研究的批評史家”。他的重要貢獻(xiàn)是把文學(xué)研究劃分為“內(nèi)部批評”和“外部批評”,并更鐘情于文學(xué)“內(nèi)部研究”。但這里的問題是,不能因?yàn)轫f勒克的“內(nèi)部研究傾向”,而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美國學(xué)派倡導(dǎo)的比較文學(xué)本質(zhì)上是一種內(nèi)部研究的比較文學(xué)。“實(shí)際上,他雖然身為該學(xué)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將,但卻未曾盲目地局限于這種方法,而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國學(xué)派的其他領(lǐng)軍人物并不完全贊同韋勒克的主張。我們考察美國學(xué)派對比較文學(xué)的定義也不難發(fā)現(xiàn),美國學(xué)派的比較研究并沒有分清楚韋勒克式的“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韋勒克那里,內(nèi)外之分不僅僅指的是文學(xué)要同社會(huì)歷史批評脫鉤,不僅僅指的是文學(xué)要脫離政治、脫離歷史賦予的“因果性”聯(lián)想,還指的是文學(xué)研究要“區(qū)分文學(xué)作品的‘本體存在’與‘經(jīng)驗(yàn)存在’,并由此確立這樣一個(gè)理論論點(diǎn):文學(xué)研究的對象是文學(xué)作品的‘本體存在’,即一種‘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jié)構(gòu)’”。韋勒克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建立在語言基礎(chǔ)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語言,可以分為三個(gè)層次,即“聲音層面、意義單元和世界層面”,是一個(gè)“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研究”就是對這一現(xiàn)象學(xué)意義上的“本體結(jié)構(gòu)”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則主要涉及文學(xué)作品的“經(jīng)驗(yàn)存在”,諸如它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狀態(tài)以及讀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見,韋勒克“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二元區(qū)分最主要的話語功能就是要突顯文學(xué)作品這一超越一切經(jīng)驗(yàn)現(xiàn)實(shí)的“本體存在”由語言構(gòu)成的“符號結(jié)構(gòu)”,并進(jìn)而對其進(jìn)行審美的分析。因而,所謂的內(nèi)部研究就是指對文學(xué)本體結(jié)構(gòu)的研究,關(guān)注的是文學(xué)語言的符號性,而外部研究則指的是對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層面的研究,包括我們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會(huì)影響到文學(xué)的種種外部因素,如社會(huì)歷史背景、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讀者接受情況等。再來看美國學(xué)者對比較文學(xué)的界定,以雷馬克為例,他指出:“比較文學(xué)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xué)研究,并且研究文學(xué)與其他知識(shí)及信仰領(lǐng)域的關(guān)系,包括藝術(shù):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xué)、歷史、社會(huì)科學(xué)(如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學(xué))、自然科學(xué)、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xué)是一國文學(xué)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xué)的比較,是文學(xué)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lǐng)域的比較。”
雷馬克的定義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國內(nèi)學(xué)者在寫作比較文學(xué)教材時(shí)竟然沒有人對這樣一個(gè)內(nèi)涵和外延幾乎都不確定的定義進(jìn)行責(zé)難和質(zhì)疑,而是想當(dāng)然地把它作為美國學(xué)派的代表性定義接受和吸納。殊不知,美國學(xué)者在比較文學(xué)上的貢獻(xiàn)要遠(yuǎn)遜于他們的法國同事。除了眾聲喧囂地進(jìn)行所謂的理論變革之外,他們在比較文學(xué)上的貢獻(xiàn)可謂少之又少。從雷馬克的定義里,我們除了能感覺到新批評的一大弊端———不負(fù)責(zé)任地亂聯(lián)系之外,幾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說韋勒克的“內(nèi)部研究”了。韋勒克的重要貢獻(xiàn)就在于其對文學(xué)批評的重新解釋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學(xué)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學(xué)批評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較文學(xué)領(lǐng)域幾乎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和回響。美國學(xué)派號稱進(jìn)行了比較文學(xué)的內(nèi)部轉(zhuǎn)向,從事實(shí)聯(lián)系轉(zhuǎn)向了對文學(xué)審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國內(nèi)學(xué)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為審美價(jià)值關(guān)系,但是從美國學(xué)派的定義和研究中,很難感受到其價(jià)值和審美究竟體現(xiàn)在哪里。
因而,其實(shí)可以下這樣一個(gè)論斷,美國學(xué)派的平行轉(zhuǎn)向,實(shí)際上是把比較文學(xué)的外部研究擴(kuò)大化了,并沒有解決文學(xué)審美關(guān)系研究這一問題。我們熱衷于翻譯各種各樣美國學(xué)者的理論,實(shí)際上如果我們清醒一點(diǎn)就可以發(fā)現(xiàn),即便是在理論建設(shè)上,美國學(xué)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從比較文學(xué)研究文學(xué)外貿(mào)到無所不包的大“跨越”,國外比較文學(xué)注定打上了在文學(xué)外部關(guān)系兜圈子的理論缺憾。
二、中國比較文學(xué)的理論尷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論沼澤
反觀中國學(xué)者,我們?nèi)狈鈱W(xué)者批判的力度,并沒有意識(shí)到國外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真正問題所在。再不客氣一點(diǎn)說,我們是在美國學(xué)派大而無當(dāng)?shù)哪嗵独锢^續(xù)深陷不出。這種情況不是比較文學(xué)獨(dú)具的特點(diǎn),整個(gè)外國文學(xué)研究似乎都存在這一問題。在貌似客觀和真實(shí)的學(xué)術(shù)研究立場上,我們集體性盲從,集體性不敢說“不”。一旦有人對國外理論提出某些質(zhì)疑,馬上就有相關(guān)人士從各種角度進(jìn)行辯護(hù)和還原。這種情況暫時(shí)不會(huì)改觀,慣性思維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國理論活著。試看國內(nèi)學(xué)者對比較文學(xué)性質(zhì)的一些界定。學(xué)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當(dāng)屬劉象愚先生。在《比較文學(xué)的不變與變》中,他指出:“比較文學(xué)的不變,在于標(biāo)志它本質(zhì)特征的那些東西。我想,至少有三點(diǎn)是它必然要堅(jiān)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發(fā),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學(xué)的界限之類,因而比較學(xué)者也需有兩種以上語言、文學(xué)與文化的學(xué)養(yǎng);第二是方法論上的比較性。也即自覺的比較意識(shí)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學(xué)性。由此出發(fā),比較文學(xué)的研究,無論跨越了什么樣的界限,總須把文學(xué)性也就是文學(xué)之所以為文學(xué)的那些基本性質(zhì)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較文學(xué)則將喪失自我而不復(fù)存在。”作為中國比較文學(xué)界的代表性人物,劉象愚先生對中國比較文學(xué)進(jìn)行了最精彩的總結(jié)。但是這三個(gè)方面存在的問題依然是內(nèi)外不分。我們不是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研究一定要進(jìn)行內(nèi)部研究才算高層次,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如果缺少內(nèi)部研究,文學(xué)研究的價(jià)值肯定會(huì)大打折扣。從國內(nèi)比較文學(xué)的理論建設(shè)和實(shí)際研究來看,其關(guān)注焦點(diǎn)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來看“跨界性”。“跨”意味著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現(xiàn)參照物。在比較文學(xué)相關(guān)論述中,這種參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現(xiàn)。按照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看法,中國文學(xué)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參照中才能顯示自我的價(jià)值和存在意義。因而,相關(guān)學(xué)者在進(jìn)行論述時(shí),基本上都會(huì)采用或提到“他者”這樣的觀照視角。比如孫景堯教授的《簡明比較文學(xué)———“自我”和“他者”的認(rèn)知之道》(屬于較早的比較文學(xué)教程)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但“他者”盡管可以彰顯“我”的特異性存在,從而可以更清晰地確定“我”的特點(diǎn)和意義,但假若“我”本身的特點(diǎn)和內(nèi)涵并不明晰,或者說,“我”缺乏足夠的力量與“他者”進(jìn)行對比時(shí),“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顧“他者”理論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史可以發(fā)現(xiàn),最早對“他者”進(jìn)行過闡釋的黑格爾,是把“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放置在主人與奴隸這一對應(yīng)性關(guān)系中進(jìn)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開始就打上了奴隸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論中,“他者”就是邊緣化的弱勢群體。換而言之,按照這種理論,中國實(shí)際上是處于“他者”這樣一個(gè)范疇里。如果我們忽略“他者”的這種文化劣根性,想當(dāng)然地變“他者”為“我”,試圖用一個(gè)帶有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權(quán)色彩的詞語構(gòu)筑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難免會(huì)導(dǎo)致策略上的失誤,甚而言之,會(huì)中了西方文化的一個(gè)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國比較文學(xué)試圖站在一個(gè)客觀的“我”與“他者”立場上去討論問題,去面對世界文學(xué)、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個(gè)缺陷,即主體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過于強(qiáng)勢。詞語的轉(zhuǎn)換并沒有太大意義,反而掩蓋了一個(gè)“敵強(qiáng)我弱”的事實(shí)。在這樣的一個(gè)前提下進(jìn)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導(dǎo)致間接或者無意地證明了“他者”(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優(yōu)越性,而由此導(dǎo)致“我”的瓦解和崩潰。
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文學(xué)學(xué)界為什么會(huì)一邊倒地在“他者”問題上兜圈子,甚至連一點(diǎn)點(diǎn)微弱質(zhì)疑的聲音也沒有呢?我認(rèn)為主要原因就在于國內(nèi)學(xué)者對世界環(huán)境的定位過于寬泛。我們相信這是一個(gè)全球化的時(shí)代,相信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講述的就是真理。換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環(huán)境,我們相信需要對話、需要交流;立足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我們相信哲學(xué)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他者”證明“我者”的時(shí)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中國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前提,導(dǎo)致了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盲目樂觀和理想主義。
究竟該怎么看待這一問題呢?全球化究竟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一定要參與對話嗎?不對話可以嗎?我們的對話到底有多少說服力?時(shí)代對學(xué)術(shù)的影響是必然的嗎?我們是不是在宏觀地談?wù)撌澜缧蝿荻狈ξ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趕西方的“流行風(fēng)”可行嗎?真的是當(dāng)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價(jià)值的參考嗎?“他者”真的就具有絕對的魔力嗎?比較文學(xué)在說明自己存在理由時(shí)有意無意地制造了一種宏大敘事———空談世界形勢、空談全球化、空談文學(xué)交流的日益頻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學(xué)”的時(shí)代快要或已經(jīng)來臨。在此基礎(chǔ)上,學(xué)者們大都相信交流無可避免。交流當(dāng)然無可避免,即便沒有全球化這個(gè)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學(xué)時(shí)代的來臨究竟有何實(shí)際意義,除了在理論上表明民族文學(xué)之間交流日益頻繁,在具體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上它的價(jià)值有多大?至少在當(dāng)前的研究中并沒有體現(xiàn)出來。與此同時(shí),對于比較文學(xué)的本土立場上,中國比較文學(xué)很少涉及。我們只是空談一些歷史問題,空談一些源流問題,作為中國比較文學(xué)真正應(yīng)該關(guān)注的中國現(xiàn)實(shí)問題很少涉及。
這樣的學(xué)術(shù)立場決定了根本無所謂對話不對話。我們的立場跟西方的立場沒有差別,都是對西方生存環(huán)境的宏觀回應(yīng)。唯一區(qū)別的是,對他們而言,這個(gè)宏觀現(xiàn)實(shí)場是真實(shí)的,對我們而言,我們只是在想象世界的處境,想象他們的立場,進(jìn)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對我們自己的推介,則少之又少。在國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上,我們很少能讓外國人了解我們自己,反而是我們在向他們表明我們到底了解了他們多少。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他者至上主義”的過分與“我”的徹底失語。所以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環(huán)境是一個(gè)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因?yàn)槲覀兩钤谶@個(gè)時(shí)代,就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這個(gè)時(shí)代就一定會(huì)對我們發(fā)生巨大作用。對于建立在上述立場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進(jìn)行審視。我們是不是跨的有點(diǎn)太寫意,跨的有點(diǎn)太脫離中國國情,“跨”得太超越學(xué)科發(fā)展的速度。同時(shí)這種無邊無際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學(xué)研究變成一種無法約束和界定的研究。我們經(jīng)常批判“x+y”式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但是仔細(xì)研究一下相關(guān)論文,有幾篇不帶這樣的比附?在這樣的跨上,我們很容易就會(huì)把文學(xué)研究變成一種“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較文學(xué)的“向外轉(zhuǎn)”,從一種本位主義變成一種他者主義。
再看比較文學(xué)的“比較性”和“文學(xué)性”。比較,顧名思義,面對的至少是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對象。結(jié)合前面所講的跨,不管這種“跨”是跨語言、跨國家、跨民族,還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學(xué)科,一旦比較與這些“跨”相結(jié)合就注定造成一種文學(xué)外部研究的假象。這也是當(dāng)前比較文學(xué)研究執(zhí)著于文學(xué)外部研究的一個(gè)原因。在歷史上某段時(shí)期,我們已經(jīng)受夠了文學(xué)外部研究的摧殘,當(dāng)然這并不是文學(xué)外部研究的問題,而是因?yàn)椴恢廊绾翁幚矶哧P(guān)系的問題。現(xiàn)在我們一方面畸形反對、極其厭惡這種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從骨子里擺脫不了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而真正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應(yīng)該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還是內(nèi)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讓我們領(lǐng)略文學(xué)作為藝術(shù)帶給我們的美感,以及文學(xué)能否作為思想研究的自由領(lǐng)地,催發(fā)出新的有益于時(shí)代的思想。因而所謂的文學(xué)性就在于以上兩點(diǎn)。但是比較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究竟何指?我們一般認(rèn)為比較文學(xué)的文學(xué)指的是文學(xué)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學(xué)研究中的“文學(xué)”?究竟什么是文學(xué),對比較文學(xué)而言是一個(gè)致命的問題。中國學(xué)術(shù)界對文學(xué)的理解基本上還停留在康德、黑格爾階段上,強(qiáng)調(diào)美的理念與感性形式的統(tǒng)一,認(rèn)為美具有無功利性、無目的性等,認(rèn)為文學(xué)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學(xué)的正統(tǒng),承認(rèn)經(jīng)典永久性,執(zhí)拗于追尋文學(xué)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盡管我們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學(xué)理論,但我們?nèi)匀粓?jiān)守著自己的文學(xué)觀念。現(xiàn)實(shí)主義仍然是中國學(xué)界比較認(rèn)可的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式,也是學(xué)者們進(jìn)行研究時(shí)有意無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經(jīng)之地。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的德國血緣。馬克思沒有系統(tǒng)的文學(xué)美學(xué)理論,因而德國古典美學(xué)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蘇俄文學(xué)實(shí)踐的影響,整個(gè)中國文學(xué)美學(xué)研究現(xiàn)狀也就不難理解了。整體而言,我們的文學(xué)審美觀念仍然是近代的,帶有很深的傳統(tǒng)印記。
但是我們所處的現(xiàn)實(shí)情況是,文學(xué)已經(jīng)在發(fā)生種種變化。無論從作家群體還是作品存在形態(tài),無論是從讀者接受群體還是作品傳播媒介,全方位的變化已經(jīng)改變了文學(xué)的本質(zhì)。但是充斥在大學(xué)中文系教科書里的“文學(xué)”很多年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盡管我們承認(rèn)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念仍然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較文學(xué)真的就能承擔(dān)起審美價(jià)值關(guān)系研究的重任嗎?至少在當(dāng)前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和實(shí)踐中,我們沒有看到太有說服力的成果。對“文學(xué)”重質(zhì)輕文的認(rèn)識(shí)改變不了,對文學(xué)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內(nèi)部”實(shí)際依然“重外部”上,中國比較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處。就此而言,中國文學(xué)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xué)“文學(xué)性”的解讀和展開。誠如有學(xué)者所言,比較文學(xué)在國別、總體層面構(gòu)成另外一種文學(xué)研究邏輯。但是假如承認(rèn)這一點(diǎn),是不是要成立國別文學(xué)和總體文學(xué)這樣的學(xué)科。有人可能會(huì)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外國文學(xué),即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別文學(xué),但是對于中國文學(xué)而言,其內(nèi)涵外延非常明確,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響其學(xué)科的合法性。而比較文學(xué)顯然不具備與之并列的明確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說總體文學(xué)了。同時(shí),國別文學(xué)中的“文學(xué)”,不僅指的是文學(xué)研究,還可以指文學(xué)現(xiàn)象,而比較文學(xué)的“文學(xué)”如果強(qiáng)制性地界定為文學(xué)研究,顯然是與國別文學(xué)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補(bǔ)關(guān)系,兩者邏輯聯(lián)系并不嚴(yán)謹(jǐn)。
三、結(jié)語
從文學(xué)的內(nèi)、外部研究這一角度來分析比較文學(xué)的“文學(xué)研究”性質(zhì)就可以發(fā)現(xiàn),比較文學(xué)仍然處于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態(tài)。究竟是外部研究還是內(nèi)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還是固守中國本位,這些問題依然需要進(jìn)行思考,特別是后者。在一個(gè)本位主義極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學(xué)里,奢談走向全球化,奢談比較文學(xué)發(fā)展的第三個(gè)階段,只能造成中國比較文學(xué)更加積重難返。比較文學(xué)的內(nèi)外部研究,表面上顯示的是文學(xué)研究的內(nèi)外之分,從本質(zhì)上講,反映的也是本位主義與外來主義之間的沖突。
本文作者:許相全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