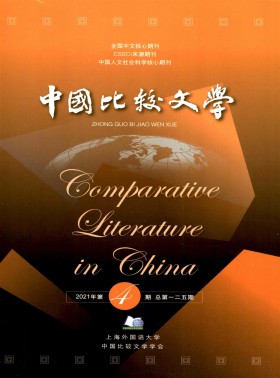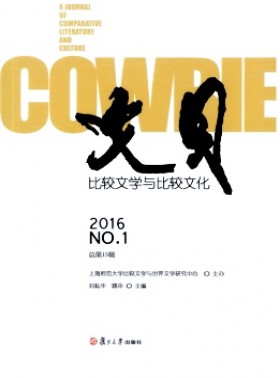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比較文學誤讀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羅明洲 單位: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漢語言文學系
比較文學在理論上注定是要引起爭議的。首先是定義之爭。截至目前,比較文學沒有一個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學科定義,雖然它不僅在國外甚至在中國國內也早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和一門“顯學”。1825年,法國兩個不太出名的教師諾埃爾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編了一本書《比較文學教程》,首次使用“比較文學”這個名詞。1827年法國學者維爾曼在巴黎大學開設比較文學講座,其后又出版一本書,叫《比較文學研究》。但他們都是只羅列史料,沒有給予比較文學以明確的定義。19世紀中期,當法國出現了一批比較文學著作之后,“比較文學”在使用的層面上,意義出現泛化。在急需給“比較文學”以精確定義的背景之下,法國學者卡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說法:“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聯系。”[1]4卡雷的學生、另一法國學者基亞也認為比較文學應是“國際文學關系史”[1]4。卡雷和基亞對比較文學的理論貢獻功莫大焉。他們從理論上為比較文學確立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強調了比較文學“事實聯系”這一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謂的“法國學派”的基礎。二戰之后,“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發難。雷馬克提出:“比較文學是一國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它表現領域的比較。”[1]5雷馬克對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做了極為寬泛的規定:除了文學關系的“事實聯系”之外,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研究,甚至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的范疇。
韋勒克更旗幟鮮明地要求比較文學要擺脫“從19世紀因襲來的機械的、唯事實主義的觀念,注重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實行一種真正的文學批評”[1]5。雷馬克和韋勒克的定義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促進了比較文學的發展,突破了法國學派“事實聯系”的藩籬,奠定了所謂的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基礎。自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誕生以來,兩國學派的爭執不斷。人們對兩派認知的爭論更是風起水生,其范圍和影響遠遠大于兩國學派的爭執。這使比較文學界空前活躍,表現出了比較文學的張力和活力。與此同時,又使比較文學這潭渾水越發清濁難辨。法國學派注重歷史性和科學性,主張比較文學應該擺脫美學的涵義,取得科學的內涵,使比較文學學理縝密、方法嚴謹,因此這種研究多適用于國際文學交流史或國際文學關系史。事實上,他們的研究確實為文學史的學科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美國學派認為文學是一種人類文化精神生產,而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時間內所產生的文學,必然存在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狀況。因此,比較文學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學現象的事實聯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討其異同及其深層原因和意蘊,從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學的本質和價值。只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學現象具有“可比性”,即可進行比較文學研究,可以不考慮它們之間到底有無事實聯系。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克服了法國學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證、過于苛求史料性的缺點,彌補了法國學派忽視美學價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優點。雖然它們為維護各自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而多有論爭,其實在他們的定義表述和理論闡發中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比較文學的追隨者和愛好者們不愿意實際上也不可能把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分得瓜清水白,著意遵循某一個學術標準,他們的大多數比較文學研究是兼備二者之長,為我所用。
其次是名稱上的名不副實。比較文學,無論是在學術界內部還是在學術界外部,都可能產生望文生義的誤解。就翻譯過來的意義上解釋,“比較文學”作為一個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為一個偏正詞組。就語法上來說,“文學”作為中心詞,“比較”是修飾成分。進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較文學在字面上的意義往往被理解為“比較的文學”。還可以理解為:動詞“比較”作謂語,名詞“文學”作賓語,把比較文學理解為一個動賓詞組。由此,比較文學就可以誤讀為“對文學進行比較”。不管是19世紀還是20世紀,甚至時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較文學學者多么煞費苦心地在理論上對比較文學作解釋,并不能夠阻止人們把“比較文學”當作是“比較的文學”或者是“對文學進行比較”。多少年來比較文學界所面臨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較文學”誤讀為“文學比較”。1997年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文學院院長巴柔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有學者提問比較文學究竟“比較”什么?巴柔詼諧地說:“我們什么也不比較,幸虧我們什么也不比較。”[2]復旦大學楊乃喬教授認為,比較文學不在于“比較”,而在于“匯通”。[3]照他們所說,判斷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屬于比較文學,不在于它們是否使用了“比較”兩字,而在于它們是否對所研究的對象與其他相關學科進行了體系化的、內在性的匯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僅在標題上還在內容上反復利用“比較”進行相同性或相異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在他們看來,比較文學代表了一種超越性的視野。它要求以國際的眼光、開闊的胸懷、全球觀念和開放意識去進行文學研究。它試圖突破國家、民族、語言、文化和學科的界限,從更大的范圍來洞察文學的特質。
比較是一種學術視域,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的一種內在的匯通性透視。這就決定了比較文學屬于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問題在于,“比較文學”屬于本體論而不是方法論多少還是帶有人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們業已習慣的思維定勢。“比較文學”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較相關。硬要把它賦予既新穎又深奧的內涵,確非讓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習慣思維:名實相符才稱之為名。人們不禁要問,若“比較文學”不可以“比較”,為什么要用“比較文學”冠名呢?在這里有一個悖論:比較文學的名稱不太恰當,但已約定俗成,目前在國際上仍在使用,并且沒有廢除的跡象。也許能尋找一個比它精當的詞取而代之,但可能會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亂。再次,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到深、由表面到實質的過程。諾埃爾、拉普拉斯以及維爾曼時代,比較文學僅僅是泛泛之談,連學科意義都沒有。法國學派的研究從理論上為比較文學確立贏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但他們排斥對作品的價值評價。美國學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但一些研究者對“可比性”的認識模糊不清,從而導致簡單比附。隨后的蘇聯學派特別是中國學派的崛起,把比較文學中的闡發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論研究引向了縱深。可以說,比較文學在不停的爭論中誕生,在不斷的探索中成長,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鑒于上述,對比較文學“霧中看花”、“遠看成嶺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曾經把“比較”錯誤地理解為比較文學的方法論。#p#分頁標題#e#
像這樣一位擁有國際名望的學者對比較文學尚且產生錯誤的理解,更遑論一般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在中國,比較文學曾長期被誤解。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在1978年以前,在國際比較文學研究高潮迭起之時,比較文學卻被排斥在中國學術領域之外。二是在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比較文學一下子受到學術界的熱捧,并長驅直入地進入大學本科課堂,繼而又逐步建立起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博士后的教學體系,出現了許多適應各種需要的教材和專著,數不勝數的比較文學論文見諸各學術刊物。諸如中世紀西方文學與中古東方文學比較、中西愛情詩比較、中西山水詩歌比較、堂吉訶德與阿Q形象之比較、高加林與于連、杜麗娘與朱麗葉之比較、渥倫斯基與周萍形象分析、中印龍女報恩故事之比較、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較、《紅樓夢》與《源氏物語》的美學比較、《長生殿》與《安東尼與克莉奧佩拉》之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說藝術比較等比比皆是、屢屢翻新。它們有些出自大家之手,像學術界精英、外國文學領域宿將、比較文學界元老,甚至還有文壇大腕也多有染指。此類文章在《文藝評論》、《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等中國著名學術雜志上屢見不鮮。此類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研究的著眼點滯留在表象上,著意去尋找兩個文學現象的類似性與差異性:雙方不同之處是什么,相同之處是什么,分析其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隨后便是將上述兩種歸結為“社會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同異,也即所謂的“X+Y或者X與Y”式的比較研究,一種簡單化的個體與個體之比或是簡單類比。使比較文學陷入到“詩學比較”的窘境。這種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引起了學術界大規模的攻擊,遭到學術精英們的清算,斥之為沒有意義。于是,“X+Y或者X與Y”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中國的比較文學實踐注定要走過一段坎坷泥濘的。首先,中國比較文學要實現突圍。鴉片戰爭至五四前夜,在翻譯西學極為繁盛的情況下,在中學西學孰優孰劣的討論熱潮中出現了像王國維、梁啟超等博古通今、融匯中西的學者,促進了中國比較文學在平行研究方面的發展。從五四到建國,政治動蕩、戰爭頻仍,中國比較文學雖有長足的進展,但作為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不可能有更大的發展。
建國后的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雖有一些文章談及中外文學關系,也僅限于中俄(蘇)文學,且少有深刻之論。“十年”中國大陸拒絕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的文章幾乎絕跡。時至20世紀70年代,臺灣大學相繼開設比較文學碩士班、博士班。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文學系,1978年香港又成立比較文學學會。恰值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形勢喜人且逼人,比較文學全面復興和突圍迫在眉睫。應當說,比較文學在精英的頭腦還沒有揣摩透的情況下,中國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已經擺在了普通學者的面前。中國比較文學在摸索著前行。因此,相對來說便于操作并且在中國大陸有一定歷史積淀的平行研究也就悄然前行,且呈一時之盛。其次,中國比較文學要凸顯實績。沉寂多時的中國比較文學枯木逢春,順風順水,不僅值大展宏圖之時,而且有大展宏圖之勢。相對遲緩的大陸比較文學在20世紀80、90年代突然釋放了諸多能量:1981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會;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1995年北京大學開始招收比較文學博士后;1998-2000年,首都師大和四川大學先后創辦比較文學系。冠以“比較文學研究成果”的論文、著作更是鋪天蓋地,難以備述。比較文學的學者精英也受這種潮流的裹挾而自覺不自覺地側身其間,于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中為比較文學研究增磚添瓦,或者以海納百川的肚量以極其寬容的態度接受了平行研究的成果。以上表述,并非是說“X+Y或者X與Y”研究模式是機會主義的產物。“X+Y或者X與Y”是中國比較文學復興初期被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模式,大多被用在平行研究中。平行比較是認識論的低級階段,它常常是不可避免的。“X+Y或者X與Y”存在著簡單對比和泛比即文學比較的傾向,但這是一個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的認識過程。問題在于,我們可以要求人們不能停留在簡單對比的層面上,但不可以徹底地、全面地、不加分析地否掉定“X+Y或者X與Y”。正如我們成年后不能去否定掉我們的童年,更不能以我們的成人處境去否定他人的童年階段。已故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任會長、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楊周翰先生曾說:“西方比較文學發源于學院,而中國比較文學則與政治和社會上的改良運動有關,是這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4]這就是說,中國比較文學從來就不是僅和極少數學術精英有關的學問,而是始終貫穿著關心現實關心生活的人文主義精神。平心而論,“X+Y或者X與Y”模式在中國比較文學復興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很多比較文學工作者甚至還包括現在的一些比較文學大師級的學者都是從“X+Y或者X與Y”模式開始走上比較文學道路的。
《比較文學讀本》的作者王福和說過:“任何一個比較文學工作者,對‘X+Y或者X與Y’贊成也罷,貶斥也罷,他所從事的哪一項比較文學研究能與‘X+Y或者X與Y’脫得了干系呢?……對此,我們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討伐聲中既感到恐懼,又感到困惑”。[5]269中國比較文學的領軍人物之一、北京師大教授陳?嚴肅指出:“只要人們承認平行研究還不失去其科學價值,那么‘X+Y’式的比較研究就不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對‘X與Y’式的研究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5]270不僅如此,陳?教授以《莎士比亞〈皆大歡喜〉與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林沖形象與威廉•退爾形象的比較研究》等為題,為“X+Y或者X與Y”模式吶喊助威,為那些現在正在從事或準備將來從事“X+Y或者X與Y”比較研究的第一線教師增加信心并予以支持。文學比較不等于比較文學,但是比較文學卻自始至終離不開文學比較。如果文學比較再開放拓展一些視野,也就是說逐步進行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跨越學科門類和跨越文化文明的文學比較研究,就可以成為現行學界認定的比較文學水準。那么,比較之于比較文學,無疑是這門學科的重要特征和手段以及研究思維的邏輯起點。
時下,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仍是一門“顯學”,但絕非精英之學,著意鑄造比較文學的神壇,人為地抬高比較文學的準入門檻只能使比較文學的道路越走越狹窄。換言之,既然文學比較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邏輯起點、是比較文學學者的學步階段、是一般比較文學追隨者容易掌握的研究模式,何不給“文學比較”一定的空間以進一步發展學科優勢,何不給年輕的初學者一定的信心以支持比較文學的未來前景。當然,也期望對“X+Y或者X與Y”模式加以引導并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X+Y或者X與Y”模式更符合比較文學的學理。#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