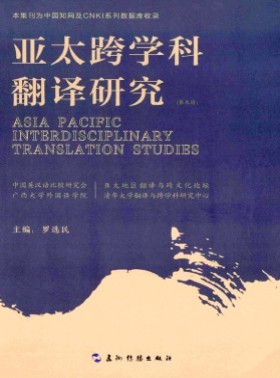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學科創建論文:中國哲學史早期創立的得與失,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蔣國保 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日本哲學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論》中首先使用“哲學”一詞。而“哲學”一詞由日本輸入中國,具體年代不詳,大約在19世紀最初幾年。至于“中國哲學”一語,最初在我國使用是在1906年,證據是那一年劉師培(劉光漢)在《國粹學報》上發表了《中國哲學起源考》。劉師培堅持“以子通經”的學術取向,其眼中的“中國哲學”,主要指中國傳統學術范疇中的子學與經學。劉氏的這一認識,大體反映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學人對中國哲學的普遍認識。丁寶銓為山西巡撫,他于宣統三年(1911)為傅山《霜紅龕集》作序,在該序中,他也是將“近日之哲學”與中國固有“諸子道釋”并提,以為中國之“諸子道釋”學說就相當于西學范疇之“哲學”:“國初巨儒,學宗漢宋,旁及地志、算術而已。究心子部者少,況乃二氏。嗇廬生際其時,岳岳兀兀,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后,遂成風氣。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畢諸著述),通釋入于儒者有人(如羅臺山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諸子道釋,一以貫之,名曰哲學。其大無外,其細無間,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學,①實嗇廬氏之支流與其余裔也。綜是而論,一二緒余,精誼所結,演繹成家,此余所謂嗇廬之學斷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窺其津涯者也。”
將中國固有的“諸子道釋”之學與西學范疇之“哲學”并提,并不等于“中國哲學”已確立為一門獨立學科,實際上“中國哲學”從傳統經學、子學、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獨立學科,在1906年之后,大約又經歷了10來年的時間。這10來年間的最初幾年情況已難了解清楚,現今根據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中的回憶,大體可以了解北京大學在1915年已開設了“中國哲學”課程。一般地說,一個大學開設某課程,即意味著該課程所講之學問,已成熟為學科范疇的學問,標志著該學科已創立。但北京大學于那時(1915、1916年)正式開講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所講的內容,實際上仍然屬于經學范疇。這個斷言非臆斷,有堅實的依據,其依據就是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中的這么一段敘說:“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位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么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②在北京大學開“中國哲學”課程一年后,中國第一部《中國哲學史》專著正式出版。這就是1916年9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謝無量著《中國哲學史》。謝氏的這部《中國哲學史》,嚴格地講,算不上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則它的出版,同樣不能作為“中國哲學”已成為現代學科的標志。標志著“中國哲學”已成為現代學科者,應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該著雖然只涉及先秦時期的中國哲學思想,不包括秦漢之際直至晚清的中國哲學思想,但從以新方法系統地闡述中國哲學的意義上講,它的確算得上中國哲學史學科已創立的標志。正因為它是第一部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哲學史,所以在它剛問世時,便受到以舊眼光看中國哲學的學究的批評與嘲諷。馮友蘭曾提及這一點,他說那位從“三皇五帝”開始講中國哲學的教授,拿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在課堂上笑不可抑,對他們三年級學生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③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式出版在1919年。10年后,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鐘泰為該著列“凡例”10條,其中有云:“中西學術,各有系統,強為比附,轉失本真。此書命名釋義,一用舊文。近人影響牽扯之談,多為葛藤,不敢妄和。”從這條著述原則可以看出,鐘泰的《中國哲學史》,應是不認同胡適的中西哲學相比附的做法、而特意與胡適唱反調的產物,盡管他在書中沒有提及胡適的名以及胡適的書。鐘泰的《中國哲學史》出版2年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④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而上下2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則時在1934年。馮友蘭的2卷本《中國哲學史》,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相比,它不是有頭無尾之作,而是對中國古代哲學之整體作系統闡述之作;同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相比,它之優長,不僅體現在它在量上遠遠超過謝、鐘氏二著的篇幅,而且體現在它突破了謝、鐘二氏傳統的敘述方式,屬于運用現代哲學方法來闡述中國哲學發展歷程之作。因此有學者高度評價它的價值,稱之為“用現代哲學方法編寫的第一部中國哲學通史著作,對中國哲學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有一定的開拓性意義”①。1933年,范壽康在武漢大學編成“中國哲學史”講義,以為教學用。該講義修改成書后,于1936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出版時取名為《中國哲學史通論》。
范氏在此書“付印題記”中寫道:“就內容言,疏漏錯誤,自知不免;即間有所得,亦多采自當代著作家之說,出諸自創者蓋鮮。而余在是書之編撰上最受其補益者,厥推武內義雄、宇野哲人、境野黃洋、小柳司氣太、河上肇及梁啟超、周予同、胡適、馮友蘭、雷海宗諸家。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從范氏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這部中國哲學史,是兼收中日當代著作家學術成果的產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內容上固然多屬于中國哲學史方面的成果,但也當包括中國之經學史、儒學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在范氏《中國哲學史通論》出版的前一年,張岱年開始寫《中國哲學大綱》。該著于1937年寫出初稿,直至1943年才首次在北平私立中國大學印為講義,后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盡管在新中國建立以前,已制版,但因故推遲至1958年才由商務印書館照原制版出版,出版時,署名宇同。這是中國第一部從中國哲學固有問題出發撰寫的中國哲學史。由于它的寫作與出版,跨越舊中國新中國兩個性質迥異的時代,其對于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的實踐與方法來說,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代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6部著作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但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繼承關系,二是對立關系,三是超越關系。這都是從如何著述的動機上說的。也就是說,就如何著述這一考慮來說,這6部著作,有的重在考慮如何在繼承的同時豐富之、推進之,有的基于反對的立場來考慮如何結構與展開,有的則基于超越的立場來考慮如何結構與展開。現在不妨稍作具體分析。先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與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的關系。這是最難說得清楚的問題,因為斷然否定或肯定胡適受謝無量的影響都有可懷疑的地方。說胡適未受謝無量的影響,為大多數學者所相信,但他們的這一相信,是建立在“先見”之上的,其“先見”就是: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是對日本諸“支那哲學史”的販賣,沒有新意,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則屬于以西方現代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第一部”,有新意是它的根本價值所在,兩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我在沒看到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之前也相信這種看法,后來看到了它,對此看法就產生了一些懷疑。其中最值得發問的是:胡適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斷代,是否承襲謝無量的斷代?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將中國哲學發展史斷為三代,依次稱為“上古”、“中古”、“近世”。#p#分頁標題#e#
“上古”是指邃古至秦末,“中古”是指“兩漢至唐末”,“近世”是指“宋元明清”。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因為只限制在秦末以前的中國哲學,所以在目錄中未反映其斷代,但他在其著第一篇“導言”中,還是較詳細地論述了“中國哲學史可分三個時代”②:“自老子至韓非,為古代哲學”;“自漢至北宋,為中世哲學”;“明代以后,中國近世哲學完全成立”①。除了一字之改,②胡適的這個斷代與謝無量的斷代,沒有任何本質的不同。既然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出版在先,那么胡適就很難避承襲謝無量的斷代之嫌,否則,他的斷代為何同于謝無量的斷代?當然,還有一種解釋,就是謝無量、胡適的斷代同是承襲日本學者關于中國歷史的斷代。日本京都學派奠基者之一的內藤湖南,著有《中國史通論》上、下,③他已經明確地將中國古代史劃分為三段:上古、中古、近世。在內藤湖南看來,自“三皇五帝”至西漢為“上古”,自兩漢至唐末為“中古”,自宋至清亡為“近世”。內藤湖南關于中國歷史的這一斷代,是否為日本學者照搬為中國哲學史的斷代?因未得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出版的諸“支那哲學史”,對這個問題不敢貿然回答。這里敢于肯定的是:無論胡適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斷代,是否直接承襲謝無量的斷代,但有一點是不難推定的:由于謝無量的斷代明顯是照搬日本學者關于中國歷史的斷代,所以從胡適的斷代同于謝無量的斷代就可以看出:中國學者一開始創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在最基本的斷代問題上,就明顯受日本學者關于中國歷史之斷代的影響。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獨立的標志,因而在它之后出版的4部中國哲學史,無論作者有無申明或者申明如何,都應視為對胡適著述立場、取向與方法的不同取舍:要么呼應與效法,要么反對與背離,要么繼承與超越。公開申明受胡適影響的為范壽康,雖未明言然實際上暗反胡適的是鐘泰,而馮友蘭、張岱年則都是力圖超越胡適。鐘泰的《中國哲學史》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相比,有三個顯著的不同:一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鐘泰明確地說:“近人影響牽扯之談,多為葛藤,不敢妄和。”這應該就是針對胡適用西方現代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而言的。④從反對以西方現代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立場出發,鐘泰的《中國哲學史》,就本質講,尚未突破傳統學術范疇。這從該書“凡例”所列多與傳統著述慣例相通可明。二是斷代的不同。鐘泰將中國哲學史“略分四期:一自有史以迄嬴秦,是為中古史;二自漢迄唐,是為中古史;三自宋迄明,是為近古史;四有清一代,是為近世史”。
這一斷代,是從謝無量、胡適所斷的“近世”中再分出“近古”。以“宋明”為“近古”這一斷代,體現了他想超越謝無量、胡適的意圖。超越之(謝無量、胡適)的意圖固然相同,但為之的做法有別。對謝無量《中國哲學史》(上卷),他實際上是有所吸收與仿效,例如照用“秦滅古學”的提法,并以它為章標題;而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卻反其道而行之,無絲毫取舍。三是敘述方法的不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敘述,主要是貫徹了三個方法,即證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統的方法,⑤這三種方法,都不為鐘泰所取,他在其著《中國哲學史》中所用的敘述方法,一言以蔽之,可謂“‘史’的方法”。具體地講,他的敘述,是仿效“史傳之體裁”:“述一家之言,則著其人;總一代之變,則標其事。”⑥而具體到“著其人”,則又“兼四體”,有分有合、有附從有連及,“附從以上,著之章目;連及之者,但見本文”⑦。馮友蘭的2卷本《中國哲學史》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相比,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斷代上不取謝無量、胡適的“三代說”,亦不取鐘泰的“四代說”,而是將中國古代哲學史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前后兩個時代:“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為經學時代。”①馮友蘭說:“中國哲學史,若只注意于其時代方面,本亦可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此各時期間所以之哲學,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稱,本書固已用之。但自別一方面言之,則中國實只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也。”②從此說可明,馮友蘭是基于中國“無近古哲學”的認識(而這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學為判斷標準而得出的認識)而將中國哲學分為二代,未必是特意針對“三代說”、“四代說”;也就是說,他在一定意義上也不反對將中國哲學分為三代。
那么,他分二代的深意何在?我認為,這不是按狹義的歷史過程作出的劃分,而是依據中國思想前后期之性質不同而作出的劃分。就今天的認識來講,此劃分似表明馮友蘭在那時已對這個問題———哲學思想的發展,有其固有的邏輯軌跡,未必與狹義的歷史軌跡完全一致———有了一定的認識。另是在敘述方法上的不同。這當然不是說,馮友蘭的2卷本《中國哲學史》在敘述上排斥胡適注重的證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統的方法,而是說除了這些方法,馮友蘭的敘述,尚有胡適的敘述所不具有的方法。胡適在談及馮著時曾評價馮的敘述仍是“正統的”。言下之意,是說馮的敘述尚缺乏現代眼光,仍未超出傳統學術范疇。馮氏回答說,他的“正”是辯證法范疇里的“正反合”之“合”意義上的“正”,非照搬意義上的“正”。在當事人之外,尚有陳寅恪的評論:“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③。在陳氏看來,馮著所以能做到不依自己生活之時代、自己所居之環境、自己所具之學養而穿鑿附會古人,全在于他對古人思想真正做到了“了解之同情”。陳氏予馮著的這一評論,應該說準確地揭示了馮著在敘述方面的特色。正因為這個特色的存在,一部用現代學術方法寫成的著作,在“以自身之哲學”談古代哲學的胡適看來,就與傳統的中國哲學史著述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既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影響,也受馮友蘭的2卷本《中國哲學史》的影響,但相比而言,他受后者的影響要大得很多。在內容的取舍上,他多效法馮著而非胡著,例如仿馮著將中國古代哲學史從孔子開始談起,而不是學胡著將中國古代哲學史從老子談起;馮著將《老子》置于戰國的道家來談,他也將老子置于戰國的道家來談;在概念的借用上,他也是多從馮著,例如他學馮著以“子學”統稱先秦時代的哲學,而以“經學”統稱兩漢以及宋元明清哲學;但在解釋上,他亦有舍馮說而取胡說之處,例如對于孔子的“忠恕之道”,胡氏將之解釋為“認識的方法”,而馮氏將之解釋為一種“人生哲學”,他則取胡說而舍馮說,強調“忠恕之道”應理解為“認識的方法”而非一種“人生哲學”。④#p#分頁標題#e#
如果說范著與胡著、馮著有什么明顯的不同的話,照本文作者看,在于它按照中國歷史發展的次序,將中國古代哲學史區別為先秦、漢代、魏晉、隋唐、宋明、清代6個時代,并以“子學”、“經學”、“玄學”、“佛學”分別稱謂之。這樣的劃分與稱謂,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已成為著中國哲學史的慣例,是值得高度重視的;照范氏自己看,則在于觀點“與當時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辯證法闡述我國歷代各家之思想”。此說見于范氏《三聯重版〈中國哲學史通論〉序言》,該“序言”寫于1982年7月25日,則我們今天是否應根據范氏的這一說法來研究范著的特點,就成為不得不十分慎重的事。就我的膚淺的認識而論,固然不應斷然否定他在其著中以“唯物辯證法闡述我國歷代各家之思想”,但除該書“緒論”有關論述貫穿了唯物辯證法思想外,從該書正文中我們很難一眼看出其所主唯物辯證法哪一種思想。反倒是,從他的書中,很容易發現傳統學術范疇中的內容,例如在該著的第二編第一章中,他細致地論述如何具體地從所據之經典以及辨別標準上區別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很容易明白,這本是傳統經學所談的內容,而非談中國哲學一定要講的內容。作為反映“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的實踐與方法的最后一部著作,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相對于它之前的5部中國哲學史,無疑具有集大成的優勢,但張著的意義,顯然不是體現在它對之前的5部中國哲學史的繼承、吸收、豐富、發展上,而是體現在它一改它之前的5部中國哲學史的著述路數,首次從中國哲學固有問題出發系統闡述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關于此著的特色,張氏在“自序”里曾論及。張氏先后為其著寫有3篇“自序”①,按時間先后依次曰“自序”(1937年2月3日)、“新序”(1957年2月28日)、“再版序言”(1980年9月14日)。在1937年的“自序”中,張氏重在談“本書的方法”時指出其著貫穿四種方法,一曰“審其基本傾向”,二曰“析其辭名意謂”,三曰“察其條理系統”,四曰“辨其發展源流”。
在1957年的“新序”中,為當時形勢所迫,張氏主要是就其著的缺點進行“自我批判”,但也概括性地論述了其著的特色:“本書寫作的原意是想對中國古典哲學作一種分析的研究,將中國哲學中所討論的基本問題探尋出來,加以分類與綜合,然后敘述關于每一個問題的思想學說的演變過程。在探尋問題的時候,固然也參照了西方哲學,但主要是試圖發現中國哲學固有的問題,因而許多問題的提法與排列的次序,都與西方哲學不盡相同。在敘述中國哲學各方面思想時,也曾經力圖闡明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義思想與辯證觀念。”在1980年的“再版序言”中,張氏主要談了“中國哲學史中兩條路線斗爭的簡單輪廓”,而這又是為了彌補他自認為的“本書最大的缺點”②;此外,他還論及此書在取材和論述范圍方面的缺欠。取材方面的缺欠,是指對《管子》和《呂氏春秋》“完全忽略了”、對“唐代劉禹錫、柳宗元的學說未加引述”、對“方以智、陳確的思想更未提到”、對中國佛學思想“沒有講”、對近代哲學“存而不論”;論述范圍方面的缺欠,是指書中的論述只限于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認識論),而對于“歷史觀未涉及”。客觀地講,張氏關于其著之得失與方法的闡述,切合實際,是可信的。據之以比較其他5著之得失與方法,當不難明白以下幾點:其一,張氏力圖揭示的中國哲學的演變過程,在其著中并不是通過對該哲學時代性、學派性的確立與界定來表述的,而是通過對該哲學問題、范疇、概念的確立、分辨與會通來表述的,這也就是說,張著關于中國哲學發展過程的揭示,不是顯性的,而是非顯性的。非顯性的演變過程得以揭示,關鍵在于按歷史之線式進程來排比中國哲學問題之提出、展開與終結的邏輯軌跡。這應該屬于對“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方法的不自覺運用;其二,胡著所運用的方法(證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統的方法)、馮著運用的方法(了解的同情),在張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但張著所注重的范疇、概念的分辨方法,卻是其他5著所缺欠的,盡管它們各自缺欠的程度大小各異;其三,張著在范疇、概念的分辨以及思想源流的梳理上,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唯物、辯證法思想原則,這較之范著,可謂是對唯物、辯證法思想更高程度的自覺;較之其他4著,可謂是開運用唯物、辯證法思想原則研究中國哲學之風氣之先。
探討了足以反映“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的實踐與方法的6部代表作之著述時代、基本內容以及特色之后,現在有必要就該探討引申出幾個話題。首先,用“正反正(合)”辯證眼光看,不妨將這6部書二二一組分為三組,其中謝著、胡著為第一組,代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正”過程;鐘著、馮著為第二組,代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反”過程;范著、張著為第三組,代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正(合)”過程。就“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正反正(合)”過程而論,6部書中以胡著、馮著、張著三書尤為重要;而胡著、馮著、張著三書中又以張著尤為重要。張著的重要性不在于內容的豐富超越其他著作、也不在于方法上之創新比它著更獨特,而在于它的“問題意識”獨到:以中國哲學的“問題”規整中國哲學的內容,以中國哲學固有的范疇貫串中國哲學的內容,以中國哲學的范疇之衍演與擴展反映中國哲學的發展。這樣的問題意識,應該是對它之前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之實踐的自覺反思的產物,對于我們今天探討“金岳霖之問”有重要啟示,它促使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張著及張著樣式的“中國哲學史”,是屬于“哲學在中國”還是屬于“中國的哲學”?其次,就內容而論,張著與其他5著的一個明顯區別就是:其他5著程度不等地存在著經學與哲學、學術思想與哲學思想混而不分的現象,而張著則比較“純哲學”,徹底舍棄了屬于經學及學術思想、政治思想的許多內容。問題是,正如張氏自己所指出的,正因為堅持求“純哲學”,使得張著不免在“取材和論述范圍”方面存在明顯缺欠。張著所遭遇的這一矛盾,是否意味著創建“中國的哲學”就一定要遭遇兩難問題:求中國哲學之純粹性就勢必犧牲中國哲學之豐富性,反之亦然。#p#分頁標題#e#
再次,如果說胡著、馮著對西方現代哲學方法的運用是自覺的、主動的,那么比較地說,張著對西方哲學方法的運用卻是非主動的、不得已的。之所以不得已運用西方哲學方法,照張氏自己的解釋,是因為談中國哲學卻“以西洋哲學為表準,在現代知識情形下,這是不得不然的”①。“不得不然”云云,顯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張氏主觀上并不想以西方哲學方法來把握中國哲學,但客觀上他把握中國哲學又只能以西方哲學為表準。換言之,張氏固然可以做到以中國哲學固有問題、中國哲學固有范疇展開邏輯來敘述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但他在界定中國哲學問題的性質(例如屬于宇宙論還是認識論)、把握中國哲學范疇的蘊涵、評價中國哲學思想的價值上,根本就做不到不以西方哲學為表準。張氏所難以化解的這一主客觀矛盾,讓我們警惕的應該是:將創立“中國的哲學”建立在徹底排除西方哲學方法之運用前提上的任何構想與實踐,對于成功創立“中國的哲學”來說,可能都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