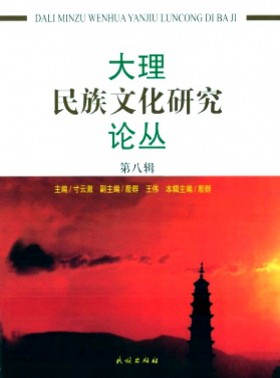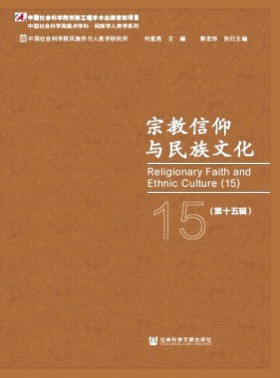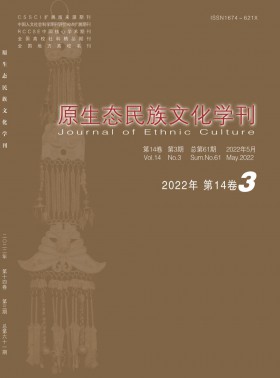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民族文化傳承路徑,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就是把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保護、傳遞和發展下去,其旨歸在于民族文化的發展、民族精神的傳承。少數民族文化場域的復雜交織態勢彰顯了民族文化認同和多元文化融合的歷史使命和時代緊迫感。筆者認為,在多元文化交叉碰撞的背景下,文化的傳承過程體現為文化融合過程,通過文化傳承最終實現文化融合。其中,適切的文化傳承路徑顯得尤為關鍵和重要。 一、少數民族文化場域的復雜交織態勢。 人類學考察關注人、文化與自然三者之間外在的和內部的關系構型,以及這些關系構型所表達出的形式、形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征。即“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各文化元素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個綜合場,它是一個文化的存在形態,是一個有向心力的、動態的和有機的系統”[1]。 (一)民族原生態文化與次生態文化的交融存在。 從生態的視角看,文化是人類適應自然生態環境的特殊方式,民族生態文化的核心,在于民族文化的自然性與原生性。簡而言之,民族文化的原生態特性是民族發展進程中歷史與自然的綜合生成,是原生場基礎上的文化養育。“原生場是個體生長的天然而成的空間場域,包括自然環境、本土文化與經濟形態等三方面,其核心為民族文化心理場,相對于個體而言,這是無法選擇的先在的、自在的環境”[2]。原生態文化指場域內部的自然生態和原始的民族文化的構成,文化是自然生態基礎上的原文化,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具有特定情境性和地區性)———相對他者視角下的地方性知識[3]。又表現為一種文化的獨特性,即受自然條件制約,少數民族文化表現出相對獨立性和封閉性,是未受外來文化沖擊的傳統文化形態。次生態文化就是基于原生態的文化生成,是相對于個體而言的繼生的、自覺的環境。在以民族文化為根基和靈魂的基礎上,次生態文化表現為文化的時代性和多變性,并與原生態文化相互交融,不可分割。 (二)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叉與碰撞,形成復雜的文化場域。場域作為一種關系構型,其活力在于各元素所構成的沖突與融合的動態關系———主要表現為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靜態文化與動態文化的互動和交流。這種作用關系形成特定時空的文化場域和文化場力,在場力的輻射下,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同向或逆向而行,最終促成三種具體情形:融合共生、對立沖突和隔離邊緣化。而在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融合與沖突是極為顯著的,表現為民族文化與現代市場經濟文化的有機結合、文化商品化與文化原生態的沖突、民族文化在外來文化沖擊下的異化等。 二、文化的民族性及文化傳承釋析。 文化傳承不只是簡單的文化元素傳遞與保存,更是多元文化交織下的文化發展、文化認同和文化融合,并最終走向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 (一)文化的民族性解釋。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本尼迪克特從民族的角度出發,認為“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動方式,一種使這個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4]。文化既是一個民族特殊性的象征,也是一個族群存在與演進的根本。“每一種文化代表自成一體的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價值觀念,因為每一個民族的傳統和表達方式是證明其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最有效手段”。[5]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文化與民族發展的特定關系,即文化的精神和價值層面在民族生存與發展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牽引作用,如西南大學張詩亞教授所言,“文化的核心是某些根本的結構性的觀念,正是這些觀念使世世代代的人們團結在其周圍,象征了該社會的延續性”[6],正是這些結構性觀念構成了民族文化的靈魂,在根本上推動民族的發展。可見,文化與民族性是不可分割的,這種特性突出了民族生存的文化決定性和文化存在的民族依托關系,表現為各種特殊的民族文化形態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具體為民族文化的物質形態和精神形態,在根本上體現為堅定的民族認同和民族自豪感。 (二)“文化傳承”的意蘊。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認為:“群體中個別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關,但屬于社會人的生活用具和行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卻可以不跟著個別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會性利用社會繼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參差不齊,使它可以超脫生物體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興廢的歷史規律。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歷史性。”[7]傳承是文化的本質屬性,文化傳承是一種能動的社會歷史過程,所以民族文化才能在共同體的精神維系、民族性格的塑造、社會結構的構筑與整合等方面發揮巨大的能動作用。有學者認為:“文化傳承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文化的民族性,從一個民族人們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文化傳承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的再生產,是民族群體的自我完善,是社會中權利和義務的傳遞,是民族意識的深層次積累,是縱向的‘文化基因’復制。”但是,“文化傳承不是簡單的文化元素傳遞,而是按照文化適應的規律和要求作有機的排列組合,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建構作必要的文化要素積累”[8]。實際上,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就是對民族文化基因的復制、民族文化的再生產和重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是文化元素在新的社會秩序下的結構性調整。從文化的傳承過程看,它不僅體現為文化的延續維度,更是發展維度。文化的發展實質上是文化的生長與豐富的過程,體現為多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其實質是文化的活態屬性,正是這種活態特征賦予了文化本身歷史價值和時代價值。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任何活態文化都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只有適應現代社會環境,被文化主體認可才能得以生存和延續”[9]。目前,我國很多少數民族地區已經呈現出區域現代性特征,即多元文化并存。在這種背景下,文化的傳承實質上是民族文化精髓的傳播和發揚,并使民族成員形成深厚的文化認同,促進多民族文化的融合。#p#分頁標題#e# 三、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路徑。 (一)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教育路徑。教育是文化傳承的根本途徑。 “教育是一種文化傳遞過程,人生活于文化之中,人的發展是接受文化傳遞,適應文化變遷的過程,而文化變遷與教育變遷具有一致性”[10]。教育本質上是對人心靈的培育與涵養,體現在其文化傳承的屬性上,就是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認同、文化自覺、文化自豪感的培養。具體表現為以下兩種傳承形式。 1.學校教育。 “學校是一個聚匯、傳遞文化的高級文化體,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以不同的文化為主體的學校對人產生不同的整合作用”[11]。在學校這個場域中,不同的生命個體與文化交融并整合。同時,學校教育的規范性和選擇性又決定了其在文化傳承功能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學校教育有其目的性、程序性和組織性,在現代教育范式下,體現為一種系統、序列的傳授模式。這種模式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上,還體現為教育的文化選擇屬性和教育價值取向性。在少數民族教育中,應該選擇能夠體現民族文化特性的教育內容,如民族文學、民族音樂、民族美術、民族體育等,加強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2.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 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在民族文化傳承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教育產生并融合于民族成員的成長環境,植根于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伴隨著民族性的養成和民族文化的發展,并作為文化傳統和精神訴求,熔鑄于民族心理。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傳承過程。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載體,承載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個體的生長,實質上就是一個民族文化因子的發育和逐步成熟,是一個自然和天然的過程,是一種濡化過程,即“習慣系統在日常生活教育中發揮教育作用的具體形式”[12]。這種習慣系統就是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說的“經驗的連續性”,社會個體首先對這種經驗適應,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習慣,包括個人習慣和群體習慣。群體習慣就是一個民族沿襲的風俗、禮儀、慣例等。個人習慣寓于群體習慣中,是個體在生活實踐中接受日常生活教育而形成的。作為濡化結果,它是民族習慣體系的現實體現;作為個人日常生活框架中的調節規則體系,它又表現出個體的性格差異。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就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落地伊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13]。如果說這種塑造模式是教育的話,那它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自我教育,二是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自我教育是一種涵化或濡化,而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是一種教化。前者是內在的動力,后者是有意識和目的的行為。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自我教育表現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不但是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自覺,也是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接納,更是對國家深厚的歷史文化沉淀、價值觀、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費孝通先生認為:“文化自覺的意義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14]文化認同,集中體現為對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和同一性認同,前者即對本民族的民族性的認同,具有獨特性。后者即對一種堅定的和獨特的忠實于自身的方式的信念———“首先是我們作為個人與我們自己的語言、地方、地區和民族共同體及其特殊價值觀念(倫理的、美學的,等等)的自發認同;是我們吸收歷史、傳統、習俗和生活樣式的方式;是我們接受、分享或置身于一種共同命運的感覺;是這樣一種使我們置身于共同自我中的方式”[15]。其次,又是基于強烈而深厚的民族文化歸屬感和自豪感,對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吸收,對國家文化、經濟與政治的高度認同。 (二)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其他路徑。 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其他路徑,可理解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形態之外的文化傳承途徑。基于當前少數民族地區旅游文化的迅速崛起和發展,將發展民族地區的旅游文化作為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一種重要路徑,是必然的,也是現實的。 旅游開發在民族文化場域中,可以被理解為少數民族群眾逐步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從文化的角度看,少數民族的物質文化在現代社會發生變遷,而在精神層面上,淳樸的少數民族群眾面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價值觀念的沖擊,也需要作出調適。文化傳承的內源性動力只能源于居于該種傳統文化“主位”的群體的“文化自覺”。在旅游開發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文化場域中,文化傳承的根本使命在于喚起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自覺,這種自覺在旅游經濟形態下表現為對本民族文化的尊重、認同和保護,還包括對其他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的吸收和借鑒,是基于民族認同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旅游人類學認為,旅游過程也是游客與東道主進行文化接觸、碰撞的過程,“不管人們愿意還是不愿意,只要發生文化接觸,其社會文化就會發生變化”[16]。要正視旅游開發對民族文化傳承的意義,并將其視為一種有效的傳承路徑。事實上,已有較多研究證明了通過旅游開發傳承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如有外國學者在研究了尼泊爾夏爾巴人為登山旅游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之后,認為旅游非但沒有破壞夏爾巴人的傳統文化,反而加強了他們的傳承和延續。[17]我國的一些學者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如覃德清在對漓江流域民族村鎮的長期考察中發現,文化保護的關鍵是要恢復民族記憶以及與民族身份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適當的旅游開發可以推進這一過程的發展,從而為鄉間“小傳統”文化的傳承提供支持[18]。同樣,在廣西龍勝梯田文化區,旅游開發使少數民族文化得以傳播,并促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