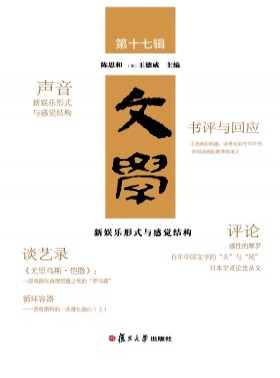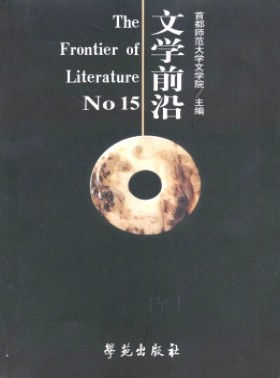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文學(xué)翻譯的語言模糊定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語言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語言的一個基本的、客觀的屬性,是語言學(xué)中存在的固有現(xiàn)象。語言,是人類社會在長期的進(jìn)化發(fā)展中,在對世界有了認(rèn)識與思考以后開始出現(xiàn)的一種用以記錄和表述世界的工具。在客觀世界里,被描述的事物既有具體的、可計量的,也有抽象的,不可被計量的。這就意味著一些客觀存在的事物無法用具體的、量化的標(biāo)準(zhǔn)來進(jìn)行描述,于是,即便是對客觀事物的描述,也出現(xiàn)了“不確定”。這種“不確定”帶來的就是語言的模糊表達(dá),模糊語言也就應(yīng)運而生。語言的模糊性,并不是語言系統(tǒng)中的一個缺點,相反,這種模糊性使語言的表達(dá)更具有彈性,豐富了語言表達(dá)的構(gòu)成與層次。[1] 特別是當(dāng)語言以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出現(xiàn),并且需要將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翻譯時,語言的模糊性就變得更加復(fù)雜。在文學(xué)作品中,除了原有的單一語言的模糊性外,還表現(xiàn)在字句、文章的內(nèi)涵與外延的擴(kuò)散性上,這種更加抽象的語言表達(dá)方式使語言的模糊性變得異彩紛呈,更加的不可控。這樣也就加大了文學(xué)作品翻譯的難度。如何在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工作中,把握好語言的模糊性與文學(xué)作品表達(dá)的精準(zhǔn)性之間的平衡,是我們在文學(xué)翻譯中一直努力追求的效果。 二、文學(xué)語言模糊的層面 文學(xué)作品,從細(xì)化來看,還是由不同片段、篇章的文學(xué)語言組成,文學(xué)翻譯中的模糊性,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文學(xué)語言的模糊性導(dǎo)致的。要完成一個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對于翻譯者來說是一項極具挑戰(zhàn)性和考驗的工作。總的來說,文學(xué)語言的模糊性又能夠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用詞的模糊性。用詞的模糊性,不是指單純的詞語本身表達(dá)的模糊性,不是我們在上文中所說的“不確定”[2]。它的重點在于是“用”的過程中加重或者是凸顯了語言的模糊,也就是作者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刻意的“模糊”。這種用詞往往是一種修辭手法,為了達(dá)到作者內(nèi)心預(yù)設(shè)的效果而有意為之。這種表達(dá)方式在我國古代的婉約派作品中非常常見,例如“疑是銀河落九天”“輕舟已過萬重山”等都是這種表達(dá)方式。句中的“九”與“萬”從數(shù)量關(guān)系上看本身是確定的,是不模糊的,但是作者具體地用到詩句中的時候,就明顯地出現(xiàn)了夸張,達(dá)到了一定的修辭效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用”詞的模糊性,在當(dāng)代中外的文學(xué)作品中都非常常見。 第二,句意的模糊。語句是組成文學(xué)作品的重要單位,文學(xué)語言的模糊還表現(xiàn)在一個句子有多種不同的理解效果。特別是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這種句意的模糊既是為翻譯轉(zhuǎn)化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同時又是對翻譯者功力的考驗。例如,對“yesterdayishistory,tomorrowisamystery”這句話進(jìn)行翻譯,從字面上看,我們能夠通俗地將這句話翻譯成“昨天是歷史,明天是謎團(tuán)”,從句意上講,這樣翻譯是能夠滿足作品表達(dá)的要求的,但是卻毫無文學(xué)翻譯的美感,過于僵硬和死板。 [3]在這種具有可擴(kuò)充空間的文學(xué)翻譯中,句意的模糊往往是作者為了表達(dá)一種感慨或是情緒。就如同智利著名的詩人聶魯達(dá)認(rèn)為,詩歌本身就不是能夠用語言來解讀的。如果用語句來解讀詩歌,就喪失了詩歌存在的價值與美感。所以對于這種文學(xué)語句的模糊,我們可以適當(dāng)?shù)仂`活處理,可以將例句翻譯成“逝者長已矣,來者猶可追”,更具有文學(xué)表達(dá)的效果。 第三,意境的模糊。相對于前兩個層面,意境的模糊意味著作品本身已經(jīng)到達(dá)了一定的表達(dá)高度,每一個讀者在作品中能夠找到不同的,能夠與自己的心靈發(fā)生碰撞的文學(xué)閃光點,這是一些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品都具備的一個普遍性特征。在中國的文學(xué)作品中,能夠達(dá)到這個效果的在筆者看來首推《紅樓夢》。當(dāng)代作家王朔對中國文學(xué)有一個很客觀的評價就是,《紅樓夢》是中國文學(xué)的標(biāo)桿,在此以后的作品雖然有了老舍的《家》《春》《秋》這樣的系列佳作,但是從文學(xué)價值上看還是不及前者。意境的模糊,在《紅樓夢》中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正是因為這種模糊,所以在這部作品以后中國有了“紅學(xué)”這一個特殊的文學(xué)研究學(xué)派,而且即便是到了今天,這種探索作者當(dāng)年寫作時的境況以及窺探這部作品所表達(dá)的現(xiàn)實背景的渴望,依舊沒有削弱。 這就是文學(xué)作品意境的模糊所創(chuàng)造的魅力與價值。 三、文學(xué)翻譯中的語言模糊問題 在上文我們已經(jīng)分析了語言的模糊性以及文學(xué)語言模糊的層面,這兩個部分都是導(dǎo)致文學(xué)翻譯中存在語言模糊性問題的重要原因,但是并沒有涵蓋文學(xué)翻譯語言模糊的所有問題。具體到文學(xué)翻譯工作中,語言模糊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學(xué)作品源語言的模糊性。文學(xué)翻譯,通常是對一個作品進(jìn)行不同語種的轉(zhuǎn)化,例如將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作品,將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作品等就是屬于此類。在文學(xué)翻譯過程中會出現(xiàn)語言的模糊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原作品中源語言本身存在模糊性。[4] 這種源語言的模糊性,就包括了我們上文所提到的語言本身的模糊屬性以及文學(xué)語言中存在的不同模糊層面。對于這個問題,有一個最為簡短的總結(jié)就是“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在全世界廣為流傳,我們暫不說經(jīng)過翻譯以后的莎翁作品對世界讀者產(chǎn)生何種影響,僅僅局限于原版的莎翁作品,也就是未翻譯的英文作品,不同的讀者對于作品的感受與理解就是不同的。一個文學(xué)作品,如果讀者獲得的感受是千人一面,那么這個作品的內(nèi)涵與外延都是應(yīng)當(dāng)受到質(zhì)疑的,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其內(nèi)涵可能集中在某一個問題上,但是其外延通常極具擴(kuò)散性,每一個讀者都能在作品中體會和領(lǐng)悟到不同的東西。 而能夠讓翻譯者進(jìn)行翻譯的文學(xué)作品,通常就是在源語言的閱讀者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被認(rèn)為是佳作的作品。這就決定了在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中,作品源語言的模糊性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這個模糊性恰恰也是這部作品被公認(rèn)為優(yōu)秀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完全地忽視這種模糊性,刻意地準(zhǔn)確,也就是改變了原作品的內(nèi)容。翻譯者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妥善地處理這種模糊性與翻譯表達(dá)的準(zhǔn)確性之間的關(guān)系。#p#分頁標(biāo)題#e# 第二,源語言與目標(biāo)語言之間文化差異導(dǎo)致的模糊性。文學(xué)翻譯,不可避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文化差異。因為文化與語言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語言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礎(chǔ),語言的差異間接的代表了文化的差異。例如,英語是西方國家普遍使用的官方語言,所以即使這些國家與國家的文化之間存在著差距,但是卻具有西方文化中的共同屬性,這種共同屬性的存在就是因為通用語言的存在。相反,要將中英文作品進(jìn)行翻譯,實際上就是跨越兩種不同文化完成一個優(yōu)秀作品的語言轉(zhuǎn)化,這樣就不得不面臨源語言與目標(biāo)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問題。作品的翻譯,一個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文化的移植,這種移植不是具有侵略性的占有和沖擊,而是一種文化的傳播與交融。巴斯內(nèi)特認(rèn)為,當(dāng)作品的翻譯受到一些文化因素的制約時,往往會出現(xiàn)形式上的譯作。嚴(yán)格來說,這種譯作并不是真正的翻譯,是一種偽翻譯。真正的翻譯,體現(xiàn)出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共譯”,也就是能將三者對于文化的理解與感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翻譯文學(xué)作品。[5] 但是在這個翻譯過程中,文化差異會導(dǎo)致一些語言模糊的問題,并且在對模糊語言進(jìn)行翻譯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文化虧損,這是任何一個高明的譯者都不可避免的問題。這與翻譯者自身的文學(xué)素養(yǎng)和語言功力無關(guān),文化差異的存在必然導(dǎo)致了這種翻譯文化虧損的出現(xiàn)。例如在西方的文學(xué)作品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橄欖枝”這個詞語,當(dāng)然,作為一個名詞在運用中既有實指也有虛指,做實指的名詞理解時,我們可以直接將其翻譯成“橄欖枝”,并不會有什么問題。但是這個詞語在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是被用來作為一種虛指、一個象征,西方人提到“橄欖枝”會不自覺地想到《圣經(jīng)》,想到諾亞方舟,想到和平。但是對于中國文化的接受者來說,則沒有這一層面的理解。所以在文學(xué)作品中對這個內(nèi)容進(jìn)行翻譯的時候,翻譯者就要對這個內(nèi)容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臄U(kuò)充,不能直接地翻譯成橄欖枝,而是翻譯成“和平的橄欖枝”,通過語言的模糊來使文章的含義表達(dá)得更為準(zhǔn)確,削弱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困難。 第三,作品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模糊性。作品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差異,歸根到底還是由于作者思維方式的差異導(dǎo)致的,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既有精確思維模式下形成的文學(xué)作品,也有在模糊思維模式下形成的文學(xué)作品。 作者創(chuàng)作思維的模糊性,會直接地呈現(xiàn)在自己的作品中。這種模糊性在許多藝術(shù)活動中得到推崇與賞識,例如油畫作品中的抽象派、印象派等,都區(qū)別于寫實派的精準(zhǔn),對創(chuàng)作者模糊的藝術(shù)表達(dá)要求更高。體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在現(xiàn)代歐美文學(xué)中盛行的意識流派。這一流派的作品很多,例如雷蒙德·卡佛的Whatwetalkaboutwhenwetalkaboutlove,中文被翻譯成《當(dāng)我們討論愛情的時候在談?wù)撌裁础罚褪且环N與傳統(tǒng)小說風(fēng)格極為迥異的表達(dá)方式。這種創(chuàng)作者思維本身的模糊性,也是文學(xué)翻譯過程導(dǎo)致語言模糊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