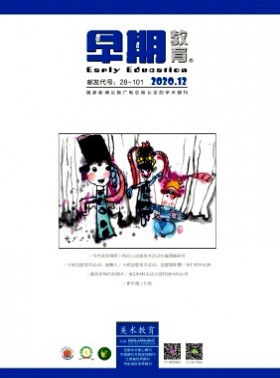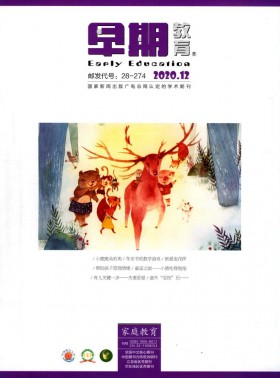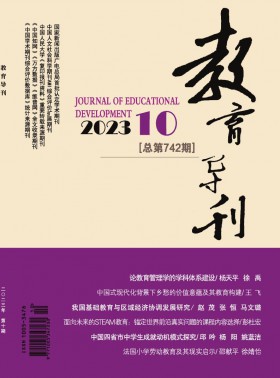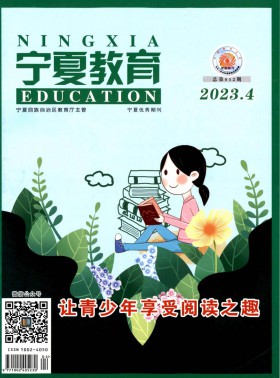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性,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教育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領(lǐng)域肇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教育語言學(EducationalLinguistics)這一術(shù)語是美國語言學教授B.Spolsky在1972年哥本哈根第二屆應(yīng)用語言學年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來的,用以指語言與教育的交叉研究。Spolsky認為教育語言學是一個以教育心理學和教育社會學為模型的術(shù)語,它描述的是語言學這一學術(shù)領(lǐng)域與教育學這一實際學術(shù)職業(yè)的交叉學科。[1]P1教育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有關(guān)教育與語言關(guān)系的所有問題,研究核心是語言在語言學習與教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一門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從語言教育實踐的實際需要出發(fā),利用相關(guān)理論與實踐學科的知識來解決語言教育者與語言規(guī)劃者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因此,教育語言學往往被看作是利用諸多相關(guān)學科如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教育中的語言所進行的跨學科性研究。近年來,它更是被看作是采用生態(tài)的、超學科的研究方法對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中出現(xiàn)的與語言有關(guān)的問題所作的研究。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屬性使這門學科呈現(xiàn)出更多的特點,也為本學科今后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一、超學科性的涵義 處于一個各種智力活動活力發(fā)展、充滿生機的時代,教育語言學獲得了充分發(fā)展并逐漸成熟,尤其是在語言研究領(lǐng)域見證了Fisherman對語言所作的社會學研究和Hymes的交際民族志學研究,在主張消除學科之間的界限,采用整體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具體問題的學術(shù)氛圍及社會背景下,教育語言學發(fā)展成為一門以問題為導向,具有超學科性質(zhì)的學科領(lǐng)域。[2]P2 Spolsky認為教育語言學雖然研究的中心是與語言有關(guān)的問題,但是必須綜合利用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獲得對具體問題的全面理解,也正是在這里第一次播下了教育語言學超學科性的種子。 Halliday在論述廣義的應(yīng)用語言學時也指出,要使用“超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不是“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或是“多學科的(multidisciplinary)”字眼,因為后兩個術(shù)語表明研究者仍然把各學科作為進行智力活動的場所,正確的做法卻是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形式去取代它們,這種新的智力活動形式,是以主題而不是以學科為導向的。拿外語教學來說,外語教學涉及到不止一門學科的內(nèi)容知識:至少要有心理學、社會學和語言學。Halliday主張對外語教學進行超學科的研究,并且指出:研究的目的不是僅僅創(chuàng)造一個具有各學科特征的智力活動的混合體,而是要更進一步,把各個學科有益于解決問題的因素都綜合起來,這樣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就是以主題為基礎(chǔ)的(theme-based)。他解釋說,所要解決的主題不是由內(nèi)容來決定,而是由考察問題的角度來決定。因此,在教育語言學領(lǐng)域所進行的智力活動的中心任務(wù)不是要去在各學科的內(nèi)容知識領(lǐng)域之間架設(shè)橋梁,而是綜合各種具體的研究工具(當然這些研究工具往往是以各學科為基礎(chǔ)的)來共同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 跨學科、多學科與超學科的核心的區(qū)別就是它們的出發(fā)點不同:在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中,出發(fā)點往往是本學科的已知知識,通過在各學科之間架設(shè)橋梁來獲得對某個問題比較清楚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方法是優(yōu)于以往從單一學科的角度去研究問題的方法的。但是,在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性的研究中,研究是從一個特定的、具體的語言與教育的主題開始的,然后利用研究者所占有的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知識資源來分析、解決它。用Halliday的話說就是,智力活動所進行的場所不是在各學科領(lǐng)地內(nèi),而是取而代之,圍繞要解決的具體語言教育問題來展開。因此,超學科研究者就像一個畫家,利用他調(diào)色盤上研究工具的不同光譜勾勒出一幅多維度的生動畫面。 二、教育語言學超學科性所呈現(xiàn)的特點 (一)教育語言學:研究廣度與深度兼?zhèn)? 正如Hornberger所論述的那樣,從根本上說,教育語言學的特點就是它與很多學科關(guān)系活躍,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專注教育中或與教育有關(guān)的以語言為中心的所有問題,這門學科的研究既有分析問題的廣度,又有研究的深度。[3]P17 教育語言學的核心特征就是它是語言學與其它學科的接口。正如Spolsky所講,教育語言學是從具體的問題出發(fā),然后向其它學科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它的學科范圍就是語言學以及相關(guān)語言學科與正規(guī)與非正規(guī)教育的交叉。[4]P2這門學科所探討的問題廣泛,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也很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教育語言學是漫無目的地在“研究的海洋中隨意漂流”,而是它是多元中心的、多方法的和多層次的。也就是說,教育語言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很多,解決它們,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教育語言學領(lǐng)域內(nèi),有很多涉及面廣泛的工作要做,因此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廣泛;同時,解決問題需要有專門知識的個人進行縝密的研究,因而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專業(yè)性和深度。教育語言學者們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途徑進行研究,有的關(guān)注微觀層面,有的關(guān)注宏觀,還有的介于其間,從而獲得對于個人、語言、社會和教育的一個整體的、超學科式的認識。 實際上,Spolsky的教育語言學“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與Halliday的超學科性的“以主題為基礎(chǔ)(theme-based)”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在任一情形下,研究者都不能簡單地把各學科的知識直接應(yīng)用到具體問題中去:在教育語言學研究中,研究者從具體的一個與語言與教育有關(guān)的問題出發(fā),然后綜合利用他所擁有的知識儲備中的研究工具來探討問題的解決。因此,教育語言學的研究工作要在或跨越多個學科門類中去進行,如人類學、區(qū)域研究、教育、外語、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這也正是人類語言學的先行者EdwardSpair所主張的語言學研究應(yīng)當采取的方式,因此,從這層意義上講,教育語言學繼承了廣義語言學的研究傳統(tǒng)。例如,教育語言學世界三大流派之一的澳大利亞教育語言學流派,就牢牢抓住這門學科超學科性的特點,采用了上述研究方法。 #p#分頁標題#e# 總之,在教育語言學的旗幟下,普通語言學與其它社會科學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相結(jié)合,共同解決在正規(guī)和非正規(guī)教育中與語言習得、語言使用、社會語言環(huán)境有關(guān)的所有問題。 (二)教育語言學:研究與實踐的自反性 教育語言學以主題為基礎(chǔ)的學科特征也彰顯了它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研究與實踐的自反性(research-practicereflexivity)。在教育語言學領(lǐng)域所進行的研究不單單是為了獲取一定的知識,而是要去解釋和解決在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實踐中的具體問題,研究的目的是指導實踐,對實踐產(chǎn)生影響;然而這也是個雙行車道,正規(guī)、非正規(guī)教育的實踐活動恰恰為研究提供了源動力,教育語言學研究的課題并不是僅僅出自研究者的大腦,而是來自他們與語言教育實踐的緊密接觸和聯(lián)系。在教育語言學中,研究與實踐相互依靠,互通有無,共同發(fā)展。 從一開始,教育語言學就關(guān)注教育中影響語言使用因素的研究,目標就是構(gòu)建一個有關(guān)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關(guān)系的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的知識體系,以推動從語言習得到語言計劃等各方面的發(fā)展。很顯然,孤立一門學科的努力是無法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因此,教育語言學將繼續(xù)沿著超學科的研究路子走下去,不受制于學科門類的界限,全心全意致力于它所要解決的問題。 三、超學科性對教育語言學學科發(fā)展的指導—生態(tài)研究的美好前景 作為一個具有超學科性質(zhì)的學科領(lǐng)域,教育語言學應(yīng)該把語言學各方面與其它社會科學相結(jié)合,然而遺憾的是,正如Gee所提醒我們的那樣,目前來看,語言學對教育施加的影響遠遠不夠,教師們對語言及語言學知識的了解程度遠遠落后于現(xiàn)今教育中語言研究的發(fā)展水平。 Gee在論述了功能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理論各自在主要教育領(lǐng)域所起到的作用后,舉例說明了一些我們對教育中的語言的確已達到的認識,包括:要關(guān)注語言在幫助孩子獲得一種學術(shù)語言新形式中所起的作用,教師需要理解學生帶到課堂上的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資料,以及了解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在課堂交往中的相互作用。正如他的教育語言學前輩一樣,Gee主張我們要在已知語言學知識應(yīng)用到實踐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人類語言學家DellHymes也支持這一觀點,他之所以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研究院的院長,是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需要改變我們對語言的看法,以及探討我們應(yīng)該如何對待學校中的語言。 世界人口的日益多語化,使世界教育體系承受了更大的壓力;在多語主義、多元文化日益顯示出其社會與經(jīng)濟優(yōu)越性的今天,研究語言與教育的關(guān)系變得異常重要;語言與教育的關(guān)系越復雜,所要進行的研究也就越復雜,超學科的研究也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雖然,教育語言學在建立之初就是沿著這樣的一個路子在走,但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統(tǒng)一、一致的知識體系,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教育語言學家們也都一致認為:教育肩負著“培養(yǎng)語言恰當性”的一份社會責任,但是,如何在大規(guī)模的水平上實現(xiàn)這個目標,現(xiàn)在還缺乏戰(zhàn)略性的對話,教育語言學似乎還缺乏一個清晰的發(fā)展路線。教育語言學要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專注語言與教育所有問題的學科,就應(yīng)該去認真探討個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無論從微觀、從中間、還是從宏觀的層面。如此一來,生態(tài)研究的方法在這個領(lǐng)域?qū)泻芎玫那熬啊? 雖然,生態(tài)研究在社會科學中已不新鮮,但只是近來才在教育語言學領(lǐng)域顯現(xiàn)其重要性。生態(tài)研究的方法已越來越多地應(yīng)用于語言學各方面的研究,從個人層次的語言習得到課堂教學法再到語言政策的制定,比如,Leather和VanDam的EcologyofLanguageAcquisition也是Kluwer教育語言學系列的首部集合了語言習得語境因素研究的作品,另外,Hornberger的“ContinuaofBiliteracy:AnEcologicalFrameworkforEducationalPolicy,Research,andPracticeinMultilingualSettings”一文,強調(diào)了多層次的分析方法在建構(gòu)、實施和評估雙語、多語教育計劃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些成果反映了生態(tài)研究的不同側(cè)面,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對于語言與教育的任何方面,孤立的研究都不會達到有效的結(jié)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tài)研究在超學科的教育語言學研究中將會占據(jù)中心位置。 與早先談到的教育語言學的核心特點相一致,教育語言學領(lǐng)域內(nèi)所進行的生態(tài)研究也是以問題為導向和超學科性的,以主題為中心的整體觀將推動這門學科扎實向前邁進,同時也堅定了它借鑒多學科來全面探討語言在教學與學習中作用的決心。總之,教育語言學在其不長的發(fā)展歷史中,一定會堅持其核心原則,同時又會不斷滿足持續(xù)變化世界中研究與實踐的實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