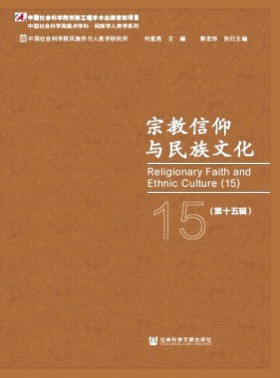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宗教信仰中的語言文學,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壯族歷史上沒有形成統一的宗教信仰。萬物有靈、多神崇拜構成了他們的宗教世界。在這個宗教世界里,六烏圣母便是其中的重要神靈之一。據史料記載:“壯俗每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圣母。”“按圣母不知何指,據邑中武平里諸壯所祀,則為六烏娘,又名六烏婆,廟在六烏山,壯人每遇瘟疫,則異六烏娘巡游村市熱鬧。”“瑤祭盤古,壯祀六烏圣母。”[1]《粵江流域人民史》亦有“壯祀六烏圣母白馬令公等神”[2]之說。雖然這些祭祀形式已經明顯披上了漢族宗教文化的色彩,但仍掩飾不住它與自然崇拜的淵源關系。因為壯族的主要宗教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的源頭是自然崇拜,它“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3]。另外,據史載,漢族宗教對壯族宗教的影響是在唐宋之后。因而,壯族本民族的宗教現象是早期的,而受漢族影響的宗教現象是晚期的,但無論壯族的宗教信仰如何深刻地受到漢族宗教文化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自然崇拜的蛛絲馬跡。據此,可以推斷,壯族的六烏圣母源于自然祟拜,它反映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反映了人們對某一客觀對象的神化,因此,必有其賴于形成的生物原型。揭示這個生物原型,對認識壯族崇拜六烏圣母的成因及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貴港一帶壯族人曾以六烏圣母的女性塑像為據,把她看作劉三姐。這純粹是出于一種美好的愿望和想像,不足為六烏圣母生物原型的憑據。因為在宗教世界中,人的形體與非人的生物體是可以互變的,即人可以變為某一種植物或動物,反過來,某一種植物和動物也可以變為人。這樣,就不可因六烏圣母的外表是女人像,就作出其生物原型是劉三姐的結論。此外,從“顧名思義”的角度看,六烏圣母名稱的含義也難于跟劉三姐之名聯系起來。所以,光從外在的神像去猜測其潛在的生物原型是很難達到準確性的。這樣,若要在這方面言之確鑿,需要從語言文學等多視角去考證。 首先,從名稱的語義上看,六烏圣母所表示的生物原型主要隱藏于“六烏”二字之中(“圣母”二字是不言而喻的通稱,在此不必贅述),但由于“六烏”二字的漢字形體反映不出漢語的任何詞匯意義(查漢語詞典無此詞),所以無法直接從字面上去理解“六烏”的含義,而只能從音譯詞方面去考慮。因為壯族在歷史上沒有文字,故常常借用漢字來記錄自己語言的讀音,形成了許多音譯詞,“六烏”就是其中之一。據載,“六烏”為土人之言[4]。從史載中的“六烏山”、“六烏廟”以及經常舉行“六烏”祭祀活動地區分布的范圍來看它們均在廣西的貴港、橫縣、桂平一帶,這一帶正是壯族先民所聚居的壯語北部方言區。所以,這些地方的土人當為壯族人,其“土人之言”當為壯語。而作為“土人之言”的“六烏”,無疑是壯語中某一特定詞語的音譯詞。至于這個音譯詞與壯語中哪一個特定詞語的讀音相一致,那就得以古代讀音為準進行比較。因為“六烏廟”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經存在。由于人類的自然崇拜源于原始社會時期,所以壯族的“六鳥”崇拜也應始于遠古時代。與此相應,“六鳥”的漢字標音也當早于太平天國以前,它所體現的是漢語的古代讀音而不是現代讀音。語音是發展變化的,漢語語音從古至今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失落韻尾-p、-t、-k等。因此,我們不能以“六烏”的現代讀音去尋找其在壯語中的音譯對象,否則,就會失去準確性。據《漢字古音手冊》[5],“六”的上古音為“來母覺部”,擬音為*lǐuk;“烏”為“影母魚部”,擬音為*a,兩者合在一起讀為*lǐuk*a,即“六鳥”。這個音譯詞的讀音和構詞特點正好與壯語中“六鳥”的讀音lok8a1和構詞特點一致,其中“六”*lǐuk對譯壯語的lok8(鳥),*a對譯壯語的a1。a1是表示鳥鳴的象聲詞,兩個詞相加負載“烏鳥”的意思,整個結構體現了壯語詞“通稱+專稱”的特點(即lok8為通稱,a1為專稱)。而音譯詞“六烏”的結構正好與這種構詞特點吻合(即“六”表示通稱,“烏”表示專稱)。另外,從古人記音用字的習慣上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漢字“六”與壯語詞lok8(鳥)的對譯關系。始于古代的方塊壯字就是用漢字“六”來標記壯語中表示“鳥”意思的詞lok8,例如“六筆”(野鴨)①。壯語地名也常見以“六”表示壯語詞lok8(鳥)的現象,例如“六居”(野雞)、“六教”(八哥)等[7]。此外,流行于壯族民間的道公經書和山歌手抄本也用“六”來記錄壯語詞lok8(鳥)的讀音。可見,漢字“六”在被壯族人借用過程中已經成為壯語lok8(鳥)一詞的固定標音符號,所以“六鳥”中的“六”標志的是壯語詞義“鳥”的意思。而“烏”的古代讀音*a與壯語詞lok8a1中的讀音a1幾乎一模一樣,它們都同是模仿烏鳥叫聲而產生的象聲詞。因此,“鳥”作壯語詞a1的標音符號在情理之中。 從上述的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六烏”二字就是壯語中lok8a1(烏鳥)一詞的音譯載體,也就是說,壯族“六烏圣母”的生物原型就是烏鳥。 壯族有過崇拜烏鳥的宗教歷史,這不僅可以從“六烏”的古音詞義中看出來,還可以從壯族神話傳說和壯族人對烏鳥的態度以及壯族神器的鳥飾等方面得以印證。先從神話傳說中看,壯族先民對烏鳥素來懷褒揚和崇敬情感。例如在壯族民間傳說《巖剛河的來歷》中,烏鳥被壯族先民描繪為指點“迷津”的神靈,它不畏險境,機智勇敢地幫助英雄巖剛殺死惡蜂王,除掉毒蜘蛛,為人民撲滅人間火災。在另一篇壯族民間故事《達加》中,烏鳥的形象也處處閃爍著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勇于犧牲的光輝。每當可憐的達加姑娘遇到巫婆后娘的殘害時,烏鳥就出現在達加姑娘的面前,幫助她逃避迫害,懲治巫婆,直至最后為揭穿惡人達侖的陰謀而遇害身亡。它身亡后,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而是變為水聲,化作竹林,繼續懲治狠毒的達侖。顯而易見,這些作品無不以贊頌的筆調,熱情洋溢地嘔歌烏鳥不畏犧牲,從善治惡的美好品格,塑造了一個個令人崇敬的烏鳥形象。其間傾注著民族的愛憎感情和崇拜心理,從而歷史地反映了壯族先民崇尚鳥鳥的思想傾向。#p#分頁標題#e# 壯族著名的神話故事《姆六甲》更是顯示了壯族先民對烏鳥的頂禮膜拜。這篇神話將宇宙分為上、中、下三界,中界有一朵花,這朵花后來生出了壯族的姆六甲。姆六甲降生后就以大地造出江河湖海,以泥人制作男女眾生,使世間呈現一派生機,因此被視為壯族的始祖母而受到無限崇拜。這一神圣地位使后人對姆六甲的生物原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不少人對此作出了種種猜測,盡管各說不一,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姆六甲的原型屬于鳥類,正如壯族學者梁庭望先生所證:“姆六甲”實為壯語讀音,“六甲”表示一種鳥,即“六甲鳥祖母”[8]。據筆者調查,在來賓縣小平陽鄉、五山鄉以及武鳴縣陸斡鄉一帶的壯語口頭傳說中,“姆六甲”(與記載中“姆六甲”的內容一致)的壯語讀音實為me6lok8ka1。壯語me6是表示女性的量詞,可以單獨用在一些表示雌性動物的名詞之前。 例如:me6pit7me6kai5 母鴨母雞 me6va:i2me6mou1 母牛母豬這樣,“姆六甲”中的“姆”標記me6,“六”是壯語lok8的音譯字(上文已述)。“甲”是壯語ka1的通用音譯字,是個模仿烏鳥叫聲的象聲詞。顯然,壯語me6lok8ka1中的lok8ka1就是“烏鳥”的意思,整個me6lok8ka1就是“烏鳥娘”或“烏鳥婆”的意思。這樣,me6lok8ka1的音譯字“姆六甲”也就負載“烏鳥娘”的意思,其中“姆”表示“母性”之義,“六甲”表示“烏鳥”之義。可見,“六甲”與“六烏”所表達的詞義相同,兩者之所以標音字形不同,是因為壯語“烏鳥”一詞的讀音有方言差異,在武鳴等地讀lok8ka1,故標作“六甲”,在隆安等地讀作lok8a1,故標作“六烏”。不同的方音必然導致不同的標音字形,“六甲”和“六烏”的字形差別就是壯語方音差異的產物。可見,“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也是烏鳥。拉法格說過“神話是保存關于過去回憶的寶庫。”[9]壯族神話《姆六甲》正是以幻想的方式,保存了原始壯族人奉烏鳥為創世始祖母的歷史圖景。 從壯族人對烏鳥的態度上,也可見其尚烏之誠。 據《粵江流域人民史》引《嶺南雜記》載,壯族人“服俱黑色,廣西最多。”聞橫縣一帶的古代壯族人喜著黑服。至今,壯族一些地區如那坡等地的人仍有“黑衣壯”之稱。一個民族的祟尚色往往與其崇拜物的外觀顏色合。因此,壯族人喜著黑衣當與他們所崇拜的烏鳥的黑色外觀有關。相傳烏鳥能反哺,束晰《補亡詩•南咳》“嗽嗽林烏,受哺于子。”蘇轍《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詩:“馬馳未覺西南遠,烏哺何辭日夜飛。”所以,壯族先民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后代受感于烏鳥的反哺精神,以孝養父母,便樹立起烏鳥的鳥神形象,并效仿烏鳥的黑色外形,著起黑服,以示虔誠。①此外,壯族人祟拜祖先,他們認為祖先死后靈魂不滅。烏鳥常徘徊于祖先墓地,必附有祖先之魂,故它們是祖先的化身。壯族民間傳說《達加》中就有達加娘死后化為烏鳥的情節,反映了壯族人的“祖先之魂附于烏鳥”的宗教思想。 壯族人對烏鳥的另一種普遍看法則以為其是報喪之神。因為壯族人發現,只要烏鳥棲于誰家房頂,誰家就有人亡。古壯族人對烏鳥這種神奇的卜兆現象未能作出科學的解釋,于是恐懼和希望交織在一起,繼而將烏鳥神化,對之燒香磕頭,以求消災。 壯族人對烏鳥的崇拜還典型地表現在銅鼓的鳥飾上。我們知道,銅鼓是壯族著名的神器。在壯族的銅鼓中,除了蛙飾之外,鳥飾亦占有重要地位,正所謂“成了鳥的天下”[11]。一些學者認為,鳥是駱越人的圖騰。壯族是駱越人的后裔,故鳥亦是壯族人的圖騰,而在壯族的鳥圖騰崇拜中,烏鳥占有突出的地位。 所以,一些重要的壯族文獻如《壯族文學概論》[12]視之為壯族的圖騰。由于銅鼓的神靈色彩以及鳥飾的圖騰意義,使壯族銅鼓上的烏鳥成為壯族人神化了的圣鳥。這些都為壯族人對烏鳥的崇拜以揭示“六烏圣母”的烏鳥原型提供了依據。 此外,從性屬上也可以看出壯族“六烏圣母”與烏鳥的一致性。據《壯族文學概論》說,烏鳥是一位女神。查壯族巫經亦有“烏鳥小娘”的記載,這些記載與史料所說的“六烏娘”、“六烏婆”、“六烏圣母”的母性特征一致。 綜上所述,“六烏圣母”的生物原型是烏鳥,與“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一致。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 壯族早期的“六烏”神像必然離不開鳥的形體。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出現,專職的巫覡應運而生,他們被視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介,能“通神去鬼”。巫覡的產生又促進了多神崇拜的發展,使神出現人格化的趨向,而神的人格化則進一步導致了神的人形化。在這種情況下,壯族的“六烏”神像也逐漸由動物形體向人的形體轉變,這就造成了壯族各地區“六烏”原型的人像化。正如廣西桂平一帶的壯族雖“每遇瘟疫,則異六烏娘巡游村市熱鬧”,但卻不知其為何物,只知其是一位人身女神。而貴港一帶的壯族,則把“六烏娘”看作劉三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