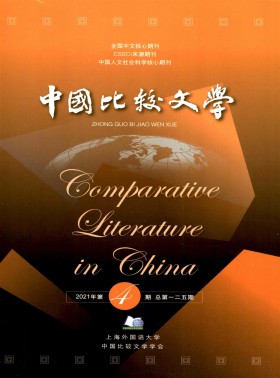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wǎng)用心挑選的比較文學(xué)角度下的英美文學(xué)教育,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優(yōu)美、凝練的語言和意境,再加上精短的篇幅,是詩歌常受讀者特別喜愛的原因,同時(shí)它也是二十世紀(jì)英美新批評(píng)派理論家們采用文本細(xì)讀法進(jìn)行研究時(shí)所喜歡使用的文類形式。英國詩人、批評(píng)家燕卜蓀出版于1930年的《含混的七種類型》一書的基本內(nèi)容就是“對詩歌進(jìn)行分析性的細(xì)讀”,其批評(píng)的要義就在于“批評(píng)要在詩作為詩的結(jié)構(gòu)中處理詩的意蘊(yùn)”。[1]同漢語言一樣,英語的文體風(fēng)格也變化多樣,各種文體豐富的表現(xiàn)力和獨(dú)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文學(xué)作品中更是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對英語專業(yè)的學(xué)生來說,要真正掌握英語,學(xué)會(huì)如何去閱讀、欣賞英美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文之精髓的詩歌,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鑒比較文學(xué)的方法對《英美文學(xué)選讀》[2]中入選的詩人代表威廉•華茲華斯、瓦爾特•惠特曼、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和我國現(xiàn)代詩歌的奠基者郭沫若的詩學(xué)理論和詩歌創(chuàng)作進(jìn)行分析比較,旨在于讓學(xué)生對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和詩之為詩的獨(dú)特魅力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和領(lǐng)悟,而非要對詩的好壞標(biāo)準(zhǔn)作出界定或評(píng)價(jià)。 1言志與緣情 有關(guān)詩歌本質(zhì)和藝術(shù)特征的論爭從來就沒停止過。普通讀者也罷,文學(xué)評(píng)論家也好,還是詩人們自己,對詩之為詩的獨(dú)特體征歷來就有各種各樣的闡釋和比喻。“詩言志”是我國古代文論家對詩歌本質(zhì)特征的一種普遍認(rèn)識(shí)。早在《尚書•舜典》中就提出了“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3]強(qiáng)調(diào)了詩歌的本質(zhì)在于表達(dá)詩人的思想、抱負(fù)、志向。而到了漢代,人們對詩歌“言志”本質(zhì)的認(rèn)同更是趨于明確,在《毛詩序》中指出了“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dòng)于中而形于言”。[4]《毛詩序》中情、志并提,將詩歌言志、達(dá)情的本質(zhì)與功能兩相聯(lián)系。到了西晉,文學(xué)家陸機(jī)在其著名的《文賦》中將文體分為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類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在于“緣情”、“綺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華麗的語言表達(dá)出詩人內(nèi)心強(qiáng)烈的情感,明確提出了詩歌表述詩人情感的本質(zhì)以及語言細(xì)膩、華美的特征。 2詩是詩人強(qiáng)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國前期浪漫派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在其為與另一個(gè)“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謠集》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強(qiáng)調(diào),一切好的詩歌應(yīng)該是“強(qiáng)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該“序言”被認(rèn)為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宣言。華茲華斯認(rèn)為,詩歌應(yīng)該描寫詩人于“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對一個(gè)詩人來說,最主要的是他“應(yīng)該選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點(diǎn)想象的色彩”。[6]事實(shí)上,華茲華斯那些偉大的詩歌正是自己生活經(jīng)歷的真實(shí)寫照。出生在自然景色優(yōu)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區(qū)的華茲華斯,不僅年輕時(shí)喜歡自由自在地在這片土地上打獵、劃船、上樹掏鳥窩、采堅(jiān)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興趣相投的朋友、兒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區(qū)美麗的自然風(fēng)光中。湖區(qū)自然風(fēng)物的嫵媚和豐富不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為其日后創(chuàng)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選入《美國文學(xué)選讀》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獨(dú)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稱作是華茲華斯抒情詩的代表作,據(jù)說就是根據(jù)詩人與妹妹一起外出在湖邊游玩時(shí)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這一經(jīng)歷寫成的,詩歌形象而生動(dòng)地體現(xiàn)了詩人在“序言”中關(guān)于詩歌應(yīng)該描寫“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的詩學(xué)理念。在詩的最后一節(jié),詩人記憶中那一望無際、迎風(fēng)舞蹈的金黃色水仙花給他孤寂的心靈帶來歡樂:“水仙花在我的心靈閃現(xiàn),使我在孤獨(dú)中感到快樂。”詩人對自然與人類之間息息相關(guān)的聯(lián)系給予了揭示,并對人與自然間和諧相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給予了充分強(qiáng)調(diào)。而這,正是此詩所賦予讀者的積極的社會(huì)意義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3詩是對那種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瓦爾特•惠特曼的詩歌風(fēng)格是許多學(xué)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對世界各國詩人的影響也是各國研究者們所樂此不疲的研究對象。美國詩人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家蘭德爾•賈雷爾在《論惠特曼的詩》一文中就對惠特曼的獨(dú)特與不可模仿和復(fù)制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rèn)為惠特曼是一個(gè)“有膽量的”,一個(gè)“最不顧后果的、最令人費(fèi)解的、也最不可能存在的”詩人。[7]131因此,在華裔美籍學(xué)者方志彤先生看來,這樣詩人,是郭沫若這樣性格的人和其創(chuàng)作的詩歌所不可能模仿得了的。“有一個(gè)像惠特曼這樣的奇跡已經(jīng)足夠了。如果再有一個(gè)惠特曼出現(xiàn),那一定得等到世界末日的到來。”如果有人硬要去對惠特曼的詩進(jìn)行生搬硬套的模仿,那結(jié)果只能是像方志彤對郭沫若詩歌的評(píng)價(jià)那樣,“錯(cuò)得不能再錯(cuò)了”。[8]186對我國現(xiàn)代詩歌的奠基者郭沫若受華茲華斯和惠特曼浪漫詩風(fēng)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新詩的研究,也是國內(nèi)外郭沫若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話題。 1955年,方志彤在他那篇《從意象主義到惠特曼主義的近代中國詩:探索不成功的詩作》中就認(rèn)為郭沫若這個(gè)真正多才多藝的人是惠特曼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道者。只要讀者將郭沫若的《我是一個(gè)偶像崇拜者》中連續(xù)7行的“我崇拜”(Iworship)與惠特曼的《別離的歌:再見》中那長達(dá)15行的“我宣告”(Iannounce)相對照,便立刻可以看出郭沫若的這首詩與惠特曼的詩行表面上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會(huì)讓人情不自禁地將郭沫若的詩當(dāng)成是對惠特曼詩歌的又一仿效之作。[8]186在方志彤看來,對郭沫若和惠特曼來說,詩歌應(yīng)該是對那種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而這兩種情緒恰好是傳統(tǒng)觀念的抱持者所要竭力壓制的東西。郭沫若的詩,既不是華茲華斯詩學(xué)所倡導(dǎo)的那種“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也不是柯勒律治詩學(xué)所認(rèn)為的“好詩是最佳詞語的最佳排列。”[8]186①對詩人郭沫若來說,他自己則多次在論詩的文章諸如《論詩三札》、《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文學(xué)的本質(zhì)》、《關(guān)于詩的問題》、《論節(jié)奏》、《我的作詩的經(jīng)過》中詳細(xì)闡釋了詩歌的本質(zhì)和詩之為詩的魅力特征,與惠特曼認(rèn)為詩是對那種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只要我們的詩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xiàn),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dòng),靈底叫喊,那便是真詩、好詩。”[9]12“詩的本質(zhì)專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也不失其詩。”[9]43而郭沫若現(xiàn)代新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詩集,里面收錄的那些創(chuàng)作于1919年夏至1920年上半年的激情澎湃的新詩,正是郭沫若心中詩意詩境的形象再現(xiàn)。#p#分頁標(biāo)題#e# 4詩就是詩 在英美眾多杰出的詩人中,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無論是對普通讀者,還是對英語專業(yè)的同學(xué)來說都是其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類。但選入北京大學(xué)陶潔教授主編的《美國文學(xué)選讀》中的麥克利什的詩歌《詩藝》,卻以詩歌的形式簡明扼要地論述了詩歌本身的藝術(shù)特征和本質(zhì)。《詩藝》一詩中詩人獨(dú)特而形象貼切的比喻,簡明扼要地向讀者傳達(dá)了詩歌的獨(dú)特魅力,在瞬間就牢牢抓住了讀者的神經(jīng),并讓讀者在不經(jīng)意間明白地領(lǐng)悟了詩歌的真諦與美好。詩歌原標(biāo)題為拉丁文ArsPoetica,譯成英語可為ArtsofPoetry,與公元前一世紀(jì)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的文論同名。賀拉斯的《詩藝》之后,有不少詩人和評(píng)論家都就此題目發(fā)表過自己對于詩歌的見解。受二十世紀(jì)初以埃茲拉•龐德(EzraPound)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詩歌理論的影響,麥克利什在這首《詩藝》中強(qiáng)調(diào)詩人不應(yīng)該在自己的作品中抽象地去談?wù)摾碚摶蛘呖斩吹厥惆l(fā)自己的情感,而是應(yīng)該著意地去塑造一些栩栩如生、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委婉間接地傳達(dá)詩歌所蘊(yùn)含的信息。這個(gè)觀點(diǎn)正契合了龐德在1914年論述意象派詩歌時(shí)對“意象”的強(qiáng)調(diào):“意象主義的要旨,在于不把意象當(dāng)作裝飾品,意象本身就是語言”。[10] 在詩歌的第一部分,詩人用了四個(gè)鮮明的、人人都熟悉的意象來闡釋詩歌的本質(zhì)。在他看來,詩歌應(yīng)該是靜靜的、可以觸摸的,就好比一個(gè)球狀的水果。詩歌應(yīng)該是無言的,就如同人們用拇指去觸摸舊的像章,那種感覺是只可意會(huì)而無法言傳的。詩歌就好像窗臺(tái)上的石欄,盡管常常被袖口摩擦,人們對它再熟悉不過,但卻不經(jīng)意間長出了青苔,帶給人們一種新鮮之感。詩歌,還應(yīng)該像是從空中飛過的鳥群,是寂靜無聲的。 四個(gè)比喻中,詩人都強(qiáng)調(diào)了詩歌本身“無言的”特征,強(qiáng)調(diào)了其應(yīng)該具有的是“可觸”、“可感”的鮮明的意象,因?yàn)檫@些才是一首好的詩歌吸引和啟迪讀者的根本之所在。在第二部分,詩人運(yùn)用的還是人們都熟知的意象,即皎潔的夜晚“爬上樹梢的月亮”,來傳達(dá)閱讀詩歌后詩歌帶給讀者的影響,是不知不覺的、難以覺察的、潛移默化的,就好比爬樹梢的月亮,人們定睛看時(shí)它似乎總是紋絲不動(dòng)的,然而它卻又在樹梢間不停地、悄悄地攀升。在詩歌的第三部分,詩人用了兩個(gè)形象的比喻闡明,詩歌藝術(shù)的真實(shí)性跟它所描繪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間是有差距的,它不應(yīng)該等同于現(xiàn)實(shí),而是應(yīng)該跟現(xiàn)實(shí)保持一定的距離,比如詩人可以用一座斑駁空洞的門廊和一枝紅色的楓葉來表現(xiàn)一段滄桑的歷史,或者用隨風(fēng)搖曳的青草或碧波上的旭日或皎月來象征愛情。這個(gè)觀點(diǎn)正如華茲華斯所謂的在描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基礎(chǔ)上,再“加上一點(diǎn)想象的色彩”,要讓讀者在欣賞的過程中去領(lǐng)悟它所蘊(yùn)含的真理,而不必照實(shí)再現(xiàn)。詩歌的最后詩人點(diǎn)明了詩歌的主題,即詩人心中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詩就是詩。它并不被指定意義。”[11]204②詩歌是無言的,它的意義是被讀者主觀賦予的。詩就是詩,當(dāng)如本是。 5結(jié)束語 不僅對詩歌本質(zhì)與藝術(shù)特征有這樣眾說紛紜的見解,對任何文學(xué)文本的解讀也如是。讀者,尤其是處在不同時(shí)代或異質(zhì)文化語境中的讀者,都會(huì)因其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huì)歷史背景、審美情趣或意識(shí)形態(tài)等原因而對同一事物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或?qū)υ谋拘畔⑦M(jìn)行有意無意的選擇、滲透甚至創(chuàng)新,從而形成自己的獨(dú)特理解。但我們應(yīng)該看到,正是由于對同一事物或某文本積極的或消極的、有意的或無意的不斷解讀,才使文本的意義不斷豐富,從而更加具有不衰的持久生命力。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老師可在英美文學(xué)的教學(xué)過程中,立意將英美文學(xué)作品的閱讀與鑒賞作為一門素質(zhì)培養(yǎng)課,鼓勵(lì)并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尋找、發(fā)現(xiàn)與闡釋過程中來,逐步培養(yǎng)學(xué)生敏銳的感受能力,掌握嚴(yán)謹(jǐn)?shù)姆治龇椒ê蜏?zhǔn)確的表達(dá)方式。通過老師逐步的引導(dǎo),從而讓學(xué)生把豐富的感性經(jīng)驗(yàn)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認(rèn)識(shí),準(zhǔn)確理解文本的意義,并嘗試運(yùn)用正確的方法將自己在文學(xué)作品鑒賞過程中所獲得的認(rèn)知用英語表達(dá)出來,以深化對文學(xué)作品的理解,同時(shí)又可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文學(xué)鑒賞力和英語寫作與表達(d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