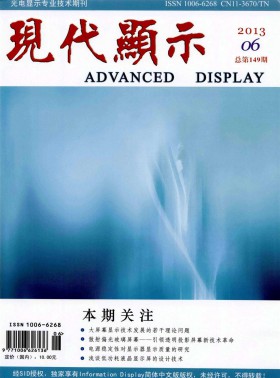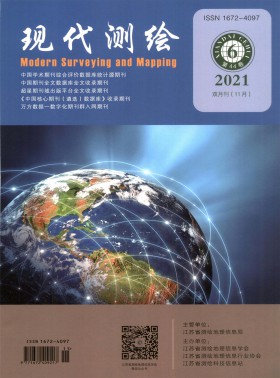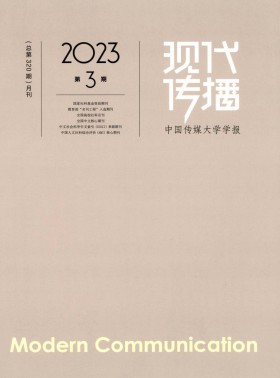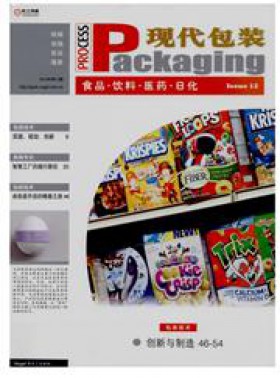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生存理念的倫理學詮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葉繼奮 單位: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倫理學既是一門規范科學,又是一門價值科學,它研究關于一切特殊的、具體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種共同的、抽象的、普遍的道德,探索優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訂過程以及實現途徑。倫理學作為價值科學,同時意味著“在關于道德價值判斷是真理的條件下,所制訂的道德規范才能夠與道德價值相符,從而才能夠是優良的道德規范”。道德價值的推導前提是考察和判斷道德行為事實是否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由人類社會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所決定的。由此可見,“倫理學是尋找道德價值真理的科學,是關于道德價值的科學。”①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斷完善成熟的倫理科學,其真理性日益增強,成為人類生活行為規范和價值判斷的標準。魯迅在日本學醫時,修習過倫理學科,且成績在優等,這對于他以后的思想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魯迅在1925年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目標,集中體現著他關于中國人的現代生存觀,滲透著現代倫理科學的價值理念。
一、公正與人道:合理生存的倫理基礎
實現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地生存和發展,是由人類自身利益所決定的,它代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藝術家思考的重大命題。魯迅主張“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合理”是它的邏輯前提,意味著人的合理的生存與發展只有在公正、人道的社會里才能實現。“公正”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則。“公正的根本問題是權利與義務的交換或分配:權利與義務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則。”其中,“比例平等原則”是就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而言的;“完全平等原則”即“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應該完全平等”。由于“每個人一生下來便都同樣是締結、創建社會的一個股東”,這就意味著,不論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個人才能、貢獻大小存在怎樣的差異,他都有權利得到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的基本權利,這也就是所謂“天賦人權”。“完全平等原則”和“比例平等原則”構成了現代社會公正的根本原則,彰顯其本質與核心的關鍵詞是“平等”。由此可以推論,“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②由于社會公正要通過一系列社會管理活動來實現,因此,社會公正并非個人行為而是社會行為。又由于這一系列管理活動是通過社會統治者的管理行為來體現的,因此,要實現社會公正的最根本問題,即是約束社會統治者的道德,使其做到權利與義務相等,這其中最根本的是做到各種社會行為規范的實現。“因此,社會公正,歸根到底,乃是社會行為規范的公正,亦即所謂制度公正。”由于“制度”亦即一定的法和道德的體系,“這樣,所謂制度公正,說到底,也就是法律的公正與道德的公正”。③以此倫理學原理為邏輯前提作逆向推理即可得出結論:當一個社會是人治的而不是法治的社會時,它對社會統治者就失去了起碼的道德約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權利和義務分配不平等的基本事實。輕則體現在“比例平等原則”的失衡,重則連“完全平等原則”都無法保證,從而出現人的權利被剝奪,人的尊嚴被踐踏,人的價值被輕視的嚴重后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歷史是滋生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社會的文化根源,魯迅以及“五四”啟蒙先驅者所奮力摧毀的正是這種專制統治下形成的文化傳統。
在魯迅寫下的許多相關雜文中,《燈下漫筆》是其中最深刻有力的一篇,它對中國封建宗法制社會歷史作了整體的反省與抨擊,對中國人生存不合理事實進行了概述與剖析。“將人不當人”,人是“非人”;“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歷史循環。歷史的惡性輪回以及歷史主體地位喪失的基本事實,是中華民族無法進入人類現代文明軌道的根本原因。歷史主體地位的喪失,意味著基本人權被剝奪,這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人淪為奴的基本事實。從倫理學角度而言,所謂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的、起碼的、最低的權利”,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等三個方面。政治基本權利表現為一個人能否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作為一個傳統而古老的民族,在連現代民主制度的萌芽都未曾出現的歷史條件下,個體的公民權利根本無從談起的,更為悲慘的事實則是人淪為“牛馬”和“奴隸”,究其深層原因是封建專制等級制度。在中國,貴者、大者、上者“吃”賤者、小者、下者,是人權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此外,兵荒馬亂的戰時,個體生命被任意殺戮,連基本生存權都不能保證。在暴力裹挾之下,“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所謂“亂離人,不及太平犬”。在經受了“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的太平年代,社會秩序建立起來,厘定的仍然不過是奴隸規則。磕頭頌圣,踐踏了人的尊嚴;服役納糧,橫征暴斂,是特定時代社會分配不公的表現形式。如果一個社會不為個體發展、生存提供基本條件,反而一味加以壓迫,這樣就根本顛倒了社會與人的關系。因為在人道主義看來,人本身就是目的。
“人本身之所以是最高價值,則是因為人本身或每個人是社會的目的;而社會則不過是為人本身或每個人服務的手段而已。”④與之相對照,中國封建社會的非人道本質可見一斑。由中國“家天下”宗法制社會性質決定,皇帝“圣旨”即是法律,在這背后隱藏的是權利與義務極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把人當人看”,作為衡量一切行為是否人道的基本總則,意味著“視人本身為最高價值而把任何人都首先當做人來善待”,與此相反,“無視人本身為最高價值而殘忍待人”,是“把人不當做人看”的非人道行為。⑤即從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事實來看,中國傳統社會的非人道本質已暴露無遺。當然,從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史角度來加以觀照,孔子、孟子、荀子都曾經提出過較明確的人權平等觀點。但“儒家講人權平等,主要是就人的道德價值而言,而不是政治上的平等”。“其出發點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所以,‘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個體必須無條件服從社會等級秩序,就成為各種道德規范的核心。”由此形成道德事實的不平等,其虛偽面目也昭然若揭。經濟基本權利表現為吃飽穿暖,即以保證人得以生存的最低的起碼的溫飽條件。魯迅在“生存”與“發展”這兩者中間,特別增加了“溫飽”一項。其獨到的考慮在于,除了當時中國餓殍遍野的苦難現實之外,還包含著他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審視以及由此產生的改革思路。中國傳統哲學對人的片面理解,其中之一即體現在“重精神生活而輕物質生活”,甚至達到了一個極其苛刻殘忍的程度。#p#分頁標題#e#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為了取信于民,以達到社會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惜將民眾的性命置之度外,統治者的殘酷性可見一斑,它與以人為本的現代倫理觀格格不入。與之不同的是,魯迅始終將國計民生問題置于首位,強調保存生命之于人生的重要性,強調經濟權之于目下社會的緊迫性。“溫飽”作為最基本的生存權,與生命的關聯最為直接,顯然,魯迅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從個體生命存活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的。在《燈下漫筆》中,魯迅用簡約的筆墨描繪了一幅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悲慘景象,揭示了社會分配不公的基本事實。民眾除了遵循老例服役納糧之外,還要遭受意外災殃。社會分配不公的實質是權利與義務的不相等,“即一個人所享有的權利與負有的義務不相等”。這“不但是一種社會不公正,而且是根本的不公正,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本原則”⑥。在中國,宗法制度下的“家天下”治理模式,從根本上缺少一套約束社會統治者的道德規范。魯迅在揭露中國人的溫飽基本權利喪失的社會現實的同時,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社會統治者的不道德及缺少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本身。言論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思想權利。這是每個人作為締結社會的一股東應當享受的精神自由的權利。人道主義承認人本身是最高的價值和尊嚴,并將人的價值置于首位,努力恢復人的本質,把人當作人而不是當作非人,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承認人的主體精神價值,離開了主體的精神世界就無從談人的創造。否認了人的主體精神自由,人就被當作工具、牛馬,甚至牛馬不如。在封建專制社會里,對人的根本蔑視體現在限制人的精神自由,壓迫人,奴役人,使人淪為奴隸。魯迅深刻體驗到封建專制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傳統對人的個性和精神的壓抑與摧殘,強調“尊個性而張精神”,并將之貫穿其文學創作和文明批評活動始終。魯迅在早期吸收了西方“新神思宗”的合理因素,寫下《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鮮明地表現了個性獨立、精神自由的現代人權主張。1930年2月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則是對國民黨專制統治下,“查禁書報,思想不能自由。檢查新聞,言語不能自由。封閉學校,教育讀書不能自由。一切群眾組織,未經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會結社不能自由”現實的強烈抗議。旨在通過自由運動大同盟組織,將“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為爭自由而共同奮斗。無獨有偶,馬克思早年也曾對普魯士書報檢查令作過辯論:“我們大家都服從檢查制度,就像專制政體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樣,這當然不是從承認我們每個人的價值的意義上來說,而是從我們大家都無價值的意義上來說”⑦。顯然,取消了人的精神自由,也就意味著不承認并取消了人的價值意義。由此可見,在將人的精神自由置于人的價值的重要地位的觀點上,馬克思、魯迅以及一切偉人的思想都是相通的。
二、宗法倫理觀念:人淪為奴的文化淵藪
致力于適合中國人合理生存的新倫理、新道德的創立與實踐,在另一維度上則表現為對民族舊倫理、舊道德的針砭與否定。“五四”啟蒙者“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主要是基于政治改革與人的解放兩個方面考慮。從政治改革角度而言,由于儒學作為一種家庭主義的意識形態,家庭的概念就不單純表現為家庭與個人的關系,而擴大延伸到家庭與社會的范疇。在儒學家庭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家庭價值和父權制是儒學所想象的道德世界的基本成分”。家庭被“看作是人際關系的中心和原型”。“儒學不僅把人視作‘家庭動物’,而且進一步把家庭關系延伸到社會關系,把家庭價值放大為社會道德”,“把人的理性和政治的規定同家庭關系及家庭主義的社會相聯系。或者說會以家庭主義的角度解釋人的理性和政治的規定。”⑧因此,陳獨秀提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⑨。“解放婦孺”成為“五四”新文化啟蒙的主要任務。
魯迅對民族舊倫理道德的抨擊,主要矛頭指向以“節烈”為標志的兩性觀和以“孝道”為標志的父子觀。這既是以“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為內容的“三綱”指向普通民眾的倫理規定,又是儒學家庭主義意識形態中“君為臣綱”的基礎所在,它具有鮮明的東方色彩和民族特征。與那些“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眾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的含糊其詞的辯護不同,與那些將“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奉為“國粹所在,妙不可言”的昏庸之說截然相反,魯迅始終清醒地從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宗旨出發,將“國粹”置于現代倫理觀念之下加以批判。一種道德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取決于它之于人本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這是有其深厚的理論依據的。元倫理學的研究表明:“所謂道德價值、道德善,行為之應該如何,不過是行為之事實如何對于社會制定道德的目的(保障社會存在、增進每個人利益)的相符抑或相違背之效用,因而是通過道德目的,從行為事實如何中推導出來的;符合道德目的的行為之事實,就是行為之應該;違背道德目的的行為之事實,就是行為之不應該。”在道德的諸多內容中,核心是道德目的,它是“衡量倫理行為事實如何的道德價值的終極標準,只有借助它,才能從倫理行為事實如何推導出倫理行為應該如何的優良的道德規范”⑩。由此可見,“道德目的”是判斷道德價值的依據。即通過道德行為事實如何之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可以得出道德價值之正負;它也是判斷道德行為優劣之依據。
即符合道德目的行為,就是應該道德行為,反之不然;“由于每個人的行為是社會道德所規范的對象”,由此可以說,每個人的道德“行為事實”其本質上是道德規范的感性顯現。從行為事實中可以判斷一定社會道德規范的優劣程度。最后,作為一種終極標準,它還能幫助人們由此推導出優良的道德規范。將此還原到規范倫理學的范疇中,“人”的重要性則被鮮明地凸顯出來。人類為什么需要制定道德?歸根結底是為了保障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增進每個人的利益。以此出發來看行為事實如何與道德目的之關系,即得出結論:利人行為符合道德目的,損人行為違背道德目的。道德規范應該利人而不應該損人。利人的道德規范具有“道德價值”,損人則與之相反。由于道德價值是由道德行為事實如何之于道德目的的關系推導出來的。因而,它與道德目的、道德行為一樣,具有“他律本性”,這一性質無疑增強了它判斷道德規范優劣的客觀力量。與人類的普遍道德相比,處于不同地域空間的民族,往往會制定或奉行與本民族文化相關的道德。“但是,這些道德規范的差異,只能說明道德具有多樣性,特殊性,卻不能否認道德具有普遍性、一致性。”???普遍道德由于體現著人類的整體要求,因此它適用于一切社會,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特殊道德制定的根據是各自不同的民族歷史文化條件,因此,它只對一部分民族與人種有效用。這兩者是“根本”與“非根本”,“產生”與“非產生”,“決定”與“非決定”的關系。“普遍道德”體現著人類道德的終極標準,指向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終極目的。因而,它同時也是一種“絕對道德”。“特殊道德”可以在表現形式上呈現不同,但卻不可違背普遍道德所代表的終極目的。如果違背,就是一種惡劣道德,就只有“負道德價值”,而沒有“正道德價值”。???從現代倫理學這一規定性和真理性出發,魯迅對本民族的特殊道德———“國粹”進行了嚴格的概念界定和價值判斷。“什么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從歷史和現狀來看,“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他對“國粹”判斷與取舍的標準是:“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在此認識基礎上,他又將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置于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全局中加以觀照:“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p#分頁標題#e#
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所謂“國粹”,包括“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拖大辮,吸鴉片,……至于纏足”,“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如此以殘酷為樂、丑惡為美的野蠻的“國粹”,顯然與人類的存在與發展總的道德目的相違背。因此,魯迅以現代道德的價值標準為依據,就已經預見到,作為一種特殊道德———“國粹”必然導致民族的衰亡。“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包含其中深重的憂患令人潸然慨然。在對“國粹”可能導致民族生存與發展阻滯甚至滅亡的大憂患大恐懼中,魯迅對之抨擊最力的是所謂“節烈”和“孝道”。不僅因為這兩者是儒家“三綱”中之“二綱”,家庭的關系作為中心和原點制約并延伸到社會的人際關系,而且更多地體現著魯迅對于被碾壓在綱常輪子下的婦孺之于民族人種的繁衍和健康生長發展關系的考慮。《我之節烈觀》是一篇聲討摧殘女性生命,提倡“節烈”陋俗的舊倫理道德的檄文。歸根結底,人類的道德源于社會需要和個人需要兩大方面。從社會道德需要看,主要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存在發展;從個人道德需要看,它是“完善自我品德之心”的途徑和手段。???社會之于人的影響,以及人之于社會的締造構成的關系,這兩者在事實上是無法截然分開的。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正是從社會與人的關系、從改變社會風俗與人的生命發展的視角去剖析“節烈”觀念的。在對事實做了具體客觀的分析后,全然否定了節烈之于救世的虛偽論調,并對無辜受害的女子深表同情。寫于1925年的《堅壁清野主義》和1933年4月的《關于女人》等文,是對“正人君子”將社會風氣不良嫁禍于婦女觀點的駁斥。魯迅還從“節烈”之于女性個人生命的角度,考察了此等畸形道德對人的精神、身體、物質生活諸方面帶來的傷痛。
婚姻、愛情和性三者能否和諧統一?這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問題,也是人類所追求的的最高境界。在現代觀念中,并沒有簡單排斥貞操一說以示與傳統的區別,貞操是愛情專一的體現。宗教學家羅贊諾夫在批判了基督教保護婚禮的形式和儀式的“唯名論”之后,指出:有名無實的婚姻是對個性生命的殘害,它完全喪失了任何有實際意義的現實內容。因此,在他看來,“向現實的回歸具有解放的意義”。但這種現實內容的解放完全不是“宣布肉體的權利”。“對待性的態度上的禁欲主義在基督教里具有更高的意義,禁欲生活甚至可能比至今所擁有規模更大些。但這個禁欲生活是個性的事情,是自由精神的事情,是精神性的增長,而不是社會強迫的事情。應該同時外在地和社會地解放人的個性,內在地和精神地使個性服從自由的禁欲生活,并揭示愛情的意義。使人在精神上擺脫貶低人的尊嚴的性淫欲的奴役使無意識的性的迷戀升華,是倫理學的基本要求。”???在羅贊諾夫的表述中不難看到,有名無實的婚姻是一種摧殘人性的性淫欲的奴役,對之采取“禁欲”態度,則是保持個性自由、生命尊嚴的有效手段。但它是出于自覺自愿的個人選擇,而不是外在強加的道德壓制。在某種程度上,它表現出人性的解放和精神的升華。與此同時,他也不否認這種方法可能帶來的消極性。在他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反對性淫欲的最強有力的手段,這個性淫欲是人的奴役與墮落的根源。通過愛情而達到貞潔就是獲得完整性,克服性的罪惡,克服分裂與分化”???。
由此可見,現代觀包含了人對的嚴肅性和專一性,并表現了人持之不懈地努力追求達致與人的意志自由的和諧。與此相反,“節烈”在中國則是一種由殉葬制度發展而來的極其野蠻非人道的惡俗,是儒學父權制文化統治下的一種性別等級歧視。它的悖論在于:由多妻主義特權的男子來表彰節烈的女子;由享受可以不受道德約束“放心誘惑”女子特權的男子,來評判女子的貞淫與否。在關系中,最能體現出人類在從獸類向人類進化過程中所達到的文明程度。魯迅在揭露這種丑陋的男性文化所呈現的獸性特征時是鋒芒所向、毫不留情的。在他看來,所謂“男人的進化”表現在三點:比獸性進步之一是強奸;之二是嫖妓;之三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由于性是男女雙方的事,因此,作為一種文化特權,父權文化強迫女性從一而終恪守貞潔,其實質是男女之間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對于這種陋習給人帶來的影響,魯迅分別從兩性角度加以考察。對于女性而言,“節烈”有情欲和實際生活的“苦”;在男性,除了被道德盲區所放縱的性暴力之外,是一種陰弱流氓式的性變態。以禁欲主義為特征的“節烈”道德規范,及其由此帶來的不管男女兩性在靈肉異質變態方面的惡果,都在證實這樣一個結論:道德行為事實與道德目的相違背。雖然道德規范作為道德的一種表現形式是由人為意志所決定的。但“道德規范的優劣性及其衡量標準便完全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不論人們的意志和愿望如何,只有與道德價值相符因而可普遍化的道德,才是優良的、正確的;而與道德價值不符因而不可普遍化的道德,必定是惡劣的、錯誤的”???。從倫理學的這一原理出發,魯迅認為:“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事實證明“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它是一種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不可能帶來幸福的不合理、不正常的畸形道德。
在現代倫理思想觀照下,傳統文化中的“節烈”和“孝道”這類舊道德,“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其根源在于中國家庭倫理道德關系的不平等。對父母敬孝,以自己的能力盡可能侍奉父母,物質贍養,精神尊親,這都是人倫之常情。但由于“在廣義的孝中,孝已經超越了家庭關系而被社會化和政治化了,孝意味著對國家和社會的忠誠”???。所謂“忠誠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事一也。”(《禮記•祭統》)因此,它破壞了父慈子孝的相互平等關系,特別強調子女對父母無條件的尊敬和服從。“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朱子語類》卷九十七)在中國傳統倫理中,“以為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這樣就造成了權利義務上的不平等,造成了“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的精神病態。“馴良”是所謂中國版本“好孩子”奴性的代名詞。這從兒童個體來說,是健康活潑天性的泯滅;對由個體組成的民族種群而言,則意味著更大的惡果———在人類競爭舞臺上處于劣勢。因此,魯迅特別關注中國“孝”德對人個體身心發展造成的損害。“五四”文化啟蒙運動中,魯迅對“孝”德進行過深刻反思和強烈詛咒。他保存著少年時期的陰郁記憶,待到自己成了父親之后,又在家庭教育中實驗,使后輩生長得“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他甚至從中國照相師和畫家的審美趣味上看到了舊文化的遺留,看到了中國兒童由家庭文化壓抑下產生的衰憊氣象,并由此發生發出對國民素質的隱患的擔憂:“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魯迅所言“統統送給洋人”的東西,就是充滿血性的善美剛健之氣質。魯迅正是在歷史的反思中深切體會到民族屢戰屢敗帶來的精神創傷。所以,魯迅從生物學的角度闡述,子女是夫妻愛欲的自然結晶,談不上恩典。主張以自然的天性“愛”代替“恩”。魯迅所說的“愛”,也即是現代倫理學上的“報恩心”。在現代倫理學的闡述中,父母對子女的無私之愛,是子女產生回報父母之恩的基礎。雙方都建立在無私給予,不思索取,心懷感激的基礎之上,因而,這種恩愛之心是真誠而無私利人的。#p#分頁標題#e#
在現代倫理學看來,“道德規范雖然都是人制定、約定的;但是,只有那些惡劣的道德規范才可以隨意制定。反之,優良的道德規范決非可以隨意制定,而只能通過社會制定道德的目的,亦即道德終極標準,以行為事實如何的客觀本性中推導、制定出來:所制定的行為應該如何的道德規范之優劣。直接說來,取決于對行為應該如何的道德價值判斷之真假;根本說來,則一方面取決于對行為事實如何的客觀規律的認識之真假,另一方面取決于對道德目的的認識之真假。”???這一元倫理學上的“是與應該”關系之真諦,既給出了“休謨難題”之答案,又給現代人提供了優良道德的推導和制定的方法。即將道德目的建立在人類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的基點上,以此衡量人類的道德行為事實,并從道德行為事實對于道德目的效用的關系上,判斷道德存在的價值有否。在取消了違反道德目的的惡劣道德之后,進一步尋求并構建有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道德規范。因此,魯迅認為,雖然“節烈”、“孝道”之類舊道德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還有哀悼的價值”。也即從這一歷史遺留中,使今天的我們從中吸取以生命為代價的教訓,更加理性地認識道德之于人的價值和意義,重新構建符合人性自然要求,符合社會存在發展規律的新倫理新道德,從而在“除去虛偽的臉譜”,“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強暴”,“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的基礎上,實現“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的道德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