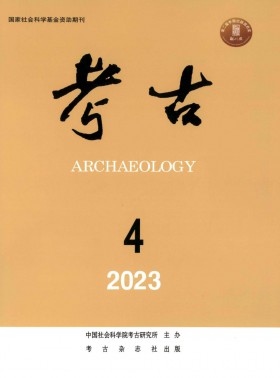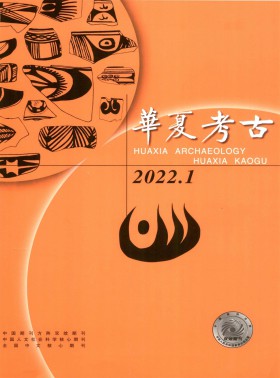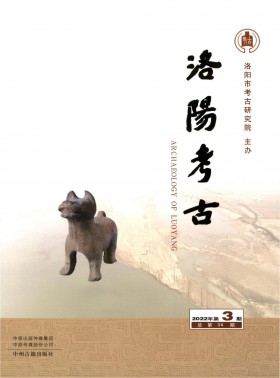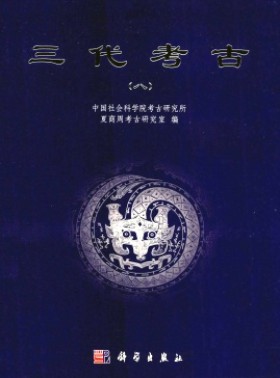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考古研究的方式問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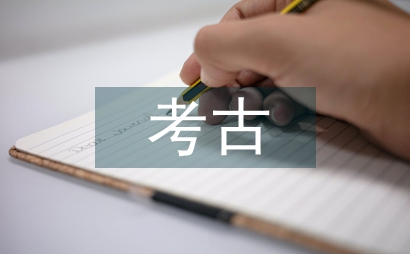
科學研究是一項認真嚴肅的學術活動,進行任何科學研究時都要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考古研究也不例外。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考古學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即以地層學、類型學等基本方法為指導,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相結合進行研究。筆者有幸拜讀殷瑋璋先生的諸篇文章,尤其是近作《考古研究必須按科學規程操作—“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題后的反思(節錄)》(刊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7期,以下簡稱《反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文中先生就考古研究中應使用何種方法進行了探討,指出:“科學研究中有科學操作規程……考古學研究既要遵照科學研究中普遍適用而必須遵循的科學規程,也要遵循考古學特定的科學規程。”拜讀此文后,筆者對先生“考古研究必須按照科學規程操作”的觀點甚為贊同,但同時也存在一些疑問。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見,以求教于殷先生及諸前輩學者。 一不斷吸收新材料,并對舊觀點進行反思 任何學術研究都建立在當時所有資料的基礎之上,隨著考古工作不斷深入開展,資料也隨之逐漸豐富,而一些原有的觀點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這在學術研究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反思》一文指出某些學者在研究鄭州商城的過程中,其觀點經歷了從“隞都說”到“鄭亳說”的變化,并指出是“因為作者在撰寫這兩篇文章時的研究思路是不一樣的,用的方法也有不同,因而操作時的程序規則也不相同。”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似乎不妥。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考古研究也存在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發表于上世紀50年代,當時碳-14測年技術尚未被引進國內,因此作者僅運用傳統的地層學、類型學方法將鄭州殷商遺址出土器物與小屯殷墟遺址出土器物進行對比,得出鄭州殷商文化年代早于小屯殷商文化、小屯殷商文化與其一脈相承的結論,并根據文獻記載初步推測鄭州商城為仲丁之隞都①。在以后的20余年間,關于夏代和商代的重要考古遺跡陸續被揭露出來,人們對于夏文化、商文化的理解也不斷加深。在這種新的學術環境中,一些學者結合新發現的考古資料、文獻材料及測年數據,提出了鄭州商城為亳都的新觀點②。這種觀點的轉變并不是由于所謂的“研究方法的變化”,而是建立在分析新材料基礎上得出的新結論。已有學者明確在文章中剖析自己觀點轉變的原因:“過去,我傾向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因而曾認為二里頭類型是早商文化。自‘鄭亳’說提出后,重新考慮這一問題,則感到‘西亳’說證據太弱,矛盾甚多。……與此相對照,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論斷論據要有力得多。”③由此可見,觀點的轉變源自于材料的不斷豐富和學者研究的深入,并非由“研究方法的變化”引起。縱觀我國考古學研究的進程,不難發現,這種觀點出現前后變化的現象比比皆是。如在陶寺文化發現初期,部分學者認為無論從其分布地域、文化性質、社會發展階段等皆與文獻中所記載的夏代接近,因此推測其為夏文化④。但是隨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重大發現和研究越來越深入,有學者從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方面對陶寺文化進行了分析,明確指出“陶寺類型很難具備夏文化主體的條件”⑤。陶寺文化為夏文化說漸漸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一些起初支持陶寺文化為夏文化的學者也逐漸轉變了看法⑥。這種觀點的變化就是建立在綜合研究新資料的基礎之上的,而并非是研究思路的變化所導致。學術研究的道路是曲折而艱辛的,任何一種科學研究都無法跳出時代的窠臼,尤其是研究一些復雜且缺乏資料的問題時,沒有人能夠一蹴而就。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根據對新材料的運用,改變自己過去的觀點也是普遍現象。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我們不能為了堅持某一觀點而堅持,應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接受新資料,經常對自己原有的結論進行反思,用新材料驗證原有觀點正確與否,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更接近于事實的結論。因此可以說,在吸收新材料的基礎上對舊有觀點進行反思以致改變舊有觀點的做法是科學的;相反,一味堅持舊說,而不及時引用新材料對舊有觀點進行印證的做法則恰恰是不科學的。 二正確對待碳—14測年結果 考古地層學、類型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只能確定古代遺存的相對年代和演變序列。20世紀中葉開始應用于考古上的碳—14測年法為斷代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可以說碳—14測年技術在我國的引進及運用為建立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夏商文化編年體系的框架提供了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⑦。尤其是自上個世紀末“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展以來,碳—14測年技術越來越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重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項技術目前仍不完善,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作為考古研究中的一個參考數值。因為測年標本的選擇、樣品的制備、不同測年方法(主要是常規測年法和加速器測年法)的運用、對測年數據不同的擬合方法等均可影響測年結果的準確性⑧。尤其是對于歷史時期的考古研究,較大的誤差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因此,碳-14年代數據只能是一個參考而非斷代的唯一依據。《反思》中認為《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的作者“從鄭州商城測定的一批碳十四年代數據中選了一個,……既不作必要說明,也未作任何論證,就直接加以引用……這種做法是很不妥當的”。但實際情況是,70年代隨著鄭州商城發掘工作的展開以及碳-14測年技術的引入,鄭州商城的發掘者在簡報中根據商城出土物、地層關系及碳-14測年結果將其始建年代定為距今3570±135年(公元前1620年)⑨。根據這一系列新的考古、測年材料,鄒衡先生反思50年代的觀點,綜合文獻分析認為鄭州商城不可能為積年只有20余年的隞都,而應當是湯之亳都。因此《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是對鄭州商城發掘簡報中發表的年代數據加以引用,不存在“既不作必要說明,也未作任何論證,就直接加以引用”的情況。此外,《反思》一文中提出:“必須用準確的年代作立論的前提。”筆者對此深表贊同,但是同時應該看到在碳-14測年技術引進之初,學術界普遍對其認識不深,加之后期測定的年代數據的不斷變化,使其不可能有“準確的年代”。尤其是近年來,學術界又發表了一批關于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文化的碳-14測年數據。在這些數據中,出現了夏商文化年代“越測越晚”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關于二里頭文化年代的認識從最初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⑩,向后推遲至公元前1750-前1540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中,眾多學者根據碳-14測年數據推斷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但僅時隔5年,又有新的碳-14測年數據公布,指出鄭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且不說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測年數據使眾多學者無所適從,就是在所謂的新技術條件下測出的數據是否準確可信也無人能夠保證。殷先生卻以此為據來證明《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引用碳-14年代數據存在很大誤差,不可憑信,與此同時又引用了另外一批測年數據來證明自己“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為早商文化”的觀點。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先生據何認為自己采用的年代數據是準確的,而鄒文引用的就不準確?通讀《論湯都鄭亳及其前后的遷徙》(見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肆篇)可以發現,作者首先以大量的文獻證據和考古事實論證了自漢代以來關于亳都地望的四種觀點的不合理性,然后分析鄭州商城為隞都的不合理性,最后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并結合鄭州商城的考古資料推斷其為亳都。在論證的過程中碳-14測年數據僅作為判斷鄭州商城性質的一個參考,這種研究方法無疑是正確的。而反觀另外一些學者,僅引用一批新的所謂“科學”的碳-14數據就判定“二里頭遺址的第三、四期遺存應在商紀年之內,不可能進入夏代紀年。……所謂二里頭文化第一至第四期遺存均是夏文化的假說,也就難以成立了。”這樣的推論難道就是“科學”的?這樣的研究方法難道就是“遵循考古學特定的科學規程”?應該看到,目前的碳-14測年技術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僅能提供一個大概的年代范圍,與實際情況存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誤差,有時甚至會出現與傳統考古學斷代方法得出的結論相矛盾的現象。因此在判定考古遺跡的年代時應綜合考慮各種情況,不能僅憑碳-14測年數據下結論。何況誰又能保證新測定經“擬合”的碳-14年代數據就是“科學”的數據呢?在進行考古研究,尤其是進行三代考古研究時,必須對碳-14測年的結果有清醒的認識,一方面不能忽視其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同時也必須避免考古學研究被碳-14測年數據牽著鼻子走的尷尬現象。#p#分頁標題#e# 三找好研究的切入點,小心求證 考古研究的途徑并不是單一的,俗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一個具有可行性研究的切入點能夠事半功倍,因此尋找一個好的切入點是首先要考慮的。其次,論證部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內容,是決定一個學術觀點能否成立的關鍵,因此必須嚴密分析,小心求證。在《反思》中,殷先生指出“《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先設定鄭州商城是成湯所建的亳都,再選用東周時期的‘亳’字陶文作為依據,指認二里岡文化為早商文化,再找‘合適’的年代去說明之”,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妥。由于商代后期之前階段的考古研究,存在著沒有發現成熟文字、文獻記載少而且相互抵牾的實際情況,因此在研究夏文化時“只靠考古學上的文化分期以及近年應用于考古學上的碳-14年代測定顯然都是無法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選取一個新的研究切入點無疑是研究夏文化問題的新途徑。在《論湯都鄭亳及其前后的遷徙》中,鄒先生明確指出尋找亳都是“解決二里頭文化的年代、性質及其社會發展階段諸問題的關鍵”。這是鄒先生研究夏文化的切入點,鄭州商城為亳都是經過嚴密論證后得出的結論,并不存在“因果倒置”的現象。通讀《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可以發現,作者引用大量考古、文獻資料,從文獻所見鄭地之亳、鄭州商城出土陶文證明東周時期鄭州商城名亳、湯都亳的鄰國及其地望與鄭州商城相合、商文化遺址發現的情況與成湯都鄭亳相合四個方面進行論證。鄒文的結論是建立在對大量文獻、考古資料進行嚴密分析并小心求證的基礎上的,并非僅憑東周時期的“亳”字陶文,就指認二里岡文化為早商文化。《反思》中還指出:“他們(指‘鄭亳說’者)主張的‘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觀點,同樣也不是從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遺存的分析與論證中提出,而是由‘鄭州商城湯都亳說’推導而來。”這種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為了論證二里頭文化的性質,鄒衡先生首先從尋找商文化的源流入手,以堅實的類型學證據論證了二里岡文化由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區的先商文化漳河型直接發展而來,先商文化的年代大致相當于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進而又對比二里頭文化四期器物的發展情況,指出二里頭文化的四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并且其年代早于二里岡文化,為夏文化。鄭州商城為亳都只是判斷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的論據之一。鄒先生以尋找商文化源流為切入點尋找夏文化,也正符合殷先生所倡導的“在早于商代早期的非商文化遺存中尋找夏文化”的方法,何來“不從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遺存的分析與論證中提出,而是由‘鄭州商城湯都亳說’推導而來”的現象呢?而反觀殷先生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三、四期為早商文化的觀點,最主要的論據就是認為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出現了一組商文化因素。眾所周知,考古學文化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封閉的,因此在某一考古學文化中很可能出現多種文化因素。李伯謙先生曾指出:“考古學文化所含諸文化因素既有質的不同,又存在量的差別,考古學文化的性質正是由其中占主導地位的因素決定的。”夏王朝和先商是宗主國同與國的關系,雙方文化早有交流,在二里頭文化中出現部分商文化因素也合情合理,因此判斷二里頭文化是否發生質變的關鍵就在于其中的商文化因素所占的地位。殷先生雖然意識到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中出現了一組與二里岡文化中富有特征的器形十分接近的器物,而且這組器物的數量隨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這一考古事實,但在論證時只簡單指出“雖然這組新器形代表的文化因素在數量上還沒有達到二里岡期所占的比重,但它的數量明顯增多,表現出替代和融合原來那組文化因素的趨勢,似可認為代表了文化發展的方向。”殷先生在《反思》一文中曾指出“研究要按規程,推測不能代替論證”,但是上文中的“似可認為”恰恰說明了殷先生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二里頭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而僅僅是一種推測。這種研究方法難道是符合“科學規程”的嗎?筆者認為,如果僅從分析二里頭文化本身來判斷其三、四期是否已經成為商文化,應該分析商文化因素的滲入是否已經導致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發生了質變。關于這一點,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者指出:“在二里頭文化三期,炊器類以深腹罐和圓腹罐為主,……開始出現陶鬲,最早的鬲腹呈罐形,器身中部捏出分襠線,底部較平,下附實足尖。由此可見,二里頭遺址的陶鬲是仿效罐的形式,從圓腹罐(鼎)發展起來的。……到了二里頭文化四期,雖然鬲的數量有所增多,但炊器類還是以深腹罐和圓腹罐為主。”殷先生忽略了二里頭遺址發掘者的權威性分析,不立足于縝密分析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中諸文化因素的比例,卻稱“假如只有在兩種文化完成‘質變’以后才能作為斷代依據,那么,在考古學中只有否認秦王朝的存在。”如果說在某一文化中一出現其他文化因素就說它的文化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恐怕學術界對此也不能認同吧。殷先生以“文化面貌的變化相比政治事件具有滯后性”來證明二里頭三、四期已經不是夏文化,又用“似可認為”的證據對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的性質下定論,這種研究方法又怎么能稱得上“科學”呢?對于分歧較大的學術問題,如果能夠選好研究的切入點,并立足于基本材料,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相反,一味拘泥于所謂的“規程”,卻忽略了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論證環節,那么得出的結論只能是經不起推敲的“不科學”的結論。 四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殷先生所提出的“考古研究必須按科學規程操作”是進行考古研究時所必須遵從的。俗話說“無規矩則不成方圓”,如果沒有一套科學而又嚴謹的研究方法指導科學研究的進行,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是紙上談兵,想要取得進步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要促進學科的發展了。對于嚴密而又科學的研究方法,要做的不僅僅是要知道,更重要的是要會科學運用。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逐步深入、進而完備的過程,在一些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有時提出的某些觀點或許有失偏頗,但如果能隨著資料的增多而不斷修繕之前的認識,那也不失為一種進步。這種精神需要鼓勵,對于不足的地方,則要進一步研究使其得到完善。早期資料的有限性加上每個人學科知識的異同,對于相同資料的理解與看法是不同的,只要按科學嚴密的研究方法開展學術研究,相信是能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的。這樣,考古學科研究才會取得較大的進步,學術問題才會越來越明朗化,學科體系才能逐漸完備。#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