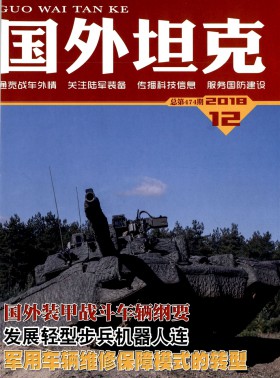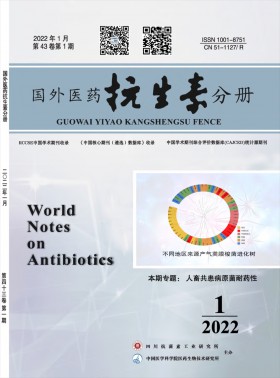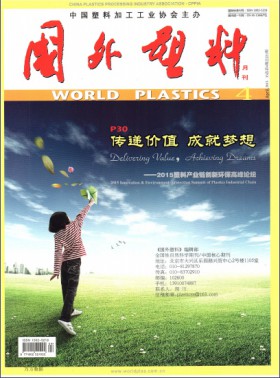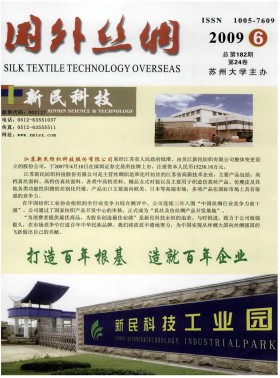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外農業生態學啟發,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駱世明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熱帶亞熱帶生態研究所 農業部華南熱帶農業環境重點實驗室
對農業生態學使命的認識
農業生態學的興起顯然是受到農業發展遇到不可持續問題推動的。“國際農業發展知識、科學與技術評估組織”總結了2008年4月由各國政府代表參加的南非會議成果,發表了《農業處于十字路口》[4]。報告清晰表明各國都認識到按照目前的農業生產方式,資源支撐不了未來社會對農業產出的要求。報告認為包括產品供應、經濟效益、生態環境服務在內的農業多功能性是不可回避的,其中第7條結論指出:“通過進一步將農業知識與科技轉到以農業生態科學為主,將有利于解決環境問題,同時維持和提高生產率。”在國外“Agroecology”使用的范圍不僅包括“農業生態”,也用到我國常用的“生態農業”表述方面。聯合國食品權特別報告員DeSchutter[5]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縱覽過去5年來發表的科學文獻,特別報告員認定,生態農業(agroecology)作為農業發展的模式不僅展現出在概念上與食物權有很強的關聯,而且證實生態農業可以在國情不同的各個國家中為眾多弱勢群體具體實現食品權這項人權取得明顯的進步。此外,生態農業展現出的種種優勢,與人們熟悉的常規方式,諸如培育各類高產改良品種的做法成為互相補充的一種農業方法。
生態農業能夠有力地推動更為廣泛的經濟發展。”他建議通過擴大生態農業的實踐,以便能夠在增加農業生產、增加收入、改善生計的同時避免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及生態環境的破壞。在美國加州大學SantaCruz分校舉辦的第13屆國際農業生態培訓班上,人們引用愛恩斯坦的名言:“我們不能夠用產生問題的思路去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人們認為引導工業化農業發展的傳統農業科研思維屬于還原論(reductionism)。這種還原論方法已經不能夠勝任未來農業發展的要求。農業生態學要促進農業一系列觀念變革,從而克服一系列傳統工業化農業引起的嚴峻問題(表1)。美國農業部在2009年終于跟隨眾多歐洲國家在人力、物力和機構設置上大力支持有機農業發展。在這個基礎上,Hooedes等[6]撰寫的美國農業“國家有機行動計劃”中,認為有機農業也應當采取農業生態學的綜合、整體、多樣的思路,甚至認為應當在傳統農業研究機構以外成立獨立的有機農業研究機構,以擺脫傳統農業研究的還原論思維。顯然國際上農業生態學被認為是一種對工業化農業方式和傳統農業科研思維的深層次顛覆和革命,并賦予了支撐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使命。
對農業生態學內涵的認識
丹麥農業科學研究所農業生態系的Dalgaard等[7]在綜述農業生態學的時候根據不同研究人員的研究范圍,提出了農業生態學的硬件部分和軟件部分。他們認為與農業生態系統的能物流、資金流有關的生態、農學與經濟學結合的部分可以稱為“硬農業生態學”(hardagroecology)部分,而與人類社會及其利益管理體系有關的則可以稱為“軟農業生態學”(softagroecology)。他們的文獻搜索結果表明,使用了“agroecology”或者“agro-ecology”關鍵詞的文獻中66%屬于自然科學,13%屬于社會科學,5%屬于經濟學文獻,16%屬于自然與經濟結合學科,2%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沒有同時跨自然、社會、經濟三大學科范疇的文獻。法國農業生態學與景觀生態學家Wezel等[8]在綜述農業生態學文獻時發現,農業生態學的研究范圍是趨向擴大。擴大方向之一是從農田層面向農業生態系統和地理景觀層面拓展。擴大方向之二是從農學、生物學、生態學的“硬農業生態學”向農業生態系統管理、農村可持續發展、社會學與經濟學等“軟農業生態學”發展。美國著名農業生態學家Gliessman[910]索性把農業生態學描述為研究從農田到餐桌的整個食品供應體系的生態學。Wezel等[8]認為,目前“農業生態學”實際上指的既是一個學科,還是一類實踐,甚至是一種運動。
農業生態學作為一種農業實踐方式的認識
在中國農業生態學指導的實踐被普遍稱為生態農業,然而在國際上生態農業的術語應用并不廣。利用“ecoagriculture”或“eco-agriculture”為題目或者關鍵詞的文獻到2010年僅有46篇,其中有34篇文獻的作者還是中國學者。在中國1990—2010年“生態農業”為關鍵詞或題目的文獻卻達到7986篇。在國際上大量使用“agroecology”來描述利用農業生態學指導的實踐,實質等同于中國的“生態農業”實踐。聯合國食品權特別報告員OlivierDeSchutter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也如此,以至在翻譯中需要把“agroecology”翻譯成“生態農業”才符合中國人的表述習慣。Altieri[11]認為應當重視循環體系建設和維護土壤有機組分,充分利用物種多樣性與遺傳多樣性以便提高太陽能、水分和養分等自然資源利用率,還應當注意通過擴大物種間有利的相互關系,強化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DeSchutter[5]提出生態農業需要模擬和利用自然進程,通過流域和生態系統的整體生物多樣性構成、養分循環和能源流動關系構建來實現系統的多功能協調。報告中列舉生態農業的實踐模式有農林結合模式、農牧結合模式、流域集水模式、綜合養分管理模式和綜合有害生物防治模式(玉米地防治玉米螟的推拉體系、稻田養鴨體系)等。在美國加州覆蓋作物和有害生物的陷阱作物也經常用到。
由于生態農業是智力密集型生產方式,而不是投入集約型生產方式[11],除了重視新技術和新模式以外,國際上普遍重視來自廣大農民的實踐經驗和經歷長期實踐證實行之有效的傳統農業遺產。2004年以美國學者SaraScherr牽頭在內羅畢成立了國際“生態農業伙伴”(ecoagriculturepartner)[12]。其最大特點是強調通過景觀層面的布局,協調生態、生產與生活關系。該組織的口號是“為了人民、食物和自然的景觀”。在其內羅畢宣言中,除了強調景觀分區布局和管理外,還強調結合喬灌草的農林體系(agroforestry)和實施有機與循環方法。Gliessman[10]認為,傳統農業向生態農業實踐轉變可以分為4個水平。第1個水平為資源節約技術,推廣節肥、節水、節能技術等。第2個水平是投入替代技術,化肥用有機肥替代,農藥用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替代。第3個水平是系統結構變化,在農業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結構、循環體系結構和流域景觀元素配置結構的變化都屬于這個水平。第4個水平是食品供應體系的改革,食品供應體系包括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業生產者、食品加工、產品運輸、商品銷售、食品消費者之間的關系調整。美國“國家有機行動計劃”中也提出要避免把有機農業簡單理解為允許和不允許投入什么的農業,有機農業是與農業所存在生態系統結為統一體的農業系統[6]。#p#分頁標題#e#
農業生態學作為一個運動的趨勢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展生態農業建設逐步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目的在于發掘農民智慧、改善食品供應體系、提高農村生活質量、增加農民經濟收益、保護珍貴農業遺產、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拉丁美洲的“農民對農民運動”(英文:farmertofarmermove-ment,西班牙文:movimientocampesinoacampesino,簡稱MCAC)是在發展中國家相當突出的一個例子,該組織成立已經36年了,目前遍布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如古巴、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巴西等,參加運動的農戶達到數十萬。在20世紀60—70年代,依托良種,并依賴化肥、農藥、灌溉等高投入為基礎的“綠色革命”在拉美國家小農中推廣失敗。8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使得拉丁美洲國家不得不接受縮減政府、出售國有企業、開放市場等措施,農產品市場被發達國家占領,土地被大公司占領,農業推廣服務萎縮,農民被迫成為城市居民或者退守邊緣區域。同期,在國際上可持續農業和農村發展(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SARD)項目推動下,拉美國家的小農發現,生態農業方法不僅使其產量倍增,而且保護了環境。于是他們就在這些項目組織交流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農民之間進行技術和經驗交流的組織。目前該組織正試圖凝聚力量,在交流生態農業技術的同時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管理體系和國家政策[1314]。
在武裝叛亂麻煩不斷的尼加拉瓜,全國農民與牧民聯盟在1987年開始實施“農民對農民項目”(campesinotocampesinoprogram)并且取得成功,農村也得到了安寧。成功的原因總結為:農民自己的試驗和評價,本土知識的交流,活躍的對話和創新,水平對話機制出現的乘法效應,有推介成果的積極分子出現,創新成為農民的風氣,不斷有地方領袖出現[15]。在古巴1999年正式成立農民對農民農業生態運動,農業生態運動成功解決了在禁運條件下通過利用當地資源與經驗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在保障供給中顯示出了明顯優勢,2009年就有超過11萬戶農民參加[16]。在巴西,2001年召開全國農業生態學會議,2002年成立全國農業生態聯盟,2003年在有機農業的法律框架內認可了農業生態,2004年成立巴西農業生態協會,2006年巴西農業研究組織正式把農業生態作為該研究機構的一個學科領域[8]。在生態農業推廣過程中,各國特別注意避免過去農業推廣那種自上而下、居高臨下的方式,重視農民的平等參與及橫向交流。農業生態在美國也已經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形式存在。在美國加州,加州大學SantaCruz分校有機農場為農民提供有機農業培訓,校內建立了社區農業生態項目(programincommunityandagroecology)。加州還成立了各種形式的與農業生態有關的民間組織。例如“社區農業生態網絡”(CommunityAgroecol-ogyNetwork,CAN)、“農業和基于土地的培訓聯盟”(AgricultureandLandBasedTrainingAssiociation,ALBA)、“社區支撐農業”(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根本的改變”(RootofChange)、“食物共有”(FoodCommon)等。這些非政府組織從不同的側面推動農業生態的發展。RootofChange致力于把被現代商業運作分割了的食品供應體系重新連接起來。FoodCommon計劃建立有機食品供應體系,力爭在2020年實現10%的本地消費食品為本地生產。
ALBA著力培訓和培育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小型農民企業。他們不但提供技術培訓,而且為起步農民提供廉租農田。CAN則通過與拉丁美洲咖啡生產者建立直接聯系,增加生產者收益,減少消費者負擔,建立起消費者對生產者和生產方式的了解。另外FarmerMarket為農民生產的有機食品提供了直接與消費者接觸的渠道。“美國收獲正義”(JustHarvestUSA)組織則為外國農民工提供保護,爭取正當權益。美國有機農業運動也是從民間開始的。在20世紀60—70年代相繼成立了“加州有機認證農民”(Ca-liforniaCertifiedOrganicFarmers,CCOF)、“有機農民和園藝者聯盟”(MaineOrganicFarmersandGar-denersAssociation)、“東北有機農業聯盟”(NortheastOrganicFarmingAssociation,NOFA)等。民間的大量工作促使美國農業部在2000年制定了國家有機食品標準,并在農業部設立國家有機農業項目,2009年專門設立管理職位[6]。
農業生態學作為一個學科的認識
法國Wezel等[8]的分析表明,德國基本還是把農業生態學放在一個生態學分支學科的范疇看待。例如德國哥廷根大學作物科學學院農業生態系定義:“農業生態學集中研究在農業景觀區和農業生態系統中的動植物群落、食物網關系和保護生物學”。德國馬丁等[17]在2006年寫的“農業生態學”中定義農業生態學為:“研究人類為某些作物的生態所塑造的環境中生物生存條件的科學”。這不同于美國以Gliessman[10]為代表的包括社會經濟體系在內的定義,即“農業生態學是研究食物系統的生態學”。Dalgaard等[7]則利用社會學家RobertKingMerton(1973)提出,后來為JohnZiman(2000)再次論述的評判科學的4條規范來評判農業生態學。第1條評判標準是關于內容的社群性(communalism)方面,要求科學的內容能夠向社會大眾擴散。第2條規范是研究人員的包容性(universalism),即科學研究人員應當不分種族、膚色、信仰、性別等,有廣泛的包容性。第3條規范是利益中立和謙遜(disin-terestedness,humility),研究結果能夠超脫個人利益和研究人員個性是重要的。第4條規范是嚴格論證下的原創性(originality),要求研究結論能夠經受得起懷疑和驗證。文章作者認為第1和第2條規范對于農業生態學不成問題。第3條規范對于農業生態學一般也不會存在問題。但是,農業生態學研究涉及社會層面時,就不容易遵循利益超脫的規范。用第4條規范來衡量農業生態學的時候,文章作者認為一方面農業生態學有些研究僅僅進行半定量的調研和訪談,結論的重復性和嚴密性容易受到質疑,另一方面農業生態學一些小規模的田間研究要上推(scalingup)到系統和景觀層面時所使用的方法太簡單,容易出錯。
對農業生態學在中國發展的啟迪
根據各國對于農業生態學的理解和發展狀況,反觀我國的農業生態學發展,會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迪,有利于更好地認識我國農業生態學發展的優勢和問題所在,以推動學科健康發展。“農業生態學”在我國指的就是一個學科,其指導的實踐和社會運動在我國稱為“生態農業”[18]。這樣就避免了國外認為農業生態學既是學科,又是實踐與運動的問題。在我國農業生態學理論框架中,農區生物與環境通過能物流整合起來的農業生態系統是基本研究對象。這就是所謂的“硬農業生態學”部分。根據控制論原理,調節和控制這個體系的機制包括分散在自然體系中的非中心調控機制和受人類左右的中心式調控機制。中心式調控機制又可以分為經營者和操作者的直接調控,以及影響經營者和操作者的社會文化、社會經濟、社會法規等間接調控。這部分調節控制機制就是所謂“軟農業生態學”部分,其中包括了價值流和信息流。盡管我國在農業生態學體系的構建上比較完整和穩定,但是在與農業生態系統調控相關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法規的實際研究還是落后于需要,也落后于不少國外同行。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我國同行在認識農業生態學對還原論思維方式下的農業方式與農業研究的顛覆性意義方面(表1),還沒有國外同行理解得那么深刻和緊迫。#p#分頁標題#e#
在我國生態農業實踐常被分為生態農業模式與生態農業技術。生態農業技術實際上對應于Gliessman[10]所指的第1水平變革(資源節約型技術)和第2水平變革(投入替代技術)。生態農業模式則對應于他提出的第3水平變革(農業生態系統結構)。我們在認識上還有3個優勢。一是認識到生態農業技術體系與生態農業模式相互聯系,一定的模式對應一定的技術體系。二是認識到生態農業技術體系是由多個相互制約相互關聯的技術組成的。三是在我國生態農業模式方面,農區景觀生態規劃、農業生態系統循環設計、農業生物多樣性關系構建被認為是生態農業模式建設中最重要的3個方面[20]。這個歸納能夠包容迄今為止國際上農業生態實踐中有關的主要模式。不言而喻的是,世界各國豐富的農業生態實踐經驗十分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對于Gliessman食物系統變革的第4水平(從農田到餐桌的社會體系)而言,我們在農產品加工鏈方面偶爾涉及,也在生態農業政策方面加以研究,但是很少在生態農業研究中涉及生產組織、運輸組織、供應鏈組織、市場組織層面。這種狀況與國情應當有關。由于我國市場化處于起步和完善階段,供應鏈的壟斷問題和生產者與消費者被分割的弊端還沒有充分暴露。然而,農業生態結構涉及的社會經濟組織方面仍然值得今后加以重視。
我國生態農業實踐在一開始就是通過有遠見的專家提倡,并在政府部門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最典型的就是“九五”和“十五”期間農業部等8個部委支持的全國100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活動。由于有經費支持,有專家指導,發展快,勢頭猛,頗有些轟轟烈烈的味道。然而其持久性和傳播效率卻不如起源于基層的拉丁“農民對農民運動”。當國家部門的興奮點一旦轉移,全國性有組織的生態農業活動就陷于停滯。相比自下而上的農民運動,自上而下的組織形式在農民自發參與的積極性、眾多參與者的創新勢頭和農民橫向知識傳播的乘法效應等方面都望塵莫及。我國在省、市、縣、鎮、鄉各級組織的生態農業建設一直此起彼伏、延綿不斷。這反映了我國對于生態農業發展的內在需求。我國公民社會正在發育初期,有關農民自發組織開展生態農業的社會環境還有待成熟。然而,我國已經有支持農民技術協會和農業行業組織發展的政策,這為自下而上有組織的農民生態農業行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環境。值得我們今后加以重視。在我國生態農業實踐中非常重視農民經驗和農業傳統知識。中國農業大學李隆教授[21]有關間套作研究、浙江大學陳欣教授[22]的稻魚共作研究都達到了很高水平。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李文華院士與閔慶文研究員領導的團隊持續開展了農業文化遺產研究[23]。李文華院士[24]主編出版的《生態農業》中總結了大量農民創造的生態農業模式與技術。我國是一個有五千年農業文明的大國,目前仍有約6億人口在農村。目前對農業遺產的挖掘和對農民經驗的提升還遠遠不夠。今后,不僅需要科研人員的繼續努力,更需要廣大推廣人員和農民懂得這些經驗和遺產的價值,并有意識地加以發掘、研究、保護和推廣。
目前我國農業生態學研究多在農田和農田以下水平開展。在農田生態系統水平的水分平衡、養分平衡、能量平衡的研究已經從短期田間取樣研究向長期定位試驗站支撐的研究發展。作物間套作的養分、光照、水分、病蟲關系,作物害蟲天敵的化學相互作用,作物土壤微生物的復雜影響,農業生產的溫室氣體排放,全球變化對農業生產影響等研究方向都相當深入,并且常常觸及前沿[25]。然而在農業生態系統和農業景觀層次的研究卻相對較少,與農業生態學相關的社會經濟學研究就更加少了。正如Dalgaard等[7]所指出的那樣,在層次比較高的體系中開展研究有兩個難點,一方面大系統受限于時間和資金,不少研究僅能夠進行半定量的調研、訪談、取樣,得到有關結論的重復性和嚴密性容易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小規模的田間和實驗室研究要上推(scalingup)到系統和景觀層面的方法還不十分成熟。因此利用模擬、模型和數學方法進行綜合和上推成為必要。這需要在我國今后的農業生態學研究中加以強化。農業生態學的社會經濟研究比較弱與我國農業生態學起源于農業高校的農學學科有關。只有通過現有農業生態學家進修有關社會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或者通過與社會經濟學家合作才能夠克服農業生態學在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