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虛假廣告罪的難題探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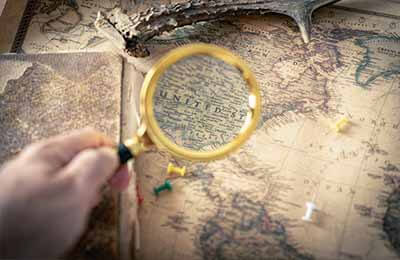
作者:李彥峰 單位:中北大學
虛假廣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屢禁不絕,但虛假廣告罪自1997年刑法典設立以來,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案例卻并不多見。“海量的虛假廣告行為,區區數起虛假廣告罪案件,二者在數據比例上的強烈失衡,反映出了虛假廣告罪的司法窘境。”[1]42造成這種窘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刑法對于虛假廣告罪的相關內容缺乏清晰界定,司法人員在面對虛假廣告行為時往往難以準確把握虛假廣告罪的適用范圍,只能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之間徘徊。以刑法適度干預的價值理念為指導,對虛假廣告罪理解與適用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準確把握該罪的適用范圍,充分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生活應有的調控作用。
一、刑法適度干預價值理念確立
“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和個人兩受其害”[2]。學者們多是從刑法謙抑性的角度對刑法適度干預的范圍進行界定,并在以下幾個方面達成共識,這些共識形成了刑法適度干預的價值理念:第一,刑法是整個社會調控系統中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如信仰、道德、習慣以及其他法律等。第二,刑法在整個社會調控系統中能夠發揮強力的保障作用,刑法的積極價值是不容質疑的,刑法確保了這個社會應有的基本秩序,沒有刑法的社會調控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刑法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對于它的本旨———抑止他人實施違反秩序的行為而言,它只能在一定限度內完成,超過這個限度它的抑止作用會大大減弱。即使有刑法的存在,仍然會有人冒險實施違反秩序的行為發生,因為它只能讓人因為恐懼遭受其懲罰而盡可能不去實施違反秩序的行為,但無益于消除他人產生實施違反秩序行為的沖動的土壤。因此,當整體環境必然使行為人產生實施違反秩序行為的強烈沖動而無暇顧忌刑法的恐懼時,刑法的抑止也將無效。可見,刑法雖然強大,但其預防犯罪目的的完成仍需依賴其他社會調控手段的充分配合,否則,面對犯罪的浪潮,再強大的刑法也無能為力。另一方面,社會中面臨的問題并不單純是令行禁止的問題。當前社會是個相對自由而復雜的社會系統,每個人在一定的限度內都應該有自己選擇做與不做的權利,當因為他的選擇給別人或社會造成侵害時,完全可以讓他通過其他方式來進行補償。一定范圍內的出爾反爾、欺詐違約、辱罵傷害等違反良好秩序的行為是社會正常運作必然存在的,不用法律手段堅決禁止這些不良行為從總體來看也不一定是必然有害的,而應當通過社會的一般規則給予引導或調整。保護他們這種選擇的自由是一個社會正常運作所必需的,不顧任何個人選擇自由的令行禁止是會讓這個社會走向衰亡的。因此,除刑法之外的其他社會調控手段是應該有自己獨立而不被刑法干涉的空間的,否則,將有害于整個社會的發展。總之,僅僅或主要由刑法組成的社會調控也是不可想象的。第四,刑法的手段是昂貴的。刑法比其他任何社會調控手段都要昂貴,它的使用不僅摧殘個人而且拖累和危害社會。“刑法是一種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統治手段”[3]。刑法的使用是權衡了犯罪對社會的危害與刑罰對社會的危害之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因此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社會調控手段。
二、虛假廣告罪虛假廣告的界定
虛假廣告罪虛假廣告的界定是虛假廣告罪認定中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由于現實生活中廣告形式多種多樣,紛繁復雜,且對廣告的感知因不同的受眾或在不同的時代有很大的差異,導致了司法中界定虛假廣告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對虛假廣告的準確界定依賴于以下兩個問題的合理回答:第一,虛假廣告罪所指的“廣告”范圍多大?第二,何為虛假廣告罪中的“虛假”?
對于第一個問題,廣告是基于一定目的通過一定媒介廣而告之的一種宣傳手段,考慮到虛假廣告罪在刑法分則中的體系性位置以及虛假廣告罪與《廣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經濟法的銜接,將此處的廣告限定為與市場交易有關的“商業廣告”較為合理。因為虛假廣告罪的設立旨在打擊和預防在市場交易中對商品或服務進行虛假宣傳而破壞市場秩序的行為,而非商業廣告與市場秩序的良性運行并無關系所以不應歸入虛假廣告罪的干預范圍,應由其他罪或其他調控手段干預為宜。有學者依據《廣告法》中關于商業廣告的規定①,歸納出了虛假廣告罪中廣告的特征,即廣告主必須是以經營、贏利為目的的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商業廣告是付費的宣傳且旨在推銷其商品或服務[4]730-731。據此,社會中出現的廣告不論其形式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如未依法審查而的廣告、街道上四處散發或張貼的廣告;也不論其樣式多么的新穎和令人迷惑,如有償新聞、“專題報道、人物專訪、科技成果、健康專題節目或者在網站上通過網上調查、網上新聞以及在商業網站主頁上開辟論壇討論企業產品與服務所作的變相廣告”[5],只要其符合以上特征,就可認定為該罪中的廣告;而尋人、招聘、懸賞、征婚等廣告因其不具有宣傳、推銷商品或服務的特征而不能納入該罪調整。本文認為,上述標準抓住了虛假廣告罪中廣告的本質,尤其將形式不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非法廣告納入其中,符合該罪適度干預的要求。因為對形式合法的廣告而言,其內容是否真實容易受到相關非刑事法律法規的監管,而非法廣告,刑法之外的調控手段對其監管力度減弱,往往更容易在內容上發生問題,這時虛假廣告罪作為保障廣告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線更應積極干預。此外,對于推銷的對象為法律禁止在市場中流通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的廣告,如出賣槍支彈藥、、提供私刻公章服務等,不應認定為虛假廣告罪中的廣告,因為該行為侵害的法益并非市場經濟秩序,應該運用其他罪或其他調控手段予以干預。
對于第二個問題,我們通常認為“虛假”意味著與事實不符,當廣告在內容上存在虛假時便是虛假廣告,但法律上的虛假廣告范圍要小一些,“廣告就是合法的欺詐”。合理的夸張是廣告的一種藝術表達,屬于消費者對于廣告的合理期待,不會誤導消費者,也不違反良好秩序,在法律中不能被認定為虛假廣告,任何法律均不應干涉。而虛假廣告罪所干預的虛假廣告范圍更小,過度的夸張顯然有悖廣告秩序的要求,應被認定為法律上的虛假廣告,但因其不會誤導消費者進而嚴重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對其干預不符合虛假廣告罪的立法宗旨,而只有那些能夠使消費者陷入錯誤認識的法律上的虛假廣告才能被納入虛假廣告罪的調整范圍。對虛假廣告罪應當干預的虛假廣告的認定應按照以下兩個步驟進行,一是客觀上廣告的內容是否與事實不符,這是一種客觀判斷,容易準確進行,是認定的前提。二是內容與事實不符的廣告是否使消費者陷入了錯誤的認識,這是一種主觀判斷,是認定的關鍵。美國在司法實踐中提出的“合情合理的人的標準”[6],即以當時情況下合情合理的消費者對廣告是否產生誤解為標準進行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張明楷教授也提出最為重要的是考察廣告的內容,如果內容抽象不能使一般人陷入錯誤認識,如果內容具體則足以使一般人陷入錯誤認識[7]626。以合情合理的人或社會一般人的感受為標準,并輔助于廣告內容的考察,為這種主觀判斷提供了合理的方法。經過兩步判斷,只有廣告在內容上虛假且足以使消費者陷入錯誤認識時,才屬于虛假廣告罪干預的虛假廣告范圍。如果廣告內容真實或內容虛假,但合理夸張不會使人陷入錯誤認識,則不屬于法律上的虛假廣告;如果廣告內容虛假,但因過度夸張而不會使人陷入錯誤認識,則屬于法律上的虛假廣告,應納入非刑事法律調整范圍。#p#分頁標題#e#
廣告的內容真實,但表達方式容易令人誤解的商業廣告,如常見的“買一贈一”,是否屬于虛假廣告罪的干預范圍仍然存在爭論。張明楷教授認為,語言含糊、令人誤解的宣傳屬于虛假廣告罪的客觀方面[7]625;而王作福教授則認為這種令人誤解的廣告不屬于虛假廣告,更不能由虛假廣告罪來規制[4]734。本文認為,令人誤解的廣告與虛假廣告罪中的虛假廣告雖然同樣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同是市場經濟中不正當競爭的手段,但二者有本質的區別。該罪中的虛假廣告采用欺詐的方法會使消費者必然陷入錯誤認識當中,行為方式不能被社會容忍,行為者主觀惡性較大,情節嚴重的,理應成為刑法打擊的對象;而令人誤解的廣告運用了語言的策略和銷售的技巧,“消費者雖然對其所宣傳的事實作出錯誤的理解,但是也可能作出正確的理解”[8],并非必然會陷入錯誤認識當中,行為方式雖然違背了商家應有的誠信,但其仍在社會對于商業活動的正常預期之中,行為者存在投機取巧的心理,主觀惡性較小。因此,運用非刑事法律手段予以調控即可,不宜由刑法介入,不屬于虛假廣告罪中的虛假廣告。消息虛假的廣告,因為其所宣傳的商品或服務根本不存在,這種廣告不符合商業廣告的本質特征,只是假借廣告之名行詐騙之實,其行為未依附于市場交易而存在,侵害的是普通的財產權益,而非消費者應有的權益,也未擾亂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不應由虛假廣告罪規制,情節嚴重的可構成詐騙罪。
三、虛假廣告罪情節嚴重的理解
虛假廣告罪情節嚴重的理解是虛假廣告罪認定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2001年,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作出的一個司法解釋中給出了相對明確的標準,分別從廣告主違法所得金額10萬元以上、消費者直接經濟損失金額50萬元以上、因虛假廣告被2次行政處罰、造成人身傷殘及其他嚴重后果五個方面進行認定。對于該司法解釋,有學者認為背離了虛假廣告罪的精神,使該罪功能不能充分發揮。因為虛假廣告罪的主要客體是市場交易秩序,“對交易秩序的侵害不僅僅只是包含了行為人的獲益,交易者的直接財產損失,還包括了交易人必然的間接財產損失以及其他廠商的財產損失……衡量破壞交易秩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應以其所導致的交易成本的不合理增加以及交易行為的萎縮效應為基礎。”[1]45-46而司法解釋卻側重以行為人的獲益和交易者的直接損害為依據判斷情節嚴重,這樣不能全面反映該罪的社會危害性,使一些諸如行為人未獲益、交易者未損失,對整個交易市場卻造成很大沖擊的虛假廣告行為不能入罪(如通過虛假廣告進行價格適中的銷售對不進行虛假廣告的廠商造成了負擔)。此外,虛假廣告罪法定刑較低,將其作為行為犯看待更加合理,但司法解釋卻均是以結果為衡量標準。也有司法人員提出,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應該“突出結果,全面衡量”[9]。以上觀點均體現了虛假廣告罪的立法精神,為準確理解情節嚴重提供了價值指導。本文認為,司法解釋提供的各項標準本身并無不當,因虛假廣告行為而使行為人獲益或交易人受損達到一定程度必然應該認定為情節嚴重,但僅僅堅持以上五個方面的標準,單純以是否出現后果來評判的確不夠全面。況且,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獲益、交易人受損的金額并不容易認定,這樣就使一些具有刑法可罰性的虛假廣告行為脫離刑法制裁。在司法實踐中,應對虛假廣告行為進行全面考察,包括虛假的程度,虛假廣告的媒介,投放的持續時間、次數、涵蓋的范圍,所涉商品或服務的性質,行為人獲益程度,交易人和其他競爭者受損程度,對整個市場良好秩序的破壞程度等。出現上述具體嚴重后果的當然認定為情節嚴重,未出現上述具體嚴重后果的,也應根據以上各項指標綜合評估是否足以造成具體嚴重后果,尤其是當適用非刑法手段調控達不到抑止效果或處罰太輕的,應該大膽認定為情節嚴重,適用虛假廣告罪規制。這樣并不會違反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因為可以將這些具有刑法可罰性的虛假廣告行為對市場秩序的破壞均視為司法解釋中所規定的“其他嚴重后果”。
四、虛假廣告罪主體范圍的把握
虛假廣告罪主體范圍的把握是虛假廣告罪認定中較為復雜的問題。我國刑法在虛假廣告罪中明文規定了該罪的主體為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據此,通說認為,我國虛假廣告罪是特殊主體,并依據《廣告法》的規定對三者進行了解釋。而有不少學者對虛假廣告罪是特殊主體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本文認為,對虛假廣告罪主體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廣告法》的規定,虛假廣告罪的主體并非特殊主體。《廣告法》旨在對廣告秩序進行規范,因此,其對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的界定注重形式的合法性,而虛假廣告罪旨在打擊虛假廣告的制作和傳播,其對相關主體的界定更側重于實質的方面。具體來說,對于不具有合法營業資質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實施虛假廣告的行為,虛假廣告罪不能因為其主體不符合《廣告法》的規定而不予規制。如沒有營業執照的人為出售手頭貨物而委托他人制作廣告的也應認定為廣告主,無廣告經營資質的人接受廣告主委托為其組織制作廣告的也應認定為廣告經營者,在街道上散發廣告傳單的人也應認定為廣告的者。正因如此,雖然《廣告法》中規定廣告者只能是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但我國通說仍然認為廣告者不排除個人[10]。可見,任何人均能成為虛假廣告罪中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該罪的主體并非特殊主體。反之,如果將其視為特殊主體,則后果不堪設想。廣告活動從委托、制作再到涉及到的人員眾多,如果將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者視為特殊主體,那么所有參與到廣告活動中的人,只要與他們有通謀就可以共犯的形式構成虛假廣告罪,尤其在廣告制作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并非專業的廣告從業者,如臨時參與的群眾演員,如果其在參演之前沒有按照相關規定盡到其對所推銷商品或服務是否真實合法的審查義務,很容易被推定為具有虛假廣告罪的間接故意,最終認定其構成虛假廣告罪,顯然打擊面太寬,且也是強人所難。
虛假廣告罪如此規定并非畫蛇添足,而是旨在限制該罪的處罰范圍。如同擾亂交通秩序罪中特別規定了首要分子且參與者眾多但只有首要分子可構成此罪一樣,在虛假廣告活動中,雖然參與者人數眾多,但只處罰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因為這三者是虛假廣告活動產生社會危害性的根源,而對于其他參與者不按照共犯刑罰處罰。這種理解符合刑法適度干預的價值理念。對于社會問題的治理,不能完全依賴刑法,必須充分發揮整個社會調控系統的作用,刑法的適用要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對危害性大的適用刑法;對危害性較小的適用其他非刑罰措施,這種有層次的治理才能達到最好的社會效果。當然,對于三種主體之外的參與者有時其實際危害性并不比這三種主體小,如名人虛假代言、推薦,但只要對三種主體進行有效地刑罰打擊,對虛假代言、推薦的名人科以嚴厲的非刑罰懲罰措施,則這種現象自然會喪失存在的土壤。反之,如果對作為廣告參與者的名人實施刑罰制裁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如名人與普通人如何界定以及名人的參與對廣告業不可或缺,但刑罰的打擊會嚴重壓制名人參與廣告業的意愿,影響廣告業的正常發展等。因此,在虛假廣告罪的認定中,應當將主體僅限于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者三種,對于其他參與者不能以共犯形式處罰,也堅決反對在虛假廣告罪中增加廣告推薦者的主張[11]。#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