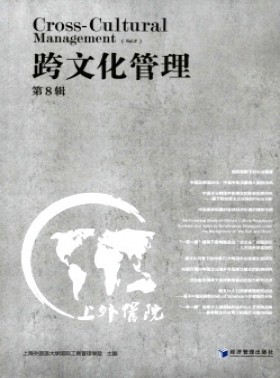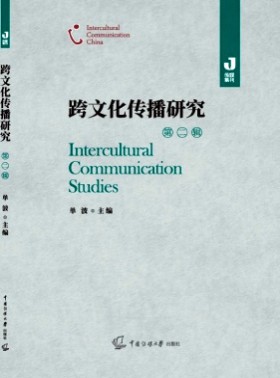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跨文化視野中的功夫熊貓,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2011年5月,《功夫熊貓2》在中國內地首映,這只延續了以往風格的可愛熊貓在上映前兩日就在中國內地狂攬1.2億元(約合1850萬美元)的票房,[1]這一令人驚愕的票房高度使得2010年的巨制《阿凡達》都相形見絀,足見其非同凡響的受歡迎度。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熊貓、功夫、煙花、宮殿等這些具有典型中國風格的一系列文化符號出現在這樣一部由好萊塢出產、在中國放映的影片之中,不免有些譏諷的意味。這一跨文化傳播的主動權或許本來應該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然而吊詭的是卻被好萊塢先發制人,讓一只外國熊貓披上中國外衣,結結實實地把我們“反跨”了一把。 一、《功夫熊貓》系列:跨文化傳播的經典案例剖析 跨文化傳播學者古迪孔斯特(WilliamGudykunst)認為,跨文化傳播涉及有關文化與傳播研究的各個方面。于是有學者認為,跨文化傳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間以及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與活動,設計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活動,以及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流動、共享、滲透和遷徙的過程”[2]。由此觀之,《功夫熊貓》系列確實可以看做跨文化傳播的一個經典案例。在這部影片之中,受眾感受到的滿眼都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元素符號,如熊貓、中國功夫(虎拳、鶴掌、蛇拳、螳螂拳、蛇形刁手)、傳統中國服飾(阿寶的布鞋、父親鴨子的長袍馬褂)、中國食品(面條、包子)、中國建筑(宮殿、寺廟、小院)、中國的哲學思想(尊重客觀規律、心靜如水),等等。然而在這層中國傳統包裝的外衣下,我們看到的阿寶卻是另外一副模樣,幽默的語言、大大咧咧的性格、夸張的肢體動作、豐富的表情……這完全不是一個我們所了解的東方人的性情。具備這副模樣的阿寶儼然就是一個“西方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只美國熊貓,這是我們經常可以在好萊塢影片中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也就是在這種中國文化外衣的包裹之下,這只熊貓帶著它的美式風格和美國文化席卷而來。受眾可能會意識不到美國文化的侵襲,然而這的確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在這部影片中,好萊塢的制片人用他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來向中國人講述其美國文化的種種精神。比如阿寶面對強敵時的樂觀精神、總是能夠在最后力挽狂瀾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觀等,這些無疑都是中國文化中少有表現的。盡管受眾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些美國精神的傳播,然而這正恰恰說明了這種跨文化傳播的潛移默化。當受眾從電影院里出來,心滿意足且饒有興趣地回憶起電影情節甚至推薦親朋好友也來觀看時,他們已經對這部影片建立了心理認同,《功夫熊貓》系列的跨文化傳播也就得以成功完成。 之所以說《功夫熊貓》系列是跨文化傳播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因為它有著與其他好萊塢電影的一個不同之處,這個不同之處可以叫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從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至今,我國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三百多所孔子學院,這無疑為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與國學教育開辟了新途徑。因為文化意味著國家的軟實力,文化輸出是比物質產品輸出更重要的層面,這是全世界都認同的話題。所以挖掘我國的傳統文化,以恰當的方式傳播我國特有的中華文化,不僅能夠消除國家之間的偏見和誤解,還能達成文化的認同,提升我國的軟實力。當然,不只是我們意識到文化巨大的影響力,作為美國電影最重要的根據地,好萊塢早已成為美國進行跨文化傳播的大本營。在《功夫熊貓》系列中,好萊塢創造性地將我們輸出給他們的中華文化進行了包裝,然后又以此為賣點將包含眾多中國文化元素的電影賣到了中國,不僅賺得盆滿缽盈,而且還達到了將美國文化進行傳播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雕。當我們試圖輸出中華文化來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時候,美國人這招“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著實令人驚嘆。 二、跨文化傳播并不等同于文化侵略與文化殖民 《功夫熊貓》系列上映伊始就引發了關于文化侵略與文化殖民的討論,這或許也正是上述好萊塢“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文化效應”。畢竟這部影片中有著太多我們所熟悉的文化元素,然而這竟然是一部用我們的文化賺我們的票房的好萊塢之作!這一系列影片帶給國人的心理落差在所難免。但是如果將其看作嚴重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又似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從文字表面來看,“侵略”與“殖民”的原始含義都是指在違背對方意愿的情形下采取的強制措施。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功夫熊貓》系列影片并不存在所謂的文化侵略與文化殖民,它給觀眾帶來的影響嚴格說來也只能歸為文化傳播。因為在該系列影片取得極高票房的背后,沒有人遭到了夢工廠的強迫,也沒有人受到派拉蒙的威脅,觀眾對其發自內心的喜愛和有口皆碑的評價都源于影片本身的精彩。對于《功夫熊貓》系列文化侵略與文化殖民的恐懼的產生,恰恰說明了傳媒與權力的極大關系。蔣原倫教授在《媒介文化十二講》中指出,統治階級的話語霸權“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是通過諸如家庭、教育制度、教會、傳媒和其他文化形式這類機制而得以運行”。其中,傳媒作為一個結構有序的意識形態領域,作為一個復雜的統一體,是建立在傳媒與作為整體的社會分享的指意語匯之上的。 由于這一分享,“觀眾感到他們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碼,故而是認可了作為系統的傳媒”[3]。掌握了傳媒,就很有可能掌握話語權,這在當代社會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認為《功夫熊貓》系列會產生文化侵略與文化殖民的學者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會害怕有一天美國文化會搭乘好萊塢大片長驅直入我們的文化國土,消亡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當然,我們并非認為這種情況絕對不會發生,任何一種情況都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文化層面是整個社會系統中最為穩定的,并非輕易就能被消亡,何況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而長盛不衰,其穩定性更是超出想象。反過來說,對于像《功夫熊貓》系列的好萊塢作品的跨文化傳播,我們要采取的并非是抵制這種低級的做法,而應該用更為精彩漂亮的作品將觀眾拉回來,甚至更高一層次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讓他們也見識一下我們的文化傳播。#p#分頁標題#e# 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影視創作上的吸引力和市場前景 當我們一面想看《功夫熊貓》系列影片一面卻又害怕被文化殖民時,我們缺少的正是在影視產品(如電視劇、電影、動漫等)創作上的自信,這種自信的缺乏是由國產作品的長期劣質所累積起來的。《功夫熊貓》系列影片可以說是用中國文化完美地制作了一件精致的外衣,套上這件外衣,這兩部好萊塢大片就能迅速獲得票房和口碑上的雙豐收,美國文化的普世精神也就自然獲得了觀眾的心理認同。在跨文化傳播中,心理認同是一個重要的隘口。拉里•薩默瓦曾經說道:“文化最為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幫助其成員建立他們的認同。”[4]唯有建立了這種認同,受眾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內涵,才能真正達到跨文化傳播的終極目的。然而,我國目前在影視作品制作上,與國外還存在這較大的差距。以近幾年熒屏熱播的動畫片《喜羊羊與灰太狼》為例,雖然這部作品的收視率很高,以此為基礎制作的電影版動畫片票房也讓人滿意,但是從專業角度來看,其與《功夫熊貓》系列影片的差距仍然極大。甚至相比于20世紀40年代上映的《貓和老鼠》,《喜羊羊與灰太狼》無論在制作還是在創意上都難以望其項背,這不能不說是當今中國動畫的悲哀。倘若以這種作品來進行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乃至與各國的動畫電影去競爭,其結果可想而知。 實際上,《功夫熊貓》系列動畫影片在擊敗了國產動畫電影的同時,也為國產動畫指明了出路。暫且不說《功夫熊貓》系列在制作技術上遙遙領先的程度,國產動畫首先要考慮的是對于受眾需求的把握和自身創新意識的覺醒。如今的受眾欣賞水平提高,對于新鮮創意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強烈,一部制作簡單且缺乏創意的《喜羊羊與灰太狼》終究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所以國產動畫電影一定要做好對于受眾需求的市場調查,并以此為基點來進行創作。 作為一個五千年的泱泱大國,我們有深厚的文化積淀,有數不清的神話故事,有不勝枚舉的傳奇形象,還有眾多具有強烈吸引力和神秘色彩的文化元素與符號,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資源,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倘若能夠以這些為基礎,迎合當今電影市場的流行趨勢,再加上新奇的創意和精良的制作,相信中國動畫影片的崛起指日可待。或許到時候我們自己制作的《功夫熊貓》能在美國的院線廣受好評,我們所希望的跨文化傳播也就順理成章地實現了。 羅伯特•舒特曾經指出,跨文化的目標是不斷增加對每個社會及其傳播道德的復雜性的深刻理解。傳播者需要了解和感受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和道德規范,以及規范人類言行的深層的文化信仰和傳播期望。真正的內文化旅行是具有挑戰性的,它讓旅行者置身于陌生的道德和傳播系統之中。傳播者只有通過多樣的內文化旅行,才能獲得跨文化道德的覺悟———它是一種個人意識,即人們對不同于己的道德系統能多大程度的接受。[5]誠然,好萊塢的確為我們提供了兩部極為好看的動畫電影,然而當我們看到屬于自己的傳統文化元素被運用在外國電影之中來進行文化傳播,并且比我們自己的電影還要受歡迎時,我們的心中自然會泛起一絲酸楚,這種感覺正是跨文化傳播的效果體現。體會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明晰自己在影視跨文化傳播領域的責任和擔當。因此,在跨文化傳播的道路上,除了作出自己的《功夫熊貓》,我們別無他路。今天我們是如何通過《功夫熊貓》系列接受了其中內含的文化因子,明天就會如何讓其他文化系統主動地接受我們的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