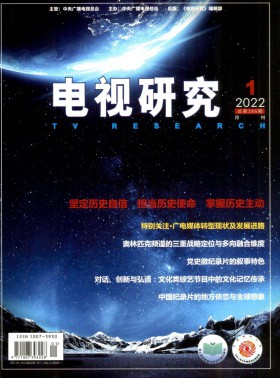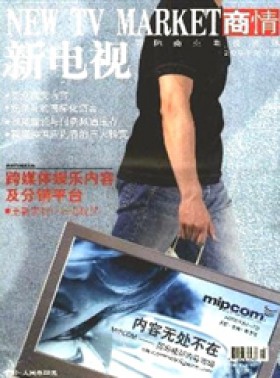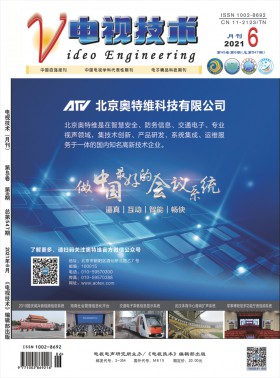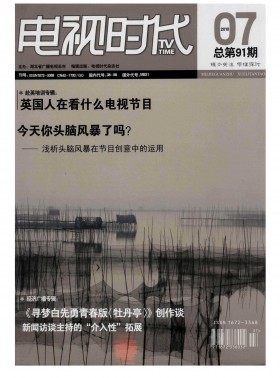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電視文藝與文本傳播探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彭鐵祥 黃春平 單位:懷化學院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近年來,很多過去只為少數人所欣賞的中外名著被改編為電視劇(可以具體界定為電視文藝類),隨著電視走進千家萬戶,讓更多的人們從電視媒體中接觸并加以欣賞,如:《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保爾•柯察金》、《紅與黑》、《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這些文學名著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象其電視劇那樣同時享有如此廣大的觀眾群,并在觀眾中引起如此巨大反響和共鳴。可是另一方面,這類以電視劇為主體的電視文藝傳播卻給文學的文本傳播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麻煩。就此本文加以深入的探討。這里需要說明的兩個概念:本文的電視文藝傳播是指以電視為傳播媒介,以電視劇、電視詩歌、散文、紀錄片與綜藝節目等為主要傳播形式的一種電子傳播。文學文本傳播是指以紙張為傳播媒介,以文學著作、期刊等文學藝術類書籍為傳播形式的一種印刷傳播。
一、90年代電視文藝傳播的興起與文學文本傳播的日趨衰落
隨著電子媒介事業———電視事業的飛速擴張,電視文藝傳播日益興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電視事業獲得高速發展。1980年全國有電視臺38家,到1998年,全國無線、有線電視臺已達740家,而且中央、省級電視臺大多以衛星傳輸方式覆蓋全國。就全國而言,我國電視人口覆蓋超過85%。[1]目前全國約有3億臺電視機,觀眾近9億,電視人口的覆蓋率達到86%,日人均收看電視不少于3小時,人們常收看的節目中,一半以上是各類電視劇。[2]據統計,目前我國電視劇年產量已達6千(部)集,每年還從境外大量引入,其他電視文藝節目(如電視紀實片、電視藝術片、音樂電視、電視詩歌、電視散文、電視綜藝節目)年產量超過10萬小時,電視文藝節目在全部電視節目中占60%以上。[1]電視文藝已成為大眾文藝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人們逐步疏離書刊,把更多時間交給電視和網絡,有相當部分的讀者轉化為觀眾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人們在繁忙緊張的現代生活中,很少一天花2到3個小時來讀文學;但花2到3個小時看電視,卻是當今大部分人的正常休閑方式。與此相對照,20世紀80年代,以報紙、雜志和書籍為代表的文本傳播還扮演著文學的主導型傳播媒介的角色。許多文學期刊發行量都達數十萬份,甚至上百萬份,一部稍有影響的小說印數也可達十萬冊。
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電影和電視等電子媒介在當今媒介網絡中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媒介,原來高踞藝術家族霸主寶座、主要依賴文本傳播的文學,由于遠離核心媒介而不可避免地發生深刻的角色變化。文學藝術類書籍傳播的生存空間正逐步被擠壓著并不斷的縮小。這具體表現在,隨著媒介權力的移位,文學的文本傳播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有人作過統計,在1952—1966年間,文學藝術類書籍在我國當時的出版圖書總量所占比例為27.6%,1979年為12.2%,1985年為8.6%,1994年僅占3.3%。[3]1995年一份關于上海作家現狀的調查,統計數字最明確不過地反映了文本傳播的變化:王安憶,80年代初作品印數幾萬冊,現在只有幾千冊;陸星兒,原來作品印數七八萬冊,現在也只有幾千冊。《收獲》在80年代中期以前發行最高達百萬份,現在2萬份;《上海文學》原來發行量40萬份,現在2萬份。[4]據《羊城晚報》1998年10月5日消息,“每種文學期刊只有十個讀者”!消息來自1998全國大型文學期刊主編(社長)研討會,部分代表說,“《漓江》停刊,《昆侖》停刊,《小說》即將停刊,下面是不是輪到我們停?”消息還引《福建文學》主編黃文山介紹,目前全國共有800多種文學期刊,平均每種期刊發行3000冊,每種期刊平均大約有10個讀者。而且,這個數量還在萎縮。①通過以上的對照我們似乎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90年代以來文學的文本傳播單從發行數量上看正呈現出日趨下降的態勢,而電視文藝傳播則隨著電子媒介事業特別是電視事業的興起正贏得越來越多的觀眾。為什么會呈現這樣一種態勢?它們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內在關聯?
二、文學文本傳播衰落的原因分析
文學文本傳播的衰落,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撇開其他方面的原因,單從媒介發展的角度來解析,可以發現,電視、電影等現代電子傳媒變文學的文本傳播為“電子傳播”,這似乎是導致文學文本傳播的衰落(主要表現為文學藝術類書籍發行數量所占比例的不斷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種傳播載體發生重大改變的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子媒介傳播的代表———電視文藝的迅猛發展及其對大眾文藝消費的霸權式占有。如購買書籍期刊需要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而看電視文藝則除了讓你耗費點時間看廣告之外,無須在經濟方面有所付出。這恐怕是大眾群體選擇電視文藝的首要因素。這是最基本的經濟方面的原因決定了受眾如此的抉擇。除此之外,印刷媒介傳播(文本傳播)的局限與電子媒介(電視)傳播的優勢發展,似乎是形成文學文本傳播急劇衰落的一個必然的原因。具體的說,電視對文學的傳播相對文本傳播而言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傳播優勢:
(一)電視傳播的主動性與文本傳播的被動性有人把電子媒介中的電視稱為“闖入型媒介”,當家家都把電視機作為必不可少的現代生活用品時,您只要打開電視,那些利于大眾接受的、極富自然真實感而又極盡煽情誘惑之能事的電視畫面,便闖入您的視野;而面對這樣直觀具體的信息誘惑,人們是非常愿意打開電視機的。無論在私人場所還是公共場所,電視都會迎面而來。一旦電視開關被打開,它就會將電視節目展現在人們面前,不顧人們的喜好和需要,帶著強迫式的力量將那些電子圖象和語音信息灌入人們的視覺和聽覺器官里。從這種意義上說,電視是一種主動性的媒體。當它載著文學名著改編的電視劇走進千家萬戶時,所有的觀眾幾乎是無條件地接受了它所提供的節目。它所占據的觀眾是難以計數的。文本傳播則并非如此。文本是一種客觀的、被動的存在物體,它必須被購買或借閱。讀者需要去書店或圖書館,在眾多書籍中做出選擇。選擇會受到個人興趣、文學水平以及書本價格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和約束。作為一種被選擇的媒體,文本是被動性的。在電子媒介的傳播優勢飛速發展的今天,普通民眾對文本的選擇,常常是在“不得不”的情況下才勉為其難的。這樣,文本傳播的非“闖入”性和“不得不”才被選擇的現狀,其傳播局限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決定了它的讀者數量和范圍的有限。如電影《秋菊打官司》。陳源斌的中篇小說《萬家訴訟》社會反響并不很大,但借助電子媒介的直觀具體的傳播,尤其是后來熒屏的多次復播,秋菊這個形象卻走入千百萬普通民眾的期待視野,成為90年代的一個大眾話題。#p#分頁標題#e#
(二)電視傳播的易解性與文本傳播的難讀性觀看電視是一個解碼過程。電視信碼是一種用來產生光和聲的電子信號,通常只有一種解碼度,相對于文字解碼要簡單得多。理解電視圖像遠比理解書本印刷的文學作品中的語言容易得多,電視觀眾只須被動地接受屏幕上提供的信息,將所聽到和看到的結果組合在一起。屏幕上創造的結果是名著改編者所設定的成品,人物、音樂、風光、眼淚與歡笑、幸福與悲哀都呈現在屏幕上,不需要觀眾的再創作,觀眾的各種感官只是在被動地接受、欣賞和感覺著已有的一切。因此,屏幕上的人物會吸引眾多的、不同層次的觀眾,如年老的、年少的,男性的、女性的,有文化和無文化的等。在文本傳播中,文字是人們理解內容的唯一媒介,要求讀者有一定的識字、理解和欣賞能力,即較強的文字解碼能力。有統計表明,一個人要求學會5千個符號才能達到基礎文化水平,掌握2萬個符號才算達到學術水平。這樣就無形中限制了接觸這種媒體的人數,將一大部分人排斥在外,少年兒童、無文化者等都不得不遠離該媒體所提供的文學欣賞園地。以《水滸傳》為例,其簡寫本有96萬字。其中有許多語言仍以原著的風格保留著,例如,“老虎”被稱作“大蟲”等。它的讀者群只局限于有一定文化素質、文學修養并對古典文學感興趣的人群。當該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第一頻道的黃金時段播出后,這個故事在同一時間里走進9億中國人的視野中。據估計當時的收視率是44%,在收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般來說15%的收視率就被認為高收視率。而《水滸傳》的小說本一共出售過五千萬本。[5]在文本傳播的環境中,人們不容易打破行業領域界線,在讀者群之間也會有比較明顯的界線。如中外名著、古今名著都存在著明顯的讀者群差異。電視媒體則因易解性很容易打破了老少、男女、中外的界限。
(三)電視傳播的娛樂性與文本傳播的單調性電視媒體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娛樂性。而其娛樂性又是通過其表現手段和調用感官的多樣性實現的。電視劇中的人物通過手勢、聲音、動作等來表現心理活動、故事情節等,聲音的語調、面部表情等可以讓觀眾感覺到人物的感情以及為何作出反映。另外,電視的綜合技術,如:攝影、音樂、舞臺效果、背景、服裝、道具、化妝等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增添電視劇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人們欣賞它能帶來全方位上的感官娛樂。文本傳播中只能通過文字或極少量的圖畫來表達各種內容,表現形式顯得非常單調,根本沒有電視那么多的表現手段,而語言符號又是抽象的,只能通過視覺來感受,所以受眾的感官調用也非常單調,遠不如電視的綜合技術給觀眾產生的效果強烈和深刻。
(四)電視傳播的快捷性與文本傳播的緩時性。電視由于使用了多種表現手段,文本傳播中需要幾千字來描述的一個情節,在屏幕上只需幾秒的時間,并且還能給觀眾更生動和更直觀的畫面。它是一種快餐文化,大眾文化。這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簡直可以說完全一致。人類的生活,就既在時間之中又在空間之中。它雖然也要展示事物發展的過程,但在每一幅畫面中,它把許多事物共時地呈現在觀眾的面前。同一幅畫面上的山川河流,好人壞人,如果在文學中,要一項項一個個地逐一介紹,影視則是讓一個鏡頭入一眼就看到了。文學是時間性的,它的接受是通過一個字一個字的掃瞄完成的。從接受效率上說,電視遠遠超過了文學。電視的瞬間性抹平了文學文本中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如一部長篇小說我們可能讀一到兩個星期,但看電視我們幾十個小時也就夠了。電視的誕生把一種集閱讀(文化精品)、觀賞和獲得審美快感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帶到現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學專業的讀者/觀眾只需花上一二個小時的時間就讀/看完了一部濃縮了的長達數百頁的文學名著,并且能獲得感官和視覺上的巨大享受。
綜上所述,電視對文學的傳播相對文本傳播而言,有很多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是文本傳播永遠無法實現的。而以最小的成本和代價獲得最多的愉悅和利益是每個人的生理本能。所以對普通的大眾來說,在電視文藝傳播與文本傳播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自然會傾向于前者。盡管文本受眾與影視受眾是不一樣的(文本文化是一種精英文化,受眾有限,利潤有限。影視文化是一種大眾文化,受眾數量最大化,利潤也最大化。而現在的文化發展方向正從精英主導(權威主義)轉向大眾主導(民主主義)),他們并非是完全重合的同心圈。但如果前面的分析不容否定的話,那么文學文本傳播的衰落似乎是一種由正在興起的電視文藝傳播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三、文學文本傳播衰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電子媒介———電視憑借獨特的傳播優勢,將孤傲的文學女神請到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男女老少面前,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給文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這些男女老少極盡喜怒哀樂之情。實現了文學傳播的大眾享有權。單從這一點來說,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從傳播學的另一角度看,其消極影響卻不容忽視:
首先,就文學的傳播媒介而言,其圖像傳播得到了空前的擴張,以文本為主體的文字傳播正因此而緊縮。文學文本是以文字的形態呈現的。而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傳媒及其文化則是以“圖像”的形態存在并呈現的。“文字文化”的符號抽象,直接訴諸于思維。“圖像文化”的符號直觀,直接訴諸于視聽。圖象文化消除了受眾在條件上的限制,他們可以文化低、識字少,也不需要專門的修養,這樣其受眾隊伍便擴大、膨脹了。如此一來勢必影響到“文字文化”的文學受眾的銳減與其注意力的迅速轉移。現在流行的不是去“讀”而是去“看”。讀的人少了,看的人多了。曾有西方學者預言:文字文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進程已經開始;“文學”這一概念最終甚至可能徹底消亡。姑且不論預言的準確與否,但由電視帶來的圖像文化的強大存在及其不可估量的發展前景無疑是不容樂觀的。文字傳播正在失去其陣地。其后果我們在下面將會討論到。
其次,就傳播中的受眾而言,受眾的個性和自由正隨著圖像產品的“標準化”而被銷蝕。一方面,文學創作一直是以個人化為特征的。個人化包含個人創作與作品的個性化兩個層面的含義。正因為如此,其“成品”在藝術上有不可取代與不可低估的價值。另外文本的解讀是一個繁重的參與過程,需要付出一定的心理和生理勞動,它不僅需求讀者來解讀語言,理解其含義,也要求讀者通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來構建作品中的人物、行為和情感等。讀者也是一個作品中人物的再創作者,他也有個性。相反,電視則受廣告利潤的驅動,盡管傳輸的是文學的內容,但卻進行的是“標準化”的生產,它可能受到一項集體的、權力的、利潤支配,其產品便可能成為缺乏獨立聲音、個性特色、精神價值、滲透政治意識、包藏利潤目的的“標準化”消費品。更具威脅與欺騙性的是它以貌似民主的、大眾的迎合面目出現,假傳媒難以拒斥的特點控制了受眾幾乎全部的閑暇時光,并以此方式在不知不覺中控制、支配了大眾的思想與心理。德國哲學家威爾什正確的指出:在媒介時代,我們從電視形象中接受的刺激越是豐富,越是強烈,我們對這些視覺形象的感知越是麻木和無動于衷。[6]還有學者認為,“電視所提供的是一種文化快餐,是事先已經消化過的文化糧食,提供預先已形成的思想。”[7]由此可見電視傳播對受眾個性化欣賞的嚴重銷蝕。隨著電視文藝作品進一步的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潛移默化中的受眾在快樂中被納入了商業化的消費體系。他們心情愉快地解開了錢袋,不知不覺中放棄了個性與精神。一代人(又一代人)將在電視文化浸淫中鑄成價值可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根本無創造性可言。#p#分頁標題#e#
另一方面,受眾在電視的“強迫性”中又失去了文學文本傳播中的選擇自由。在文本傳播中,受眾面對的是一個又一個各自獨立的個性化文本,他可以選擇此而放棄彼。他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空間,樂意的在任何時間任何處所閱讀或反復閱讀隨身攜帶的任何一種文學讀本。他可以細讀,可以瀏覽,也可以隨意檢閱其中的某個章節,可以慢慢思考。簡言之,他是自主的。他有對文學文本的選擇權、支配權、過濾權。但電視則不同。電視是以“強迫性”對待它的受眾的。受眾無法自主地選擇“節目”,沒有時間的支配權,必須依據它的時間表作息。沒有空間的支配權,必須坐在室內的一臺電視機前(人人可提在手中的微型電視在其實際意義上為時遙遠)和人共賞。即使面對很敏感的鏡頭,也不能有自己的隱私。沒有過濾權。你不能把自己愿意看到的保留下來(你雖可以節錄、回放,但由于手段的制約,你便無面對一本書的自由)、把不愿意看到的部分“翻揭”過去。由于電視文化對于時空的高度占有,其“強迫性”使受眾在事實上難以發現,發現后又難以拒絕。其結果是,受眾不再作為自覺的主體存在而成為電視文化的奴隸。眼下眾多文學讀者紛紛放棄了文學文本享有的“自主性”,幾乎是“自愿地”接受了“強迫性”的電視屏幕。
再次,就傳播的內容而言,文學文本傳播的高雅正被圖像傳播的煽情與俗氣所吞蝕。我們知道,文學文本內容的接收必須要有相對的文化教育水平,而電視類圖像的欣賞則對此要求不高。文本傳播雖然也能復制(通過大量的印刷發行實現),也有著商業的目標因素在里面,但就其傳播的內容而言,其對商業性的追求并不如電子傳播那樣明顯。現在很多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子版本后,很大程度上都有違原作的初衷。“戲說”成風。很多內容都加進了煽情的成分,人物故事變得庸俗不堪。之所以這樣做,圖的就是“賣點”。只有賣點,才會有滾滾的利潤(如主要表現在影碟的復制率大量的提升,影視節目的廣告收入飆升)。這樣的話,高雅的文學文本傳播終因電子技術的革命,其內容最后被媒介消費主義浪潮所顛覆。在利潤面前,高雅不復存在,商業賣點正成為文學內容能否取得電子傳播青睞的關鍵性因素。所以盡管圖像(電子)傳播能夠實現文學的普世化,但文學在傳播的過程中卻以內容由高雅走向低俗煽情為代價而告終。
總之,盡管電視文藝在很大程度上給文學文本傳播帶來了很多的不良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學文本傳播的式微,但電視與文本傳播在表現文學作品時各有特色,兩種媒體始終是難以相互取代的。無論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視劇多么成功,文學作品中的語言魅力是無窮的,對語言的欣賞永遠給人們帶來電視無法帶來的愉悅。這種精英文化與文化精髓永遠是電視文藝取代不了的。因此在這里我們也無須為文學文本傳播的式微而擔憂,更無需為此提出什么對策。因為文學的這兩種傳播方式都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式微與興隆最多只是其傳播方式的一種重新洗牌,二者所占分量在新的媒介技術時代的一個調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