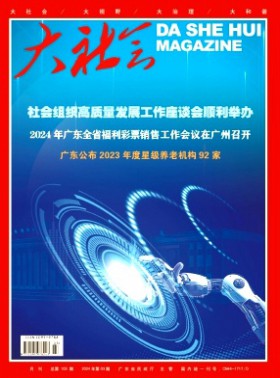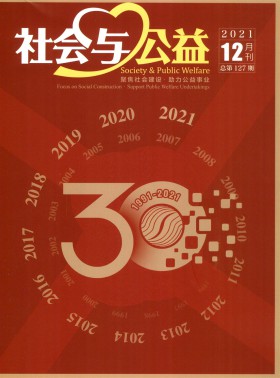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社會民俗學論文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民俗學百年歌謠思索
本文作者:黃丹莉 黎亮 單位:宜春市第三中學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
歌謠研究的最初動因
《歌謠周刊》第一期發刊詞闡述了歌謠收集的目的:“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地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GuidoVital)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謠征集活動第一個目的即是學術的目的,主要是將民間歌謠作為民俗學研究的資料。而民俗學研究本身也有其社會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為改造社會一方面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去民間尋找國民的心聲。中國20世紀初改造國民性的時代風聲構成了歌謠收集的真正歷史動因。第二個關于文藝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謠研究運動的刺激和影響。雖然文人編纂整理前代歌謠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雜歌謠詞》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謠諺一百二十余則。
以后歷代都有編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豐富,而清代杜文瀾《古謠諺》則被認為是繼《樂府詩集》之后最好的選本。北大歌謠征集活動卻與傳統的歌謠編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對近世歌謠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為新詩創作提供啟示和借鑒。為文藝的目的與黃遵憲“詩界革命”引民間歌謠入詩一脈相承。但直接的沖擊恐怕還是受外國影響。英國1878年成立的民俗學會專去采集英格蘭島以及歐洲大陸的傳說故事、歌謠、風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紹的歌謠理論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編的《北京歌謠》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詩歌可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詩歌”,周作人提出“為文藝“的口號受到外域研究的沖擊不可忽視。爭議問題:為學術還是為文藝研究工作的重點是民歌的社會科學還是文學方面曾經有過明顯的躊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會議上提出除搜集民間散文和韻文之外,還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謠周刊》里出現了許多關于結婚、節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時,胡適在《復刊詞》中說:“我以為歌謠的收集與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民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為文藝的結果呢?也有爭論,有人懷疑“已經搜集到的許多歌謠和故事,對于民族的純文學(詩歌、小說、戲劇)的復興究竟會有什么益處。”魯迅也曾經說,文人的文學僵死了,就從民間去尋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絞死。
值得思考的是:這個為文藝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為什么民族的詩歌遲遲沒有出現。為文藝和為學術其實可以囊括在新文化運動改造國民性的需要這個最大的歷史動因之下,為改造國民性去民間尋找民情和民文藝,就是從內部完成啟蒙的努力。這個動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黃遵憲、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救亡運動。我們怎么來理解這個新文化運動中的國民性改造運動,我們如何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切身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問題這同樣很重要。且不論歌謠運動最后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歌謠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確立,后來歌謠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從中生發。
研究方法的開拓與傳承
田野調查。歌謠研究是在歌謠征集活動(1918)中開始的,這為中國歌謠研究奠定了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歌謠研究會(1920年2月)與風俗調查會(1923年5月)組織的田野調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謠達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首。風俗調查會所列風俗調查表將歌謠放在“思想”一欄中,與環境、習慣兩個大項并列,可以說為歌謠研究打開了視野。遺憾的是,此表沒有注意歌謠在什么時間、場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參與者的反應。歌謠的曲調也沒有保留下來。不過這些遺憾在后來的研究論文中稍稍得以彌補。比如孟森在《有關山歌的史料》中,講到他家鄉每年七月最后一個晚上的歌謠比賽。隨筆中涉及杵歌,說明了是舂米時唱的歌,甚至在葬禮中也唱。比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進一言》中提到“在每一個省,有時甚至是鄰近地區,對同一首歌卻有不同唱法。”胡適在《民歌比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題”和“細節”兩個重要的比較研究概念。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則在收集異文的基礎上具體展開了歌謠母題的比較研究,并發現水路和陸路傳播的效果與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結合法:周作人在《歌謠周刊》16號上提出了歌謠研究文藝的和歷史的兩個方面。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價值時,他寫道“其資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謠,但舊的也一樣重要”。文史結合法在張競生擬定的風俗調查表中有所體現,表中所列將實地調查、記載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參。此法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將考古、史料、風俗歌謠一視同仁地對待,進一步鞏固了歌謠的國學地位。
音樂文獻學下花兒研究
摘要:本論文以中國知識期刊網自1979年至2018年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獻內容為分析對象,從音樂文獻學的視角出發,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花兒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呈示。從數量看2001年是分水嶺,數量比之前陡增十倍;從內容看,花兒研究動向與國家大政方針密切相關,也體現出音樂文獻學對花兒研究方法的導引價值。
關鍵詞:音樂文獻學;花兒歌種;發展趨勢
“文獻”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對學生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是現存資料關于“文獻”一詞的最早記載,也是孔子感慨文獻不足而無法深入去考證夏商之禮。各個領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獻的支撐使很多領域的研究都處于滯后甚至空白狀態,文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音樂文獻學在音樂領域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音樂文獻學也是20世紀80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音樂文獻學是通過對音樂文獻的研究,揭示音樂形態變化、社會流傳和發展規律,并為音樂文獻的使用提供理論依據的一門較新的學科。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需求,音樂文獻學本體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產生于明代的花兒作為廣泛存在于我國西北地區的音樂形式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于花兒的研究近年也越來越得到學界專家的重視。
一、1979年—1989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檢索到有關花兒研究內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異明顯,以普通刊物為主。(一)文章研究的對象花兒音樂分析、花兒演唱、創作的花兒劇、花兒音樂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兒的相互關系、花兒的歷史形成以及花兒音樂審美等方面。(二)文章的敘述內容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花兒、花兒會的民間傳說、口頭故事等進行介紹;從文學的角度對花兒歌詞的語法、方言、詞式結構等進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學術身份1.花兒演唱名家有朱仲祿、蘇平等,他們對花兒音樂的類別、音樂表現和演唱技藝等進行了介紹。2.高校民俗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者有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柯楊。他在1980年與雪犁合編《花兒選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叢》第3期發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顆明珠——甘肅蓮花山花兒漫記》,把花兒音樂介紹到了海外。此外,還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錫文、魏泉鳴等學者。3.專業音樂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喬建中于1987年在《中國音樂學》發表《甘肅、青海花兒會采訪報告》一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花兒音樂的形態從音樂材料的分析到其歷史成因和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這一時期總的來說,對花兒的研究還是以文學性研究為主,對花兒的曲令音調的研究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這十年內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章為106篇,這一時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核心期刊中有關花兒的研究比上一時期明顯提升。1.民俗學、文學角度的研究,從介紹、描述型發展到較深層次的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系統研究。如柯楊于1997年發表在《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的《花兒會——甘肅民間詩與歌的狂歡》一文。2.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杜亞雄1997在《民間文學論壇》發表的《“洮岷花兒”與生殖崇拜》已經涉及社會學方面的問題。3.文章研究涉及的內容與前一個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結構上有了一定的調整,花兒研究中音樂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學性研究向音樂性研究傾斜。
國內猴文化研究
摘要:中國國內研究者從人類學、文學、語言學、藝術、民俗學等視角對日本猴文化進行了多元闡釋,積累了可資借鑒的前期成果,但是相關研究在質和量上仍有拓展的余地,系統性研究闕如。
關鍵詞:日本;猴文化;綜述
20世紀末至今,國內對日本猴文化的研究總體呈現發展之勢,雖體量不大,但研究視角多樣。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人類學、文學、語言學、藝術、民俗學等角度開展研究,從多個側面闡釋日本猴文化內涵,發表了許多有益的研究成果。誠然,在日本文化研究領域,猴文化研究在數量和質量上尚存巨大的研究空間,并且系統性研究闕如。本文將目前國內日本猴文化研究成果綜述如下,希望對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有所貢獻。
1人類學視角
張沐陽1(2019)以著名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著重體現“物”的象征意義的四部著作為依據,梳理了大貫的歷史象征主義。通過分析大貫的著作《猴子作為鏡子:日本歷史與神話中的象征性轉變》(MonkeyasMirror:SymbolicTransformationsinJapaneseHistoryandRitual),指出大貫在這本書中更深層次地理解了猴子象征意義的變化及與社會背景之間的邏輯關系。書中寫到,在古代日本,因為“比克猿”與太陽女神的神話故事以及作為山神的使者的傳說,猴被認為具有神圣性。之后,受猴子是“少三部分毛發的人”這句傳言的影響,猴子被認為試圖打破人與動物的邊界,被認為是人的“替身”而遭到歧視,代表了不受歡迎的人。在當代,猴子一方面作為日本“現代”和“進步”的代表出現在旅游紀念品上,另一方面出于滿足人高于動物的心理設想,以及回應當時日本社會分層中的原則,猴戲從中世紀的祛除人身上不祥之氣的儀式性表演變為小丑表演。猴形象從古到今的轉變,展現出日本文化中自我和他者概念的轉變過程,從中可以看出日本社會思維結構的變化。張沐陽評論說,這本書中,大貫對于猴象征意義的變化的論述具有濃厚的歷史人類學色彩,偏重于史料收集和敘述。大貫將結構主義分析與日本民間傳說和文化分析相結合的嘗試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大貫強調歷史過程中社會環境動態變化對猴象征意義變遷的影響。
2文學、語言學、藝術視角
2.1民間文學
民族民間民俗群眾文化藝術發展
摘要:
近年來一些人士對我國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與群眾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探究。而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不但可以從根本促進群眾文化的進程,同時還對社會的全面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傳承;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群眾文化
群眾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要素,群眾文化建設的進程是加速社會文化傳播及發展的主要路徑,同時對群眾的精神文化也能夠有較大的促進。特別是民族民間民俗文化,在傳承環節其自身具有顯著的民族歷史文化特性,合理的與當代群眾文化建設相結合,能夠推動我國文化特色全面進程,可以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
一、群眾文化建設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的基本功能
目前群眾文化建設的全面進程已獲得廣大群眾的認可,群眾文化本身就是對以往文化藝術的傳承,不管在文化藝術的構架以及類型上,都能夠利用群眾活動去全面開展,進而去完成創新。從國內現階段一些以常規形式傳承的傳統文化活動我們可以觀察到,就算經過一定時間,一些文化活動在特性依然沒有改變以往的風貌,比如國內一些地方所開展的賽龍舟就是典型的文化承遞。同時還有一些民族傳統佳節在歷史過程中已變成被大眾所接納的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但可以體現我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向全世界彰顯了華夏文明豐盈的文化底蘊。就用戶縣農民畫為例子,其發展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戶縣農民畫結合了傳統美術的一些藝術形式,讓農民畫煥然一新,在國際上也享有盛名,同時被一些學者所贊揚。因此我們要將傳統文化藝術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的展現給世人,不僅要進行傳承及保護,同時還要側重于對傳統文化的創新,要將它融入到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環節之中。從群眾文化特性視角來看,其有較為顯著的唯一性、區域性以及民族性,這種特性在持續的發展中表現的非常明顯。物質文化可以為群眾活動的構建奠定路基,而制度文化被視為兩者間的介質,可以把群眾的相關規范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行有機的結合。在歷史文化的持續發展的浪潮,群眾文化構建活動只有和常規的傳統民族文化適應,才能夠得以長久的生存及發展,在傳承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時代背景,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確保與當下的社會背景相適應。
室內設計教學創新路徑
一、高職室內設計專業教學改革的思路
室內設計專業與建筑裝修行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建筑裝修市場需要一高多能的人才,高職室內設計教育應以此為人才培養目標。一高是指室內設計專業人才需要在掌握計算機、建筑裝潢、工藝美學等多方面技能的基礎上尤為精通某一項技能;多能是指室內設計專業人才需要較高的審美能力、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良好的身體素質等。針對這一人才培養目標,高職室內設計專業教學改革的思路為:在培養室內設計專業人才的過程中,應把學生、教師、實訓、學院、教學質量五個方面結合在一起,根據市場的實際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專業人才,市場需要什么就讓學生學什么,確保學生在畢業之后能夠適應社會需要,順利上崗。在教學設施方面,數量上應該滿足學生需要,質量上應該最大限度地反映室內設計專業的最新技術。在師資隊伍方面,教師應該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和過硬的實踐技能。最重要的是,高職院校應實現產學研結合的教學機制,提供充足的時間和設施滿足學生的實踐需求,提供校內實訓基地和企業實訓場所供學生實踐操作。另外,室內設計專業教育必須打破學科界限,本著實際、實用、實效、實踐的原則,精心挑選教學內容培養一高多能的專業性人才。由此可知,在高職室內設計專業教學改革中,應以提高學生的專業素質和實踐能力為主線,在此基礎上完善課程設置、改變教學理念、強化師資隊伍、增添教學設施。
二、高職室內設計專業教學改革的實施途徑
1.明確教學目標
只有明確教學目標才能進一步確定教學模式,進而確定教學內容。高職室內設計教育培養的是一高多能的專業性人才,這一目標指引著后續的教學活動。高職室內設計專業教學目標主要培養學生的設計思維、設計能力、想象力和藝術素養,以適應該行業的需求和發展。
2.合理設置教學內容
教師在設置高職室內設計專業的課程內容時,應多介紹美學、建筑學、力學、民俗學等相關知識,注重突出重點。對學生的審美能力和敬業精神的培養同樣不可忽視。只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達到一高多能的人才培養目標。
射箭文化研究
摘要:蒙古族射箭活動是其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射箭活動起源于狩獵生產,在文化傳承以及民族性格塑造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并且其技藝傳承也是民族教育的組成部分,與中原漢地的射藝有異曲同工的功效。蒙古族傳統射箭文化研究是把民族體育這種物質與精神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文化整體加以研究,在外部研究蒙古族傳統射箭文化與社會現狀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內部研究蒙古族傳統射箭文化的現狀,各民族射箭文化的異同,射箭文化的社會功能,射箭文化的心理積淀,及其射箭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的揚棄和繼承、創新與發展,讓其在新時揮更好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和育人價值。
關鍵詞:蒙古族;射箭文化;民族傳統
蒙古族是中國北方最為重要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入主中原,建立了疆域最為遼闊的元朝,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對于蒙古族的歷史、文化、民俗等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的熱點。因為蒙古族驍勇尚武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所以體育運動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騎馬、射箭和摔跤為特色的“男兒三技(藝)”是蒙古族傳統的體育項目,所以關于蒙古族傳統射箭文化的研究是整個蒙古學的一個分支,雖然也有相關研究,但多支零破碎未成系統。總體來看,蒙古族傳統射箭文化的相關研究大多還是在蒙古族民俗研究中被談及,如或作為研究蒙古族男兒三藝(技)之一的一個分支內容,或作為那達慕盛會中的一個競技項目,或作為整個蒙古族體育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沒有突顯射箭文化自身的專業性研究。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偏重蒙古族騎射運動的研究,蒙古族射箭文化分靜態射箭和動態射箭兩種,其中動態射箭就是所謂的騎射,是配合騎馬運動的綜合性運動項目,所以騎射只是射箭運動的一部分,而未能全面展現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射箭文化在蒙古族傳統文化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其研究也有著深厚的基礎和前期成果,值得學界作以總結和歸納,以促進蒙古族射箭文化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那達慕大會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那達慕是蒙古族歷史悠久的體育盛會,射箭則是該盛會中最為重要的一項體育競技活動,因此對蒙古族射箭運動的相關研究早期多出現在對那達慕大會的研究中,作為蒙古族傳統盛會相關內容的一個環節予以展開。如特木爾吉如何、阿榮著的《那達慕(蒙文)》[1],蒙文寫就,認為錫林郭勒盟的那達慕最具代表性,作為蒙古族人民喜愛的一種傳統體育活動形式介紹了那達慕的相關情況,其中談及了射箭運動。相類似的著作還有那恩和確吉的《蒙古族那達慕(蒙文版)》[2]、德力格爾的《草原那達慕》[3]及賈瑞光的《那達慕文化變遷研究——以黑龍江省杜爾伯特那達慕為例》[4]等。相關論文最為豐富,如榮•蘇赫的《蒙古族男子三項那達慕歌》[5]、納古單夫的《蒙古族“那達慕”文化考》[6]、趙永銑、巴圖的《那達慕文化的由來與流傳》[7]、蘇葉和劉志民等的《蒙古國那達慕的起源與發展》[8]等。上述這些研究無不是將蒙古族射箭運動作為大會活動主題之一予以討論,而不是對蒙古族射箭運動的專項研究。那達慕作為蒙古族體育活動最為重要的展示和競技賽會,當然無可厚非地成為研究蒙古族文化傳承和展現的對象。射箭活動僅是那慕達大會其中的部分內容,因此基于那慕達大會的研究,并不能展現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
二、中國射箭運動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射箭運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悠久,并不僅僅是蒙古族特有的運動和傳統,包括漢民族在內的許多民族都有射箭、游藝、訓練等傳統,所以很多在對中國體育運動或者射箭運動的整體研究中都談及和旁涉了蒙古族的射箭運動傳統。如馬庸編著的《銀箭紅心攀高峰:談談新中國的射箭運動》[9]是較早研究民族傳統射箭運動對新中國射箭運動的作用和推進的著作;也有專門從競技體育角度展開的研究專著,如孟繁愛、董文瑾、朱萍編著的《射箭》[10]、茹秀英的《射箭》[11];還有從體育史角度出發展開的研究,如劉秉果的《中國古代體育史話》[12]、王俊奇的《遼夏金元體育文化史》[13]、羅時銘的《傳統射箭史話》[14]等。相關論文也非常豐富,如劉世明的《射箭述略》[15]、劉丹婷的《元明清射箭文化研究》[16]、房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射習俗》[17]、孟林盛的《晉北射箭文化溯源》[18]、余曉慧的《論古代軍事射箭對體育發展的促進》[19]、李培金和欒彥茹的《中國傳統射箭運動器材發展的現狀調查》[20]、佘麗容和樊永安的《傳統射箭復興中的民族主義》[21]等。上述學者研究的視域較大,基本都是站在中國體育運動史或射箭運動整體研究的角度,所以蒙古族射箭只能是其研究中占很小比重的一部分。在整個中國體育文化和射箭文化的研究中,蒙古族因其民族傳統保留較好,所以其射箭活動至今仍是活態民族文化,因此,其在整個中國傳統射箭文化的研究中意義極為重大,成為中華體育文化的重要一環。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研究3篇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篇1
文化強國戰略是我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只有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才能激發全民族的文化活力與文化創造動力。為此,要建設文化強國戰略,把握文化發展規律,以此來增強我國的軟實力,以及民族號召力、凝聚力、感召力,激發文化創新活力,樹立文化自信。在文化全球化視角下,文化強國就是與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創新力,還是競爭力和傳播力,都遙遙領先的國家。然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表現形式,也是一種特殊的傳統文化形態[1]。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首次確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專業,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和發展命運,依靠文化自信,發揮了民族文化特征,實現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新時期下的傳承和發展。
1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體現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我國上下幾千年發展過程中所有體育活動的延伸,是歷史留給現代人的寶貴文化財富,能體現出濃厚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自信[2]。社會文化與人們的實際生活息息相關,是由基層群眾打造,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對社會能產生較為廣泛的影響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自身價值主要來源于社會文化的基本價值,深厚的體育文化底蘊能夠實現我國各地區、各民族對體育文化的深刻交流。
1.1體現科學價值、歷史價值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源遠流長的一種傳統文化,從文化角度來看,傳統體育運動不僅具備民族文化特點,還具備體育文化特點[3]。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現代舉辦,不僅能夠幫助人們全面、真實地了解我國的體育歷史和文化歷史,還能讓人們了解體育的時代性特征和事件性特征。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包含的專業和學科也是眾多的,如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等,每一門學科都能體現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民族體育項目中舞龍舞獅的服裝、端午節賽龍舟項目龍舟的制作方法、民族服裝、工藝品元素,伴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都在不斷創新。也正是人們需求的不斷提升,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科學價值與歷史價值的形成得以實現,為學者的后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
1.2呈現社會價值、經濟價值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考評
作者:姜愛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由此引發的自然生態災害日益嚴重。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把“建設生態文明”明確列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因而“生態文化”越來越成為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名詞,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開始受到眾多領域里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我國世居著5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影響下,通過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生態文化,這些獨特的民族生態智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人與自然的和諧親密關系,有利于尋求解決現階段生態環境問題之路。筆者通過對近10年國內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實反映學界的研究現狀,并為進一步研究該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參考。
一、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涵研究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一詞是隨著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所特有的尊重自然與保護環境的物質技術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及生產生活方式的總和[1](7~8)。傳統生態文化體現在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藝術、倫理道德等多個領域,所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袁國友認為,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認識,也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的經驗性感知,當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態條件下的各民族在謀取物質生活資料時由客觀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主觀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態文化類型和模式”[2]。廖國強、關磊在比較“民族生態文化”與“生態文化”的區別與聯系中,指出了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具體內涵,認為民族生態文化是一種“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態觀的基礎上”,“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3]。
我國55個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態文化內涵豐富、各具特色,許多學者都展開了對不同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容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如廖國強、何明、袁國友系統研究了中國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領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態文化以及樸素而深邃的生態倫理觀[1](19~144)。郭家驥對云南少數民族藏、納西、白、彝、傈僳、普米、獨龍、傣等民族的傳統生態保護文化進行了闡述[4]。王永莉探討了西南地區彝族、藏族、苗族、壯族、羌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內容及特征[5]。一些學者還展開了對某一個特定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內容的詳細深入研究。如劉榮昆從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飾、飲食、傣寨、文學、音樂舞蹈等七個方面,系統研究了傣族的生態文化[6](8~31);葛根高娃詳細解讀了蒙古民族的生態文化[7](14~176);楊紅闡述了摩梭人的生態文化和生態倫理觀[8](60~96);王紫萱系統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態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態文化[10](79~461);等等。學術界普遍按照文化學的分類標準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劃歸為三類:生態物質文化、生態制度文化和生態觀念文化,許多學者都選取了微觀研究范式,具體闡述這三者中某一個維度的內容。
1.傳統物質生態文化研究。物質生態文化意指適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各種生產生活用具、物質生產手段和消費方式等。崔獻勇、海鷹分析了與維吾爾族生存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技能,剖析了維吾爾族的生態物質文化具有適應性、實用性、穩定性等特征[11];廖國強闡述了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刀耕火種農業中蘊含的樸素而深刻的生態智慧[12];戴嘉艷以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一個典型的農耕村落為個案,分析了達斡爾族農業生產中的生態文化[13];梅軍、肖金香分析了黔東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諧的生態觀念、因地制宜的規劃原則、就地取材的節能手段、可持續開發的建筑構造四個方面所體現的科學性及合理性[14]。
2.傳統制度生態文化研究。制度生態文化意指維護生態平衡、保護自然環境的社會機制、社會規約和社會制度,主要包括蘊藏著生態思想的少數民族習慣法、族規家法、古代法等。劉雁翎認為,貴州苗族環境習慣法為保護苗族地區優美的自然環境起到了跨越歷史時空的基礎作用[15];康耀坤認為,西部少數民族環境習慣法文化與西部環境資源保護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內在關系[16];白興發闡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傳統習慣法規范與生態保護的關系[17];奇格、阿拉騰、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討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態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