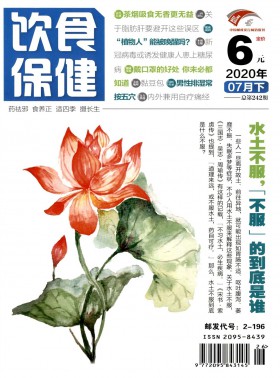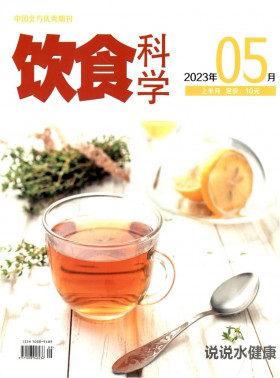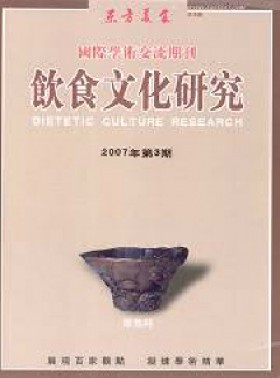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飲食人類學的探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張敦福 單位:上海市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被稱為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除了馬克思對“社會學家”的標簽不感興趣外,他們更極少被成為人類學家。然而,馬克思與查蘇利奇關于俄國農村公社的通信,馬克思描述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形態的《人類學筆記》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都進入過人類學文獻。《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是建立在馬克思有關筆記的基礎之上———是馬克思計劃寫而未能去寫的著作,事實上他的逝世使他壯志難酬;馬克思對人類學的關注,成為他學術研究的中心,直到他生命的終結①。人類學歷史上,懷特(Leslie White)寫了一系列文章,與博厄斯為首的歷史特殊主義論爭,認為社會演化有其普遍規律。懷特還復活了摩爾根的進化論類型學。盡管懷特沒有提到馬克思的名字,但一般認為,懷特理論的調子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強調勞動力和生產資源,懷特則以對能量的控制取而代之,認為后者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②。人類學家閱讀和討論馬克思、恩格斯似乎言之有據。國內學者對這一點也有所認識。陳慶德指出,馬克思理論體系不僅對經濟人類學有認識論上的啟示意義,而且其經濟分析也直接為經濟人類學開辟了學科道路③。陳建憲也注意到,馬克思放棄《資本論》的寫作,轉而閱讀大量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從政治經濟學轉向了文化人類學研究④。羅力群也對文化唯物主義認識論原則、理論原則做了縝密梳理⑤。通過回顧和檢視近百年來的相關重要文獻,筆者試圖突顯和強化以下看法:“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不認為自己是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他們轉向人類學和歷史,與其說是要關心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本身,不如說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他們往人類學那里繞一下彎,就是為了要證明這些概念的靈活性、暫時性和相對性。”①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是人類學唯物主義傳統的理論源泉,尤其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知識與智力的來源,從而成就了在人類飲食研究領域別具一格的研究策略。
一、從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立場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策略
哈里斯研究工作的理論前提是,“人類生活是對其生存實際困境和難題的反應”;他也名副其實地宣稱,“盡管不是我發明創造了‘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但確是我給這個概念賦予了意義”②。他認為,范式(paradigm)是一個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他主張以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取而代之,而這種研究策略有其唯物主義依據。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著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③如果說文化唯物主義有一套相互關聯的理論原則,哈里斯認為,馬克思的這段話富有先見地闡明了這些原則的核心;這一偉大原則是人類知識史上的一個重大進展,其意義和價值與同時代華萊士和達爾文表述的自然選擇原理不相上下。但從現代人類學的角度看,“生產方式”用語具有認識論上的模糊性,對“再生產方式”的疏忽,以及缺乏對主位與客位、行為與思想的區分,都極需要重新給予闡明④。對人口再生產方式中技術和手段的忽略,“未能賦予人口控制的技術發展在文化演化中以中心作用,極大地傷害了經典和新潮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和理論的可信性”⑤。對文化唯物主義研究策略的理論闡明始于客位、主位之分。在哈里斯看來,每一社會必須解決生產問題———在行為上滿足最低限度的生計需要;因此必須有一種客位(etic)行為的生產方式。
其次,每一社會必須在行為上解決再生產問題———避免人口出現破壞性的增長或減少,因此必須有一種客位行為的再生產方式。再其次,每個社會必須處理好一個必要問題,即保證組成社會的各個團體之間、與其他社會之間安全、有序的行為關系……行為的上層建筑是這種普遍反復出現的客位方面的合適標志⑥。主要的客位行為包括以下類別:(1)生產方式:用于擴大或限制基本生計生產的技能和實踐活動,特別是食物和其他形式的能的生產,假使特定的技能與特定的居住地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限制和機會。具體包括生計技能,技術與環境的關系,生態系統,工作模式。(2)再生產方式:用于擴大、限制或保持人口數量的技能和實踐活動。具體包括人口統計及其模式的醫學控制,配偶方式,生育力、出生率、死亡率,育嬰,避孕、墮胎、溺嬰。(3)家庭經濟:在宿營地、住宅和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內組織的基本的生產、交換、消費和再生產。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分工、家庭社會化、家庭紀律與性角色等⑦。其中,生產方式和再生產方式歸入基礎結構,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歸入結構。(4)政治經濟:在群體、村落、酋幫、國家之間的生產、交換、消費和再生產。藝術、音樂、舞蹈、文學、儀式、戶外活動、游戲、業余愛好等被列入行為的上層建筑。
這樣便得到了基礎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的三重方案。與這些客位行為大致相應的一套思想則分別是:(1)生計知識、民族動物學與植物學;(2)親屬關系、種族關系;(3)象征、神話、審美與哲學等①。文化唯物主義對馬克思原則的理論表述可以概括為:客位行為的生產方式和再生產方式,蓋然地決定客位行為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客位行為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又蓋然地決定行為和思想的主位(emic)上層建筑。可以簡潔地稱之為基礎結構決定論原則②。把再生產方式標入基礎結構,就能闡明一套有創見的、首尾一致的可檢驗的重要理論③。文化唯物主義策略還基于扎實的實證研究。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哈里斯就“對主張多實地調查、少閉門造車的研究方法極感興趣”④。他曾在巴西、莫桑比克、印度、厄瓜多爾和紐約等地從事田野工作,以充分的經驗資料和社會事實為依據,證實了他的發現。哈里斯從人口、技術、環境、生育控制等因素著手,檢視了采集狩獵社會前后的社會變遷,其嚴密的論證和有力的事實證實了馬克思的以下兩個著名論斷⑤:“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⑥“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⑦哈里斯反對那種把文化視為純粹主位現象和個體精神、思想活動的看法。對于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哈里斯認為這是一套研究思想、上層建筑的原理,雖然是西歐影響最大的人類學研究策略,但它是反實證的、反辯證的、唯心的和無視歷史的⑧。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內的心理人類學家先驅們提出,人格構型是社會生活中穩定的、經久不變的核心。而文化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則是,基礎結構和結構的根本改變能在極短的時間里導致人格構型的徹底逆轉⑨。認知主義則在主位規則的知識基礎上預測客位行為瑏?瑠,而文化唯物主義的選擇也比弗洛伊德的選擇更為可取?瑏瑡。重要的是,哈里斯通過在各地開展的扎實的田野工作,證實了文化唯物主義策略的說服力,展示了其在多種研究策略中的優勢。#p#分頁標題#e#
二、飲食的奇風異俗:豬肉、昆蟲及其他
人類社會的飲食現象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奇特習俗和傳統。Robert Rowie喜歡收集此類資料,并稱之為人類飲食習慣中“變化無常的非理性事件”。飲食人類學展示給人們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民族中,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人們飲食偏好背后的規范和機制。比如,存在這些飲食禁忌: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不吃豬肉,印度教不吃牛肉,美國人不吃馬肉、山羊肉和狗肉;也有看似怪異的飲食偏好,馬肉是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的美味,大多數地中海沿岸居民喜歡吃山羊肉,蛆蟲和蚱蜢在更多的社會里被當做美食①。問題是,這些飲食的背后有多少營養學的因素?多少遺傳學的因素?多少消化生理學的因素?多少環境生態學的因素?多少區域人口學的因素?多少歷史文化傳統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對差異迥然的飲食習俗,哈里斯贊同“談到口味無爭辯”的文化相對論主張,不應當責難或譏笑不同的飲食習慣和風俗。但依然留下許多值得討論和深思的問題。哈里斯關心的問題是,人類的飲食方式為什么存在這么大的差異?人類學家能否解釋為什么在這種文化而不是別的文化中發現了某些食物的禁忌和偏愛?
哈里斯指出,人類學存在三種解讀方法:文化唯心主義、折中主義和唯物主義。有學者主張,不應當到食物的項目性質中去尋找,而是到人們的基本思維模式中尋找。文化唯心主義者,如列維斯特勞斯認為,自然物種被選擇,不是因為它們是“好吃的”,而是因為它們是“好想的”,另外一些食物則是“不好想的”②。“在道格拉斯看來,人類學家研究飲食方式的主要任務是解碼它們所包含的神秘信息。對古代以色列人的豬禁忌,不必研究自然史、考古學、生態學、豬的營養價值和生產豬的經濟學。折中主義表面上站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立場之間,實際上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對具體的飲食方式個案做唯心主義的解釋。”③。法國人類學家Fischler表達了一種流行的看法:“當我們觀察與人類飲食習慣相關的象征和文化表現時,只能接受如下事實:其持久性和頑固性是任意的原因造成,其中大部分很難講出什么道理來。”④這種論點則顯然流于不可知論。哈里斯的視野總是同更加廣闊的經濟、人口、環境、生態、地理等因素聯系在一起,揭示了飲食禁忌與偏好的“文化之謎”,認為“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決于它們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飽群體的肚子,然后才充實其精神”⑤。
猶太教《舊約》借上帝之口規定不可吃豬肉。1859年醫學發現旋毛病與烹煮不夠的豬肉之間的臨床關聯,被神學家用來為《舊約》食物禁忌辯護。哈里斯把禁忌產生和發生作用的生態環境、自然地理狀況作為考察的重點,得出這樣的結論:中東地區的氣候和生態環境不適合家豬飼養而有利于反芻動物(牛、羊)飼養,古代以色列人迫于成本和收益比較的生存壓力和人口壓力,不得不放棄曾有的養豬生產。現代的歐美人不吃昆蟲,認為它們有細菌、骯臟、令人生厭。事實上,人類的祖先是吃昆蟲的。中世紀以來,歐洲人也吃昆蟲。哈里斯指出,從營養學的角度說,昆蟲幾乎和紅肉、家禽一樣有營養。昆蟲攜帶的細菌可以通過烹煮殺死。回答現代歐美人為什么不吃昆蟲的問題,必須檢驗吃昆蟲或其他小東西的比較成本和效益。他以生態學的最優化覓食理論預測:狩獵者和采集者將只尋覓和收獲相對于“處置時間”(追尋、殺死、運載、烹煮等)能得到最多卡路里回報的物種;只要新項目增加了覓食活動的總效率,該項目就會被添加到他們的食譜中。哈里斯說,歐美人有足夠的牛肉、羊肉、禽類和魚肉,連馬肉都看不上,怎么會需要昆蟲呢?
三、印度圣牛之謎
印度擁有十億人口,需要大量的蛋白質和熱量來維系如此眾多民眾的生命和健康。因為食物不足,印度人口曾普遍遭受饑餓和營養不良①。但同時,印度大量的活牛或將死的牛不被人宰殺為食。吃慣了牛肉的歐美人可能大惑不解,因為看似非常不合理性的情景確實存在:印度人禁止宰殺牛作食物吃掉。國家政策的指導性條文第48款規定:“禁止屠殺母牛和牛犢,以及其他產奶和駝物的動物。”印度有兩個邦通過了“牛保護”法案。因為沒有人宰殺牛肉吃,印度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家畜,即大約1億8千萬頭牛;也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游走于田野、公路、街道上的老弱病殘之牛②。
印度人為何如此保護牛、回避吃牛肉、飼養大量無用的家畜?一個重要的解釋把它歸結為宗教狂熱:這里的主流宗教印度教的核心教義是牛崇拜和牛保護。印度人崇拜他們的母牛(和公牛)為神靈,在家中飼養它們,給它們起名字,同它們說話,用花環和綬帶裝飾它們,容許它們在繁忙的大馬路上信步游走③。母牛還成為政治的象征,母牛和牛犢的圖畫曾被國大黨當作國家的標志④。但是,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都無法解釋:為什么殺牛和食用牛肉成為首選的象征?為什么是牛,而不是豬、馬、駱駝或別的動物?哈里斯指出:“我不懷疑神圣母牛的象征性力量。我所懷疑的是,在一種特殊的動物種類和一種特殊的肉類的象征力量之認定,是出于任意的、隨機的精神選擇,而不是出于一種確定的實際限制。”⑤通過對印度宗教爭斗、農民生活、人口變遷等方面歷史的細致考察,哈里斯發現:印度農業體系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為了吃肉而屠殺了在能量和營養上更有用的動物,而禁止殺、吃牛肉的宗教戒律則有助于該問題的解決。“圣牛(sacred cow)”的宗教及其信仰和觀念畢竟是一定基礎結構(人口壓力、自然環境壓力和技術發展水平等)之上的實現最優化要求而產生、興盛的。由于這種基于歷史資料的研究,哈里斯也顯現出濃厚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旨趣。正如羅力群所說,對圣牛個案的分析,頗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味道,校正了“好吃”的偏頗、謬誤和淺薄⑥。
具體而言,哈里斯所看到的,婆羅門信徒們選擇了一種更富于生產力的農耕體制:強壯有力、肩背上有瘤的大牛能夠在炎熱、干旱和其他不利條件下充當拉犁動物,而它們消耗的飼料很少。由于這些牛很少(像歐美那樣)在人工種植的草場上放牧,也不在人類生產糧食的田地中放牧,所以,幾乎不可能在資源方面與人形成競爭。這些家畜在工作之前處于半饑餓狀態,在犁地的間歇期吃植物的主莖、谷殼、樹葉和家庭的剩飯剩菜。耕作期間,它們吃人類吃不動的棉花籽兒、黃豆和椰子的殘渣壓制的油餅。在印度的大多數地區,用家畜從事糧食生產,每單位的成本收益要比使用(像美國情境下)拖拉機更高一些。它們可以在抗病力強、耐力佳的狀態下工作12年之久。牛糞是印度最大的有機肥料,也是清潔、可靠、無氣味的熱源,缺乏木質和化石燃料的千萬家庭就靠它燒火做飯。母牛比公牛還有清道夫的優勢:麥稈、谷殼、路邊雜草、樹葉和人類不能消化的其他東西都被它吃掉,更不用說它的奶是有價值的副產品了⑦。總之,活牛在印度人的生態環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母牛和公牛是一種成本很低的耕作工具,可以在很多方面替代拖拉機;牛的糞便既可以當作肥料,也可以作燃料;印度的牛以草為飼料,它們不像在美國那樣與人爭奪糧食,這樣它們提供的肥料和燃料就是免費的,而美國則不缺乏木材、石油和煤炭。更為重要的是,只需少量飼料和水,牛就能夠在印度那樣燥熱的氣候條件下存活很長時間。如果為了饑餓的緣故就殺牛,在印度人看來是很不合算、不應該的,因此自然產生了一種“愛牛情結”。總之,印度教的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服從于由生態、政治、經濟和其他的行為和客位的條件所加的種種限制①。#p#分頁標題#e#
四、結語與討論:飲食領域的變遷與挑戰
作為飲食研究的策略之一,文化唯物主義并不諱言自己的缺陷。哈里斯坦誠,文化唯物主義關于新石器生產方式起源的理論仍然是嘗試性的、不完善的。例如,結構主義在這個題目上實際上沒什么可說的,而辯證唯物主義則受害于其“內部矛盾”概念,不亞于文化唯心主義對偉大思想的依賴。馬克思提出的“生產上的束縛”,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并沒有闡明狩獵采集者的轉變。自然和技術,而不是“生產關系”,阻礙了狩獵采集者的生產能力②。在布洛克看來,其一,哈里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點和內容;其二,哈里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持有異議,這點令人困惑不解③。結果,人們只能認為,哈里斯的理論根本談不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色④。也就是說,文化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是有爭議的。但在筆者看來,正如上文展現出來的,哈里斯正是有鑒別、有批評地繼承和發展了唯物主義,而不是機械地照搬和模仿。這種創造性開拓,正是學術進步的源泉。如同《馬克思的外套》一文結語所感慨的,“事物就是人們用來建構生活的用品,如衣服、寢具、家具等補給品,沒有它們就等于毀滅自我。我們何德何能可以藐視物品?誰又有本事藐視得起物品?”⑤回顧和環顧飲食習俗變遷的歷史和當今實際,我們仍然很容易看到,活生生的社會事實是如何支持文化唯物主義的研究策略的。正如已故著名人類學家張光直所確信的:“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它的肚子”⑥;中國人的“飯(grain foods)”和“菜(dishes)”之分,就與其農業生產、生活傳統密切相關。安德森在《中國食物》開篇就談到,中國五大區域(華北、東北、華南、西藏、中東部)在飲食內容、方法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差異,就受制于土壤、氣候、地理環境等難以改變的基礎結構⑦。湘菜、魯菜、川菜、淮揚菜、東北菜等菜系的分野背后,也有著自然環境因素的力量。韓國人在衣著飲食方面崇尚身土不二,絕非后天觀念使然。在這一點上,觀點各異的食物研究者們也頗有共識:“我們是什么人取決于我們選擇什么食物。”⑧飲食研究中文化唯物主義與其他研究視角之間的分野絕非就此消失。哈里斯明確地堅持認為,人類學是科學,像自然科學一樣,科學就必須基于一般規律,而一般規律來自基礎結構。但人類學也有其他發展方向。在普里查德看來,人類學是門人文學科,而不是社會科學。格爾茨則提出,人類學不是實驗科學,而是探尋和解釋意義⑨。不是所有的學者對探尋一般規律感興趣,飲食人類學研究有著多種多樣的研究策略、研究視角、興趣領域和發展方向。筆者在華琛的課堂上,極少聽到哈里斯的大名①。華琛注意到,當今的飲食領域,出現了許多有待研究的新議題:比如1990年代前吃肥肉,1990年代后瘦肉取代了肥肉的地位,蔬菜取代了肉食的地位;30多年前,人們把發胖看作是展示生活富裕、身體健康、家境富有的標志,消瘦被看作是倒霉、疾病和早死的征象,唯恐避之不及②。進入新世紀后,肥胖成為一種病癥,減肥成為時尚。我們也看到,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世界大牌食品幾乎不受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因素的制約而向全球擴張。而且,在一個世俗化的、祛魅的當下時代,即便是有些本土特色的食品,也被“文化人”建構出來,文化經濟(cul-trual economy)由此成為當前經濟活動的重要景觀。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里發生的一個轉向,是關注“文化中介者”在各種各樣消費品形象、消費經驗、消費認同和生活風格形塑過程中的作用和機制③。像葡萄酒那樣的商品,釀造人、營銷人員、公關人員、調酒師、分銷商和撰稿人,在酒的出處(provenance)問題上、進而在酒的消費上,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建構作用④。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中,或真或假的“起源故事”、“古代傳說”在地方小吃、地方酒、土特產品的塑造和營銷中,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日益凸顯。無論我們秉持什么觀點,食物是探知分析文化特性的一個重要視角⑤。在這個領域里,有待我們探尋的問題遠比我們已經獲知的知識和觀點要多得多。作為一種研究策略,文化唯物主義依然具有科學認識價值,同時也面臨著全球范圍內飲食變遷新景觀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