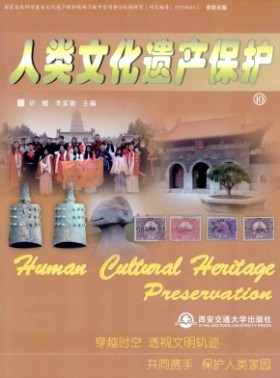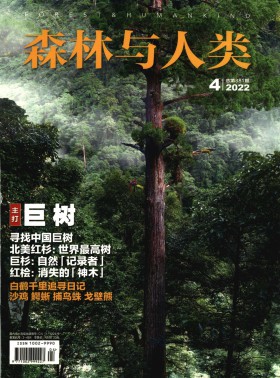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人類學論文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教育人類學視野下的傳統文化論文
一、人類學對教育的研究
人類學對教育的關注是由非正式教育(家庭教育)入手的,即嬰兒成長過程中教育信息的獲得為切入點,探析人類通過平常生活習俗中得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瑪格瑞德•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1928年),米德在本書的最后兩章,在重新系統地敘述薩摩亞養育兒童的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與美國兒童的教育實踐聯系起來并作了對比剖析。她在書中這樣描述薩摩亞姑娘的青春期:“薩摩亞姑娘的青春期與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時期別無二異,甚至會因為可以自由地談情說愛而顯得更加美好……那種在別處會出現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壓力在這里消失了……薩摩亞社會的輕松愉快的生活態度使青春期變得容易度過。……這正是由薩摩亞社會的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人類學對教育通過不同的角度進行過研究,因此后來人類學領域發展出了一門教育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專門研究人類獲得教育信息的途徑、方式、模式等一系列問題。“教育人類學主要涉及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進行研究。教育人類學在1970年以前的歷史主要是社會性的而非學術性的。其歷史的第一階段始于1900年,止于1960年;第二階段從1960年起持續至大約1970年。在第一階段中,人類學家駁拆了關于美國公立學校中移民、少數民族和低收入層次兒童以及殖民地屬地中原住民兒童學習癥結的“錯誤理論”。他們對這些兒童在學校中遇到的困難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釋,對學校的問題提供了一些選擇性的解決方案,并開展了研究工作,以為更好地解決學校問題提供知識扶持。第二階段所做的主要大事為,人類學家開始鼓勵在大學前的教育層次教授他們的學科。美國人類學協會成立了一個課程研究委員會負責開發和散播合適的課程材料。人類學家準備了一份教育參考書目,組織了多場研討會,并就具體的教育問題撰寫了論文。將人類學家引進教育的另一個原因是為糾正文化概念被誤用的需要,教育研究人員和干預主義者針對低收入階層和少數民族兒童提出的“文化匱乏”論。“文化匱乏”論意指這些兒童不具有他們來自主流白人中產階級的同齡人中所常見的一些“特質”。人類學家反對這種對文化的特質定義,支持少數民族群體關于他們的兒童在學校遇到困難的原因是基于他們的“文化中斷”的說法,并在不同少數民族群體和學校展開民族志研究以展示和尋求解救這種文化中斷。……1970年由關注教育問題的人類學家和對應用人類學概念解決教育問題感興趣的非人類學家共同成立了人類學與教育理事會。該理事會下設12個委員會,對學科與文化研究、認知與語言學研究、人類學教學、少數民族事務以及教師備課等興趣領域開展研究。從此,教育人類學作為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得于發展。”人類學的教育研究就是這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從1970年開始美國黑人孩子在官方學校(正規學校)所遇到的問題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委員會的人員站在體質特征上認為黑人孩子(或少數民族和收入低下的家庭孩子)在學校跟不上所設課程的原因在于他們的身體在進化過程中存在缺陷,由于他們的文化低下、腦部不發達所致,用一種文化偏見和人種歧視的眼光去看他們,而人類學家認為這種差異不在于體質上的不同,而是在于文化差異導致的,文化差異不應該用文化高低來看待,而是每個人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的不同導致他們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中斷”現象,所以人類學家提倡在這些少數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區去了解情況,進行民族志的調研,要找出文化差異存在的根源,從而解決他們在學校所遇到的問題等。那么,中國也是多民族的國家,內地(沿海地區)和邊疆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且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因素和傳統非正式教育系統,因此,在中國統一的課程設置和教學體系的學校教育中也存在著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對學習乏味、在巨大的壓力中學習、應付考試、理論學習跟實際應用聯系不上等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在新疆地區大學、中學甚至在小學也存在著。下面筆者舉例新疆教育中的問題和雙語教學中的不足之處作一番探討。
二、學校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教育中存在的有些問題跟基礎教育有一定的關系,大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甚至可以與基礎教育相關。中國人口眾多,各個地區都面臨著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選擇了報考碩士研究生,導致研究生也難就業的問題。這些光追究學歷不考慮質量的教育體系為什么會蔓延?是學校教育,即教育體制所導致的。我認為中國的孩子負擔最重,他們一生下來會走路以后就承擔了國家未來發展的艱難任務。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是不是忘記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環節呢?按照生物進化論的觀點,勞動是創造人類的重要環節。那么現在的孩子們學會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嗎?就像現代人對電腦或網絡依賴性越來越強一樣,他們對正式教育的依賴性也越來越高,沒有自己的設想、愛好,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沒有創造力等。我們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機械性的機器,總想把孩子培養得十全十美,讓孩子什么都要學,課外學習音樂(鋼琴、小提琴等等)、美術、外語、數學等,當然以上課程對于孩子的思維發育有好處的,但是強迫的學習會使孩子對這種正式教育產生懷疑,失去積極性。有些孩子怕長輩,只能應付性地學習,這樣對孩子的成長會起反面影響。“家有小兒,一天,忽地問道‘: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學嗎?’父親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隨口應了一聲:‘嗯!’卻突然聽見了歡呼聲:‘哦!明天不上學了!’父親這才想起,明天即非周末,也非公休日,怎么就可以不上學呢?于是狠狠地說:‘不行,明天得去上學!否則周末不帶你去玩兒。’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理由想象,這樣的狀況絕不僅僅只發生在一個家庭……”越來越多的都市孩子面臨如此的困惑,而想上學而沒有條件上不了學的偏遠的牧區、農區孩子也很多,這種問題教育學和人類學等學科也在研究并尋找解決的方法。現代人對于工具的依賴遠遠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況,雖然原始人所創造的工具很粗燥,但那是他們在艱難的自然環境中的斗爭中所制造的,是普通生活中發現的。因此,培養孩子也要考慮地方特色和非學校教育中所學到的內容。
(一)教材和教師梯隊缺乏,是影響雙語教學順利進行的根源
邊疆民族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不相同,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識的文化傳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會化教育并存的特點。所以全國統一進行的雙語教育教學模式很難適應各地區的教育實際。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學校教育時統一的教材(統一編的小學、中學漢文教材)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統一的語言———漢語。少數民族地區的孩子們也非常渴望學會一口流利的漢語,但是沒有很好的教學條件和教學設施,甚至缺乏優秀的漢語教師,而且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新疆,遼闊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著眾多民族)學校設立在偏遠的牧區或山區,教學環境很差,教師的待遇也不高,因此很少有教師愿意在那里教學。個案:“為了傳承哈薩克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阿依特斯”文化的傳承和培養接班人,我們從2011年開始編纂阿勒泰地區青河縣中小學通用的課外教材《哈薩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1)(2)(3),目前已經在青河縣各中小學開始試用,如果自治區政府和教育廳同意使用,我們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等哈薩克族聚集區普及使用,這在哈薩克族社會轉型期的關鍵時期對哈薩克族寶貴的文化遺產起到保存和傳承作用。”以上個案我們不難看出,這種地方性教材(尤其是文化類的教材)會促進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全面發展,保存和傳承少數民族優良口頭傳統文化。
(二)民漢合校和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文化人類學茶文化論文
一、穆斯林民族茶文化的茶品
(一)蓋碗茶
蓋碗茶茶葉多選龍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為主,泡茶前先準備一壺熱水,然后把茶葉、冰糖、桂圓等原料放入茶碗內,稱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稱為“五香茶”,如果加紅棗、枸杞、核桃仁、桂圓、芝麻、葡萄干、白糖、茶葉,則稱“八寶茶”,配制后,用沸水沖泡五分鐘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寶茶之外,蓋碗茶還包括“紅糖磚茶”、“白糖清茶”、“冰糖窩窩茶”。飲茶者一般根據季節和自己的身體狀況調配不同的茶。一般情況下,夏季多飲茉莉花茶、綠茶、冬天多飲陜青茶;而驅寒暖胃多飲“紅糖磚茶”;消積化食多飲“白糖清茶”;清熱泄火多飲“冰糖窩窩茶”;提神補氣、明目益思、強身健胃、延年益壽飲“八寶茶”。蓋碗茶除了自飲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種香茶,“金茶銀茶甘露茶,趕不上回回的蓋碗茶”,體現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對蓋碗茶的贊美和熱愛。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據原料不同分為三種:普通奶茶,即用磚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鮮奶和食鹽即成;第二種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將馬、羊、牛和駱駝鮮乳倒入鍋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結一層脂肪,用筷子挑起掛通風處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則先將茶汁倒入碗內,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種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燒制奶茶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將茯茶搗碎,放入銅壺或水鍋中煮,茶水燒開后一直煮到茶水較濃時,用漏勺撈去茶葉,再繼續燒片刻,待其有所濃縮之后,加入約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鮮奶,要不斷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種做法將茶水和開水分別燒好,喝奶茶時,將鮮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內,倒入濃茶,加鹽即成鮮香奶茶。有時喝奶茶時,加人適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帶辣味,可以增加熱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據味道來分,又分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調奶法同上,飲用時拌入白糖或蜂蜜,邊飲邊吃。咸奶茶,則是飲用前加入適量食鹽。香奶茶則是在煮熬茶湯時,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諸料融為一體,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喜飲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則將半炒的小麥、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搗碎,放入鍋中煮十分鐘,沸后加入鮮奶,多味融為一體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經營香料著稱于世,因而他們也養成了飲香茶的習俗,香茶茶品種類繁多,風味獨特,茶葉用花茶、綠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圓、大棗、芝麻、菊花、蓮子、枸杞等果實花卉,香茶因除加蓋碗茶配料外,還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檳榔、草果、人參、丹參、黨參、紅花、芹芥、五味子、銀耳、烏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時,應先將水燒開,然后將搗碎的茶葉放入開水中,出茶汁,然后將提前準備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進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輕輕攪拌,經五分鐘左右香茶即成,為避免斟茶時茶渣、香料混入茶湯,在煮茶的長頸壺上往往套有一個過濾網,避免茶湯中帶渣。常飲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膩。
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文化研究
摘要: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從文化視角對武術“非遺”傳承人的保護與發展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當前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有關傳承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且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主要形式;武術文化的“活態”傳承特點客觀上彰顯了武術傳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統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對于武術傳承人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和實踐參考.
關鍵詞:武術;武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武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因其特殊的文化價值與內隱的民族精神愈發受到重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武術無論是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還是區別于西方的人類身體文化和藝術,對于國人而言都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201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件,明確提出了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價值、目標和要求.在這種歷史的新時代背景下,中華武術的傳承與保護顯得更為迫切.如果說在某種程度上,武術與中醫、書法等能夠反映或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武術傳承人群體文化的理念與信仰、精神與追求或可看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或中華民族精神的縮影.正因為如此,武術作為一種活態傳承,文化保護的意義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價值.而其中,作為活態傳承的主體———武術傳承人的研究值得廣大研究者高度關注和重視.
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研究進展
1.1武術“非遺”保護的學術關注
200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標志著全球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始.從2003年我國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項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顯示出國家對于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的高度重視.為進一步落實黨中央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以及«體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關于“重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保護和利用”的相關要求,2013年,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推廣管理辦法»,并于當年公布了“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目錄”,其中有110余武術拳種入選目錄.作為我國較早從非物質文化視角關注傳統武術的學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確提出了傳統武術作為寶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盡快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此后,更專家學者針對如何保護傳統武術,從不同層面和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使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范疇內得到更好的保護與發展,如邱丕相、王崗、呂韶鈞、周偉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國家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中,已有60余項武術拳種入選.近年來,非遺視角或背景下和武術保護、傳承與發展相關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文化學和社會學視角進行的研究.此類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武術文化當展的梳理與分析,力求從文化層面上對當前武術的發展與保護提供學理層面的貢獻,該領域研究成果豐碩,代表者如王崗(2013)、陳青(2006)等.二是運用地域學理論,對我國不同區域的地域武術文化進行研究,該領域研究學者有郭志禹(2000)、韓雪(2002)等.三是對民間武術發展進行理論層面研究,提出發展相關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龔茂富(2013)等.四是運用跨學科理論對武術的保護與發展進行相關研究,如戴國斌(2004)、喬鳳杰(2005)、吉燦忠(2000)等.近年來,還出現了一批較為年輕的武術學者開始關注武術文化及傳承人相關的研究,如劉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處,關于武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態學、民俗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不再進行贅述.
1.2武術“非遺”保護學術研究問題的思考
藝術鑒賞課程設立的探索
作者:覃守達 單位:廣西教育學院中文系
當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課程拘泥于專業知識的抽象傳授,缺乏形象生動的教學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藝術素材,教材的內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難激發民族地區大學生的創造靈感,因此,建設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課程教材勢在必行。與此同時,受全球化及市場經濟的影響,許多少數民族民間藝術正在淡化、失傳,民間藝術人才發生嚴重斷層,因此及時挖掘和搶救民間藝術資源并建設成本土化的特色課程教材加以傳承發展之,已經成為一項十分緊迫的研究任務。
1.研究現狀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尚未存在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關這方面建設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護并發展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已成為全球熱點和國家策略的大好形勢下,以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為基礎的教學改革蔚然成風———如廣西藝術學院《美術教學論》課程負責教師長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廣西民族美術方面的文化資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術教學課程及其教材;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傳統體育》課程負責教師也長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廣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體育教學課程及其教材。杭州師范學院美術學院董春雷在《文藝研究》(2005年第5期)上發表題為《民間美術與學校教育》的論文認為:民間美術根植于民間,是實用與審美、物質與精神的完美統一。它既蘊藏著民族精神,同時又歷經了時間的洗禮,顯示出強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的變革,特別是在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民間美術的原生態面臨嚴峻的挑戰。河南大學藝術學院設計系胡俊濤在《教育與職業》(2009年第2期)發表的論文《高校藝術設計專業民間美術課程教學研究》也持相同的觀點———民間美術根植于民間,是實用與審美、物質與精神的完美統一。但該文更進一步地指出,民間美術的藝術形態的內涵與本質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關愛與重視,許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斷地探索研究這個領域。為了能更廣泛、更深遠地弘揚優秀民族文化,該文就民間美術的藝術特點,著重分析了課程設置意義、教學方法等問題,力求探索出一套較為合理的、適合藝術專業學生的民間美術課程的思路。
事實上,許多高校藝術類或人文類的教師都已經開始投入這一教學實踐中,就如何運用民間藝術資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邊遠地區少數民族民間藝術資源)來整合藝術類課程或人文類課程,掀起一股強勁的課程教學與教材改革創新之風。最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從1997年起,牽頭申報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優秀教學改革項目“文藝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跨學科交融”,接著又組織文藝學、民俗學、民族學、少數民族文學等學科碩士點,聯合向自治區教育廳申請“審美人類學系列研究”,獲得立項后,他們便深入地對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以及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的民間文化藝術資源進行審美人類學田野調查,基于廣西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資源來搞科研與教學,以審美人類學理論與實踐為一條紅線,把中文系相關的人文學科的研究貫穿成為相互關聯的學術整體。在他的帶動下,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審美人類學課題組積極探討審美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方案以及審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方法、意義及其學理依據等等,自覺形成一門具有影響力的特色人文課程———審美人類學,該課程教學成果榮獲2005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編的《審美人類學概論》作為“十一五”國家級教材開始了立項建設。
2.研究內容及其方法
基于廣西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資源來開展高校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建設研究,是一項具有時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學改革任務。然而,面對廣西11個少數民族許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門別類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間藝術資源,并形成一部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實際上是一個十分龐大而繁難的教學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項建設研究方面,必須選擇這樣的思路:從壯族開始,逐個對這11個少數民族民間藝術資源進行研究,并逐個形成相關的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以壯族為例,具體研究內容為:整合并利用當代廣西壯族民間藝術資源———側重于壯族神話、山歌、舞蹈、戲曲(壯劇)、樂器、服飾、工藝美術等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運用網絡及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開展當代廣西壯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建設的研究。在具體的建設研究過程中,我們將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音樂文獻學下花兒研究
摘要:本論文以中國知識期刊網自1979年至2018年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獻內容為分析對象,從音樂文獻學的視角出發,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花兒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呈示。從數量看2001年是分水嶺,數量比之前陡增十倍;從內容看,花兒研究動向與國家大政方針密切相關,也體現出音樂文獻學對花兒研究方法的導引價值。
關鍵詞:音樂文獻學;花兒歌種;發展趨勢
“文獻”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對學生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是現存資料關于“文獻”一詞的最早記載,也是孔子感慨文獻不足而無法深入去考證夏商之禮。各個領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獻的支撐使很多領域的研究都處于滯后甚至空白狀態,文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音樂文獻學在音樂領域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音樂文獻學也是20世紀80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音樂文獻學是通過對音樂文獻的研究,揭示音樂形態變化、社會流傳和發展規律,并為音樂文獻的使用提供理論依據的一門較新的學科。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需求,音樂文獻學本體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產生于明代的花兒作為廣泛存在于我國西北地區的音樂形式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對于花兒的研究近年也越來越得到學界專家的重視。
一、1979年—1989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檢索到有關花兒研究內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異明顯,以普通刊物為主。(一)文章研究的對象花兒音樂分析、花兒演唱、創作的花兒劇、花兒音樂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兒的相互關系、花兒的歷史形成以及花兒音樂審美等方面。(二)文章的敘述內容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花兒、花兒會的民間傳說、口頭故事等進行介紹;從文學的角度對花兒歌詞的語法、方言、詞式結構等進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學術身份1.花兒演唱名家有朱仲祿、蘇平等,他們對花兒音樂的類別、音樂表現和演唱技藝等進行了介紹。2.高校民俗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者有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柯楊。他在1980年與雪犁合編《花兒選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叢》第3期發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顆明珠——甘肅蓮花山花兒漫記》,把花兒音樂介紹到了海外。此外,還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錫文、魏泉鳴等學者。3.專業音樂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喬建中于1987年在《中國音樂學》發表《甘肅、青海花兒會采訪報告》一文,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花兒音樂的形態從音樂材料的分析到其歷史成因和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這一時期總的來說,對花兒的研究還是以文學性研究為主,對花兒的曲令音調的研究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兒研究發展趨勢
從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這十年內發表的花兒研究文章為106篇,這一時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核心期刊中有關花兒的研究比上一時期明顯提升。1.民俗學、文學角度的研究,從介紹、描述型發展到較深層次的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系統研究。如柯楊于1997年發表在《中國典籍與文化》第3期的《花兒會——甘肅民間詩與歌的狂歡》一文。2.研究視角有所拓展。如杜亞雄1997在《民間文學論壇》發表的《“洮岷花兒”與生殖崇拜》已經涉及社會學方面的問題。3.文章研究涉及的內容與前一個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結構上有了一定的調整,花兒研究中音樂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學性研究向音樂性研究傾斜。
淺談民族音樂研究模式
摘要:西方世界對民族音樂研究分成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傾向“音樂學”方向,其代表人物是曼特爾•胡德(MantieHood),其堅持音樂本體第一位,并提出了“雙重音樂能力”;第二種是傾向于人類學方向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梅里亞姆(AlanP.Merriam)和蒂莫西•賴斯(TimothyRice),他們力求從人類的發展中真正了解民族音樂,認為通過音樂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及創造和發展該音樂的“人”。本文主要就梅、賴研究模式進行比較分析,以期管窺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研究的一種前進方向,為推進中國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做出微末的貢獻。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梅里亞姆;蒂莫西•賴斯;研究模式
一、梅里亞姆模式
梅里亞姆1964年出版的《音樂人類學》一書中,提出了其音樂人類學研究“概念——行為——音響”三重分析模式(如圖1所示)。在書中他提到:“那么,音樂觀念是音樂人類學家了解音樂體系的基礎,因為音樂觀念是所有人群的音樂行為的關鍵所在,不理解觀念無法真正理解音樂。”圖1三重分析模式他認為某一音樂事物或現象的產生,首先要研究音樂的概念,即當音樂表演者與聽眾兩者腦海中的音樂觀念契合時,這一段表演將取得成功。當人們將音樂概念付諸行動時,音樂的行為隨之出現。梅里亞姆將音樂的行為分成了四種:身體行為、言語行為、社會行為、學習行為。伴隨著音樂行為而產生的是一種蘊含深厚的文化內涵,包含在一定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種影響,它被這個特定背景下的人創造,為這個背景下的人服務,但也不能獨立于這一特定背景。梅里亞姆認為,“概念——行為——音響”是一個單向循環的有機整體,缺一不可。
二、蒂莫西•賴斯研究模式
(一)四級分析目標
1987年,賴斯在其論文《關于民族音樂學的模式重塑》中提出了人類學研究的四級目標即:一級目標:分析的程序;二級目標:形成的過程;三級目標:音樂學目標;四級目標:人類學目標。賴斯四級目標研究模式的第一級目標是“分析的程序”,包括概念分析、行為分析、音樂分析,即梅里亞姆“三重分析模式”的內容。第二級目標是形成的過程,包括歷史建構、社會維持、個人創造與體驗這三個維度(如圖2所示)。賴斯認為“音樂是基于個人的創造性而產生,個人的創造性又與歷史構成性、歷史傳統有關系,它受到歷史傳統的制約。音樂創造出來以后,又是由社區或者村莊、部落等社會群體來維持的。”他認為對音樂的研究,首先應有一個明確的歷史建構,音樂的創造一定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之下的創造。其次,個人層次的創造和體驗是指在上述歷史背景下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體驗和感受產生創作靈感,并完成音樂創作的過程。最后,社會維持指音樂的傳承和維護一定是第一個維度歷史建構下的人進行繼承和維護。圖2三個維度第三級目標是音樂學目標,這一級目標主要是用于探尋人類如何創造音樂的問題,也就是探索人們在創造音樂時所用到的方式方法以及形成的風格體系等問題。第四級目標則是人類學目標以及最終認識人類自身。蒂莫西•賴斯研究方式的四級目標是層層遞進的,他希望從音樂的生成背景、創作過程以及其傳承和維系中最終了解音樂和人類其他行為之間的聯系。
音樂民族志發展歷程
以(英)愛德華•泰勒(EdwardTylor,1832-1917)和(英)詹•喬•弗雷澤(JamesFrazer,1854-1941)為代表的古典人類學家從旅游者、傳教士和殖民地官員的手里收集日記、傳記等非歐見聞的二手民族志資料,在搖椅上寫下了關于世界土著風俗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金枝》等洋洋巨著;①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1884-1942)以田野調查寫就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奠定了科學民族志的研究范式;現代實驗民族志企望通過田野實地考察催生“以他觀我”,從田野觀察的“淺描”(thindescription)走向格爾茲(CliffordGeertz,1923-)文化闡釋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人類學民族志方法給音樂學研究以極大的啟示。 時而至今,伴隨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歐美音樂人類學的實驗民族志不斷的實踐,而我國當代民族音樂研究也在進行卷帙浩繁的音樂集成工種中探索和實踐了民族音樂研究的經驗和方法,這些新范式體現為逐漸出現的與音樂集成志書并行的現代音樂民族志上。考察人類學民族志和音樂民族志的演進以及我國當代民族音樂研究的人類學進路,有利于進一步推進我國音樂研究的人類學建設。筆者不揣淺陋,求教大家。 一、業余→科學→實驗:人類學 民族志的序進歷程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對異地人群見聞描寫的著述,也是居于田野調查的一種研究方法,是人類學和人類學家安生立命的看家本領。由于人類學家長期田野工作(fieldwork)被賦予書寫,使民族志成為現代人類學特有的學術活動而被普遍看好,成為人類學家成長不可或缺的標志。民族志對于人類學和人類學家如此重要,其間有一個不凡的發展演進過程,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是由業余民族志到科學民族志再到反思民族志的演進序列③。 業余民族志雖說可以追溯到歷史上的許多異文化見聞的游記和風俗的志書,但有用于人類學發展直接關聯的并不是如中國的《山海經》、《蠻夷傳》之類的典籍,而是來自于殖民地官員、傳教士和商人等關于海外民族的奇風異俗和奇聞軼事的記錄。這些業余民族志書寫是游歷者隨意和自發的興起使然,有別于學者研究性的專業指歸。適逢歐洲科學發展分門別類的機遇,有志于民族風俗研究學者對這些游記式的資料很為關注,泰勒和弗雷澤的杰出成就得益于這些資料的惠澤。為使業余民族志的書寫更能夠滿足人類學家的需要,泰勒積極參與編撰《人類學筆記和問詢》(1874),為往返于殖民地的各種人士的寫作民族志提供指導。完成人類學者需要的民族志實踐是由馬凌諾斯基完滿實現的。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為標志的“科學民族志”使人類學能夠以科學的身份立足,對此,弗雷澤有高度肯定和評價④。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類學界對民族志這一知識生產載體和方法進行反思,即非歐傳統文化以及非其歷史傳承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對主義的前提下被客觀描寫。馬凌諾斯基去世后出版了他對土著充滿厭惡和對田野工作厭倦的日志《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記》(1967)⑤,給“科學民族志”當頭一棒。而德里克•弗里曼(DerekFreeman)對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928)結論截然相反的調查和研究⑥,加劇了人類學的危機,以及1978年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EdwardWadieSaid,1935-2003)發表《東方學》,⑦對人類學的聲譽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使民族志客觀描述的觀念遭到懷疑,導致人類學理論受到根本性的挑戰,遭遇空前危機。 拯救人類學的是格爾茲為代表的解釋人類學,解釋人類學就是“各種民族志實踐和文化概念反思的總稱”。[1]格爾茲如同一個文化英雄,以其為代表的解釋人類學引領和推動了民族志書寫的反思和實驗性寫作,他于1972年發表的《深層的游戲:關于巴厘島斗雞的記述》就是民族志革命性的實踐。解釋人類學以1973年出版《文化的解釋》⑧中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和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⑨中的“地方性知識”(1ocalknowledge)為武器,拯救人類學界搖搖欲墜的嚴峻現實和民族志書寫的表述危機,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去闡釋和維護民族志的地位。反思和闡釋推進的是民族志實驗,如70年代格爾茲的《深層的游戲:關于巴厘島斗雞的記述》(1972)、保羅•拉賓諾(Paul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業的反思》(1977年)和讓-保羅•杜蒙特(Jean-PaulDu-mont)的《頭人與我》(1978年)等作品。集中反映和總結這些實驗作品的理論探討是1986年喬治•E•馬爾庫斯(GeorgeE.Marcus)與米開爾•M•J•費徹爾(MichaelM.J.Fischer)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喬治•E•馬爾庫斯等《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的出版。⑩反思使科學民族志走下了神壇。探索和實驗還沒有結論,也很難會再有唯一的模式成為范本,因此探索和實驗還具有合法性,還將繼續進行。客觀描寫遭遇表述危機,傳統的樣式還因“部分真理”而繼續,馬爾庫斯認為“無論如何,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原有的民族與地方之調查領域,民族志不會再回到檔案功能”。[2]客觀描寫已是不可能,解釋就是必然的選擇。音樂人類學的境況一同如此,樂譜文本(text)不能還原音樂本文(context)的尷尬現實,解釋也將成為關于音樂的民族志的必然進路。 二、比較→描述→闡釋:西方音樂 民族志的人類學步履民族志描寫的對象是人,音樂學描寫的對象是聲音,而音樂民族志(MusicEthnography)的描寫對象不僅是音樂,還“超越了聲音的記寫而去表現聲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賞和流傳至其他的個體、族群,去描寫社會和音樂的各種過程”(AnthonySee-ger,1992)。可以說音樂民族志是民族志與音樂學的結合,是在田野工作個人體驗的基礎上,對人類音樂活動全面的記錄描述;也可以理解為人類學的音樂文化的民族志。由于人類學民族志方法由“淺描”向“深描”的轉變,音樂民族志也體現由音樂記寫(“淺描”)向音樂闡釋的“深描”強調。#p#分頁標題#e# 西方音樂學研究有著自己的傳統,早期音樂民族志是來往于殖民地等海外的游記、日記和殖民檔案資料里的音樂民俗記寫。如同古典人類學利用民族志材料進行比較研究尋求人類社會規律的抱負,早期的音樂學研究也收集傳教士、旅游者和殖民地檔案民俗材料進行比較研究。伴隨民族志學者的錄音而有時音樂者也親自披掛上陣,直接采錄民俗聲音,進行聲音比較,以期歸納出人類音樂的普遍規律,因而產生研究音樂的學問———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musicology)。1885年發表了埃利斯(A.J.Ellis,1814-1890)《論各民族的音階》是比較音樂學開始的標志,奧地利音樂史學家阿德勒(Gui-doAdler,1855-1941)發表《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及目標》正式提出“比較音樂學”概念,而真正實踐“比較音樂學”的卻是德國人。1900年,德國心理學家、音樂學家施通普夫同助手亞伯拉罕及奧地利音樂學家霍恩博斯特爾在柏林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創立了“柏林人種學唱片檔案館”,對人類學家和音樂學家在世界各地采錄的數以百計的圓筒錄音進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施通普夫的《暹羅的音體系及音樂》(1901)、霍恩博斯特爾與薩克斯的《樂器分類法》(1914)等等,使柏林大學成為當時比較音樂學研究的中心,形成了比較音樂學的“柏林學派”。 一戰期間,比較音樂學學者沉浸在柏林大學的音響資料館躊躇滿志地研究音體系,馬凌諾斯基開創的參與觀察的科學民族志方法,為比較音樂學轉向田野起到啟示作用。二戰前后,許多歐洲的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比較音樂學家流亡美國,特別是喬治•赫爾佐格(HerzogGeorge,1901-1983)1925年移居美國,投奔博厄斯門下,促使了源起于歐洲的比較音樂學與人類學在美國結合,使文化之研究音樂學成為新穎的學科方法。同時,柏林音響資料檔案館毀于二戰,比較音樂家又到處逃亡,于是以博厄斯學派研究方法為代表的音樂文化研究逐漸為顯學,簡單錄音和音樂記寫的音樂學讓位于人類學民族志方法的音樂研究。 早期西方音樂民族志材料是航海發現和殖民遠征時代對異國音樂缺乏概括的泛泛描述。啟蒙時期的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對中國、波斯、瑞士等音樂的記譜和研究,到1914年斯特蘭韋斯(A.H.FoxStrangways)對印度斯坦的音樂的整體研究,是民族志方法在音樂學研究中的應用。 1930年代后的歐美音樂研究關注了自然民族和族群,以參與體驗的方式去獲得第一手的民族音樂材料,使人類學與音樂學結合,產生赫爾佐格《尤馬族的音樂風格》(1928)及其弟子內特爾(Bruno•Nettl,1930~)《北美印地安人的音樂風格》(1954)等著作。 荷蘭音樂學家孔斯特(Jaap•Kunst)1950年出版《民族音樂學》一書,提出用“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取代Comparativemusicology(比較音樂學),標志著學科發展轉型的新階段。由于切合當時音樂學以原始民族和族群的音樂文化為關注的實際,漸為學界接受和認可。這種以民族文化整體關照為視角的音樂研究的思路和實踐,導致1964年出版了內特爾的《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TheoryandMethodinEthnomusicology)和梅里亞姆(Alanp.Merriam.1923-1980)的《音樂人類學》(TheAn-thropologofMusic)兩部民族音樂學的經典著作,引領了民族音樂學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說,內特爾《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是繼承了赫爾佐格音樂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衣缽對孔斯特“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提出的進一步規范和闡釋,把學科對象和研究范圍拓展到“無文字社會、亞洲和非洲高文化音樂及民俗音樂”;而梅里亞姆則高舉人類學音樂研究的大旗,在《音樂人類學》(1964)及隨后的文章明確地提出“作為文化的音樂研究”,進一步把民族音樂學研究從民族(族群)的層面提高到人類文化的高度,有意強調了“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中應有的音樂人類學(TheAnthropologofMusic)研究的文化旨意。1950年代以來,作為孔斯特高徒的美國音樂學家胡德(MantleHood,1918-)強調“雙重音樂能力”的培養和參與觀察,兼顧音樂學與人類學研究的平衡。民族音樂學研究的主流方法論亦步亦趨的跟隨人類學的腳步,由于從事音樂研究的特殊人類學家和特殊音樂學家的特殊知識背景和特殊方法好惡,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和風格的分化和融合顯得非常的復雜多樣。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類學方法合理論受到懷疑,民族音樂學也在思考學科方法上謹小慎微,從“比較音樂學”(1885)到“民族音樂學”(1950)再到“音樂人類學”(1964),表征著學科發展的比較(Comparison)→民族(Ethno)→文化(Culture)三個階段,○11體現著從注重比較到注重描述再到注重闡釋方法的轉變。但小心謹慎地記錄著“他者”音樂,力圖客觀地描寫獨特族群或區域音樂文化的“民族志報告”。一方面既是虔誠地效仿著人類學民族志的方法路徑,另一方面又是在誠惶誠恐地力避科學民族志的覆轍。格爾茲的闡釋人類學拯救了人類學的危機,也給民族音樂學帶來了新的方法和理論。 雖然說影響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也應此形成繁復多樣的研究群體和莫衷一是的方法實踐。但是,描述(“淺描”)與闡釋(“深描”)逐漸成為民族音樂學的主流方法話語。1970年代的人類學界在反思和拯救,找到了突圍的闡釋學方法;而1970年代的民族音樂學界也在思考,于是有了內特爾和梅里亞姆等對于學科對象和方法的進一步思考,如梅里亞姆《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的定義:歷史—理論的觀察》“作為文化的音樂研究”和內特爾《民族音樂學:定義、方向及方法》對“田野”概念和研究領域的探討,○12激勵了1980年代民族音樂學的大步發展。不但學科呈現多樣化,音樂學家、人類學家研究民俗音樂,而且音樂教育家和非歐音樂表演家及一些民間音樂風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這個“民族音樂學”隊伍中來。1989年社學家霍華德.S.貝克爾在美國《民族音樂學》第二期發表致民族音樂學C•西格爾(ChalesSeeger)的信,說“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世界上的一切音樂”,[3]體現了非“民族音樂學家”的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關注和思考,也表達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宏大抱負。#p#分頁標題#e# 1980年代1990年代是闡釋音樂的民族志蓬勃發展的時代,也啟發了音樂民族志的發展。1978年[美]保羅•伯利納(Paul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被稱為音樂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費爾德(StephenFeld)1982年的《作為象征體系的聲音:卡魯利人的鼓》和1984年關于卡巴布亞—新幾內亞魯利人音樂民族志的《聲音構造即如社會構造》,○131987年安東尼•西格(AnthonySeeger)的《蘇雅人為何歌唱》,○14以及1990年[日]三口修出版《出自積淤的水中—以貝勞音樂文化為實例的音樂新論》,○15儼然是關于音樂文化的經典人類學民族志。至此,音樂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寫、注重解釋已是重要特征。 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從比較音樂學的音體系關注,到注重客觀描寫(淺描)的人類學民族志實踐,再到強調闡釋的人類學方法的音樂民族志追求,以文化闡釋(深描)為重要價值取向的現代音樂民族志就成為普遍認可的方法和模式。 三、方志集成→音樂民族志:我國民族音樂研究的人類學轉型 對于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來說,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是舶來品。1920年代初北京大學創辦的《音樂雜志》發表了早年留學日、德的蕭友梅(1884-1940)、王露(1878-1921)等關于比較音樂學的文章;1927年王光祈(1892-1936)入柏林大學師從霍恩博斯特爾、薩克斯等音樂學家,是中國人正統接受比較音樂學的先行者。但是,直到1980年南京藝術學院舉辦“全國第一次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才標志民族音樂學在中國正式確立。南京會議以來的20多年里,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或因結合中國民族學的學理特點,或因結合傳統方志的紀實要求,或因追尋人類學的現代路徑等,研究風格異彩紛呈,或偏重傳統的音樂本體,或在乎民族識別的視角,或指歸人類文化的視野。 方志是我國傳統記述地方地理文化的志書,西周的“采風”到1920年代初的“北大歌謠研究會”民歌收集,著力點不在音樂上。1940年代陜北(如延安“民歌研究會”,1938)和國統區(如重慶“山歌社”,1945)才注意了對民歌音樂的收集和研究,○16傳統方志性的民歌采風成果才開始從文學性的歌詞開始轉到音樂的記錄上,也使地方民歌以選集(集成)的形式開始了方志性的整理。建國初期有了規模較大的音樂方志集成性質的工作,1950年對無錫民間音樂家華彥鈞(即阿炳)的二胡曲、琵琶曲的傳譜和演奏技藝進行采錄、整理;1953年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對山西“河曲民歌”調查,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訪專集》(1956);1957年對“孔廟音樂”(大成樂)的調查和整理,以及1956年至1964年,進行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同時進行少數民族音樂的調查。這些對我國民間音樂進行大面積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方志性的集成和研究介紹書籍,如常蘇民《山西梆子音樂》(1954)、楊蔭瀏《蘇南吹打》(1956)、貴州音樂家協會《侗族大歌》(1958)、《苗族民歌》(何蕓、簡其華等)、《西藏古典歌舞———囊瑪》(毛繼增,1960)等專著。這一時期的巨大成績就是民歌、說唱戲曲和樂種曲目選編和地方歌舞的方志調查報告出版和發表。 過于深厚的民族音樂研究傳統和始于1979年的“十部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編纂出版的浩瀚工程,使得“民族音樂學”的發展與集成方志的編撰和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的任務方法相互糾葛,相伴相生,磕磕碰碰走過20多年的歷史歲月,在2005年浩大的音樂集成工程終于劃上一個記號,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別編撰了音樂志書集成的分卷約有120多卷。音樂集成工作組織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音樂田野調查,為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奠定了資料基礎,而許多從事民族音樂學的專家學者也在音樂集成的工作中成長起來。這一時期陸續出版《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袁炳昌、毛繼增主編)、《維吾爾十二木卡姆》(周吉、買提肉孜等)、《蒙古族古代音樂舞蹈》(烏蘭杰)、《廣西少數民族樂器考》(楊秀昭、何洪、盧克剛、葉菁)、《貴州少數民族音樂》(張中笑、羅廷華主編)和《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田聯韜主編)等樂志集成。其中伍國棟主編的《白族音樂志》就是我國傳統方志編撰模式在音樂志書實踐的典型代表。○17雖然集成志書工程在一定意義上擠壓了音樂民族志的發展,但是,為編撰音樂集成的田野研究和音樂院所的田野調查也形成的一些小型的音樂民族志(文章),陸續在《中國音樂》“中國傳統音樂采風與心得”專欄(1990-1994)和《中國音樂年鑒》“民俗音樂實錄”專欄(1991-)以及其他的學術刊物上發表。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1993年領銜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的實施拓展了音樂民族志的發展空間,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龍虎山天師道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1996)、《貴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儺壇儀式音樂研究》(鄧光華,1997)等著作以及拓寬后的《中國傳統民間儀式音樂研究•西北卷》、《中國傳統民間儀式音樂研究•西南卷》的組成篇章,○18已是大型音樂民族志(專著)。 當前我國的音樂民族志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相當于人類學的科學民族志,如“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項目中的系列民族志專著成果;另一類是相當于人類學中的實驗民族志,如蕭梅《田野的回聲—音樂人類學筆記》、薛藝兵《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和楊民康《貝葉禮贊———傣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研究》、沈恰《貝殼歌———基諾族血緣婚戀古歌實錄及相關人文敘事》、楊殿斛《民間音樂消長:鄉民生命意識的藝術訴求———黔中腹地營盤社區音樂的民族志敘事》等主題民族志。特別是洛秦的《街頭音樂:美國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縮影》,儼然以游記見聞的方式敘述研究對象,一反全知全能第三人稱的隱身敘述,以第一人稱限知視角的“我”參與觀察,加入口述紀實的內容,成功地擇用敘事語體對繁碎的街頭音樂(俗文化)進行研究,實為實驗音樂民族志的典型代表。○19可以說,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可能再進行大規模的音樂集成的調查與編纂。隨著集成任務的完成,民族音樂學者的工作目標就得很快從集成轉移到民族音樂的深層次研究上。民族音樂學研究不但要關注民間民俗音樂,也要關注城市大眾的通俗音樂活動。我們不再耗費精力去論爭“Ethnomu-sicology”是稱為“民族音樂學”還是稱為“音樂人類學”好,正如本學科1885年原稱為“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musicology),由于學科的方法拓展和學科旨趣的嬗變,到1950年人們開始接受了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如若過去些年月,我國民族音樂研究逐漸從民族的視角走向族群和人群視角的時候,人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名稱(不管是Ethnomusicology還是MusicalAnthropology)。畢竟,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97學科目錄”始設“人類學”,而“民族學”在在中國盤根錯節發展中賦予了民族政策意識而具有特殊地位。#p#分頁標題#e# 當前由于研究者個人的知識譜系不同和切入視角的喜好,可以并用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名稱,但借鑒人類學從“淺描”到“深描”的闡釋人類學的方法逐漸等到學界認可而廣泛地應用到音樂民族志的研究之中。體現對音樂民族志思考的集大成者是專著《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以中國傳統音樂為實例》的出版。○20綜上所述,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發展得益于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啟示,而音樂民族志的發展也汲取人類學民族志的給養,音樂民族志的發展也跟隨人類學的發展而具有相似的階段特征。對于中國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發展來說,西方比較音樂學(阿德勒,1885)、民族音樂學(孔斯特,1950)和音樂人類學(梅里亞姆,1964)在百年里的歷時發展中積累的理論和方法,在20多年里共時平面的呈現;加上我國方志編纂的音樂集成任務使然,使我國從1980年到現在的民族音樂研究方法和風格相互交織,多樣共存,有偏重形態方面的比較分析和集成志書,有關注民族身份的音樂系統介紹和分析,有注重音樂與相關文化的深層探究。對于音樂民族志的書寫,有集成志書的編纂,又有科學民族志風格的著作,還有實驗民族志的探索。考察人類學民族志和音樂民族志的演進以及我國當代民族音樂研究的人類學進路,有利于進一步推進我國音樂研究的人類學建設。筆者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和發展,適合于研究者各自課題需要和個人風格的音樂民族志會異彩紛呈,把中國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建設和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費孝通初期鄉村經濟思維評析
本文作者:張霞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費孝通《江村經濟》簡介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撰寫的博士論文,但這篇論文的醞釀和收集資料開始于國內,有扎實的前期研究基礎。費孝通先生論文里的江村真實的地名叫開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當時在行政上隸屬于江蘇吳江縣震澤區,該地區是中國近代傳統農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業文明后發生社會變遷最劇烈的地區之一。費孝通比較早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個村莊。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別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和“復興絲業的先聲”兩篇文章,介紹開弦弓村發展生絲制造工業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資本主義沖擊等問題,闡述了興辦鄉村工業對維持農民生計的意義。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調查的預調查。[1]1935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進行調研,是年冬,在瑤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難,他自己也受重傷,不得不返鄉養病。1936年暑假期間,接受在開弦弓村開展以推廣改良蠶種和科學養蠶為中心的土絲改良運動的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他到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從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費孝通寫了7篇《江村通訊》,相繼發表在《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題為“這項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希望”。1936年9月,費孝通帶著他的調查資料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費孝通接受導師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議決定以他在開弦弓村的調查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不久,弗思的導師、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導費孝通的論文寫作。1938年春,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村莊的經濟生活”)。1939年該論文由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英文書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國農民的生活》,扉頁上印有“江村經濟”)。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書名《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文庫》,由商務印書館再版。《江村經濟》在人類學學術發展史上改變了人類學只研究未開發文化的軌道,擺脫了人類學“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2]的傾向,對處于文化急劇變遷中的中國鄉村社區作了生動描述和深入研究。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經濟》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E•丹尼森•羅斯認為:“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3]由于費孝通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費孝通人類學最高獎———赫胥黎獎。
二、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
《江村經濟》廣泛探討了江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實際上也是一部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三農”問題的經濟學著作。本文不就該書在人類學方面的學術貢獻多加評論,僅就費孝通先生對鄉村經濟方面的研究加以評述。①*
(一)鄉村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