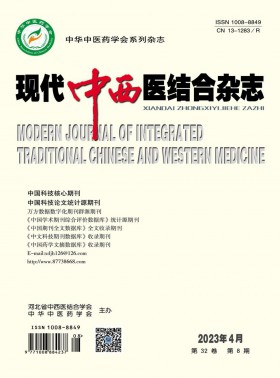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西比較下的女性主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米莉 單位: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引言
19世紀中期西方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開始興起,傳統的政治史、政治理論、社會學乃至整個人文科學領域逐漸出現了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那就是:作為長期以來被忽略、甚至被輕視的一個性別———女性的政治權利、政治地位、在歷史上的政治遭遇等等問題,開始成為了學術界和普通人群日益關注的對象,并造就了一個百年不衰的熱門話題。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從本質上而言,性別體現了一種“權力關系”[1](P10),是一個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政治、歷史、經濟和文化范疇。在不僅要研究婦女在世界中所處的地位、更要“改變”[2](P15)它的這一宏大目標和歷史責任感的強烈驅使之下,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婦女學和社會性別研究一直處于興盛不衰的狀況。由于這一議題的介入,政治領域的概念被擴大了,不僅國家、王朝、階級、民族、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等等內容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性別也逐漸成為了政治學、政治史、乃至整個人文科學領域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并對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界和知識界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本土的女性學研究于較晚時期開始出現,并分別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七八十年代、80年代之后出現了3個研究的高峰[3],在這其中,受西方早期經驗及其研究成果的影響,相當一部分學者堅持認為傳統中國的婦女長期處于“卑下”、“被動”、“受戕害”的地位[4](P1-5),發端于五四時期的“父權壓迫模式”成為他們分析這一群體時的主要研究徑路和分析范式。然而,這種基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5](P4)應運而生的分析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西社會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概念化、格式化了真實的歷史場景的同時,也無助于厘清基本概念,從而推進中國本土女性學的進一步展開。在此,本文將通過分梳中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的特征,來發掘出它們各自為中、西兩種不同的女性主義提供了什么樣的文化資源和特征,并通過對二者的特點進行比較,反思早期西方經驗在運用于中國本土研究時的局限,以期促進中國本土女性學與社會性別研究的進一步展開。
二、“二元對立思維”: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下的性別定位
作為西方傳統的典型思維,“二元論”(dualism)和“二元對立思維”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著深遠的影響。例如“理性/感性”、“精神/物質”、“靈魂/肉體”、“公共/私人”、“文化/自然”、“主動/被動”等等。在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之下,每一組對立都被分析出一種等級制,并最終歸結為一個基礎性的對立結構———男女對立。換而言之,男女對立隱藏在所有的對立之中,而在這一對立的結構之中,男性一方是積極、主動和有力的,而女性一方則永遠被看作是消極、被動和無力的代表。同時,這些本質屬性對于男女雙方來說都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文化限定,已“歷經政治與經濟改革及革命、學術及技術上的轉變都不受影響。”[6](P16)正是這個特殊的二元性,構成了西方性別關系定位的思想文化基礎。
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眾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持續建構起來的關于兩性關系的觀點,“其固有的內在特征就是,通過這個二元對立的一極(女性)來緊密地確認男性,同樣通過另一極(男性)來緊密地確認女性。”[1](P7)而其具體的做法則是“將男性的政治理論嚴格地認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則與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關。”[1](P9)由此,女性在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地位、價值被理所當然地邊緣化、低級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下所形成的對于女性的歧視,可以被恰當地稱為是“二元論性別歧視觀”[7](P164)。西方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固有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兩性職責與社會地位的截然兩分,最終導致了西方文化對于女性的歧視。通過將女性與更不理性、更低級的代表著“自然”的私人領域相連,以及與更高級的代表了“文化”的公共領域的截然分開,女性被長期地排除在政治和公共領域之外,變為男性附屬的存在。正是這一點,受到了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強烈批判和不滿。
三、整體性思維: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下的性別定位
自董仲舒之后,傳統中國的性別定位在總體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陽尊陰卑”的兩性不平等結構[8](P97-98),但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不同,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同時還表現出了一種“整體性”和“關聯性”[7](P169-170),正是這一點,構成了中國與西方性別格局的不同特征所在。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看來,事物的全體構成一個單一秩序的世界。宇宙或人世的和諧,不在于某個單獨的因素獨自發揮作用,而取決于各種因素之間的協調、融合并共同發揮作用。體現在具體的政治、倫理秩序設計中,則是盡力去保持各種因素之間的平衡和配合,而不是要一方取得絕對的獨占性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只是整個社會和文化網絡中的一分子,都應當最終服從于一個統一的家族、社會、政治秩序。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這種整體性特征,在客觀上決定了兩性之間的關系,將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合作”與“分工”,而非西方政治文化意義上的絕對化的“對立”與“對抗”。
中國傳統文化整體性思維特征的第一重體現,表現為道家傳統的“陰陽觀念”。在這一學派看來,“陰”與“陽”并不是截然分離的事物兩極,恰恰相反,這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另一方的變化,并在持續的運動過程中被另一方所塑造和影響,從而反作用于另一方,最終影響到宇宙的秩序。陰陽關系的存在和維持,必須建立在二者互融互生的基礎之上才有意義和實現的可能性。宇宙是這二者間的渾然統一體,整個社會體系的和諧也有賴于這二者間的融會貫通。因此,雖然中國傳統也有將女性、男性等同于“陰”、“陽”的做法,并將女性置于較弱的“陰”的位置,但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不同的是,建立在“陰陽和諧”觀念基礎上的兩性關系,從最終極的意義上而言是“相互補充、互融互生,而非相互隔離、內外懸絕”。男、女兩性不可能被徹底地分離,女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生活的公共領域之外。也正是由于二者間的不可分割與相互混融的特征,才使得傳統中國的性別哲理思想不但并非注定了要鼓吹男尊女卑,反倒是注定了會反對“一陽獨大”的單一性別結構。[9]在實際的生活中,女性也不可能被限制在與男性徹底隔離的領域之外。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思維特征的第二重體現,表現在儒家傳統對于家族的重視。在富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特征的儒家學派看來,家族的穩定和繁榮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基線”[10](P73)和“最看重的價值”[11](P135),是優先于個人成就和價值的文化意義與現實目標,有時甚至還具有一種“宗教上的意義”[12](P24)。個體(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只是家族網絡中的一分子,兩性的共同目標都在于維護這一體系的存在和繁衍,對于單獨的個人和社會而言,某個性別并無絕對的意義。因此,雖然從整體上而言,“男主外女主內”是兩性之間一個普遍性的地位設定和分工限制,但在這樣一個關聯著的范疇里,兩性應當保持一種互相配合、互相補充的關系,而非一方壓迫另一方的激烈對抗關系。換而言之,男女兩性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更多體現為一種差異之別,而非高低之分。這種宇宙觀反映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則具體化為如下一種現實的存在:當家庭內部缺乏一個有能力的男性領導來完成外在的事務時,女性也會被指望主動出來主持局面,并由此獲得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外在機緣與合法性。正是這種整體性思維,構筑了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很有生命力”[13]的性別文化哲學體系。#p#分頁標題#e#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整體性思維特征的第三重體現,表現在儒家傳統對于倫理秩序和“孝道”的推崇。在儒家看來,整個社會的和諧與平穩延續,來自于五倫秩序的最終實現,在此之中,“孝道”既是一切禮制秩序的根源和基礎,也是全部道德意識和道德規范的起始點[14](P131)。因此,雖然“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看上去將女性明顯地置于男性的權威之下,但孝道原則卻在事實上弱化了這一性別等級結構,使得當面對著年齡長幼的等級秩序之時,性別秩序則成為了位于其后的次要選擇,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兩性之間的性別等級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在與父親的比照中母親的地位屬于“從”,但對于兒子而言,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對于“孝”的更高價值的推崇,則使得母親在人倫秩序中的地位顯然要尊于兒子,獲得參與原本屬于男性特權的政治事務的“文化和道義上的合法性資源”[15]。對于這一點,林語堂先生在其影響深遠的《吾國與吾民》一書中也已明確提出:“凡較能熟悉中國人民生活者,則尤能確信所謂壓迫婦女乃為西方的一種獨斷的評判,非產生于了解中國生活者之知識。所謂‘被壓迫女性’一詞,絕不能適用于中國的母親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首腦。”[16](P130)尤其當家中的男性家長———父親去世之后,更是如此。正是在“陰陽”、“家族主義”、“孝道”這些充滿了整體性與關聯性特征的觀念支撐之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兩性關系,并不像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那般激烈、對抗、緊張,而是在劃分了等級地位、活動界限的同時,也被賦予了一種相互融通、互生互榮、不可分割的溫和特征與“性別彈性(genderflexi-bility)”[17](P76)。這種關系定位贏得了女性的主動接受和配合,也由此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從而使得“傳統的中國文明因沒有產生公開的性別沖突和女性主義者的抗議而引人注目。”[18](P60)
四、西方早期女性主義:二元對立思維的延續與挑戰
西方女性主義雖然流派眾多,但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為主要組成的早期女性主義“三大模式”和“三大論”[2](P167)的一個共同之處則在于,她們均認為女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被歷史刻意貶低為劣于男性的“第二性”[19],父權制的長期存在則是造成這一狀況的歷史根源。同時,這也是解釋所有文明體中關于兩性不平等關系之所以產生的一個“普遍性的框架”[1](P60)。因此,如何從根本上挑戰父權制,從而“搗毀所有以性別為基礎的統治關系”[20](P25),成為了她們的共同目標所在。盡管西方早期的女性主義理論致力于反對傳統的兩性關系,但在方法論和思維上,卻仍然深受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換而言之,她們接受了“男性/女性”、“文化/自然”、“公共/私人”等二元劃分,并試圖使女性進入男性占主導的文化、公共領域,從而改變長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狀態。因此,這一理論體現出了一種激烈的對抗、緊張和張力的特征。
如在第二波女性主義(1960—1980)的奠基人西蒙娜•波伏瓦看來,兩性先天之間并無明顯的差異,是后天的教化和社會環境才逐漸將兩性特征區分開來,形成不同的性別存在。換而言之,女性并非生而為女人,而是被塑造成女人,從而成為了男性“主體”(thesubject)的對立面而存在的“他者”(theother)[19](P5)。同時,她承認在兩性特征之中,男性的理性、智慧是更為優秀的品質,因此,女性應當放棄自身的情感、不理智等特性,通過模仿男性,并最終變成男性,來最終改善自身的地位。受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深刻影響,她還明確提出,女性應當像男性一樣出外工作,甚至應該不結婚、不生育,從而摒棄生理上的弱點,取得與男性一致的地位和權利。
而在當時影響甚為深遠的激進的女性主義,則堅持認為男女兩性有著明顯的差異,而且在這種差異中女性屬于更加高明的一方。不僅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生理缺陷[19](P4),從倫理道德方面看,女性特征和品質也要遠遠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犧牲、母性和關懷倫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殘忍、看重攻擊性和競爭性的道德標準。為了獲得女性所應當享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女性不需要追求與男性的平等,而是應當視男性為敵人,并從各個方面爭奪一切權力,占據一切主動地位,因為“女人比富有攻擊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適合、也更有能力領導這個社會”[22](P176)。可以看出,早期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無論是試圖放棄女性的生理特征、通過模仿男性進而改變自身弱勢地位的各種努力,還是試圖通過發掘“女尊男卑”的各類特征進而顛覆傳統父權制的激進做法,無不體現出了一種激烈的沖突、對抗、緊張和張力。從本質上而言,這種觀念仍然是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中二元對立思維的反映和延續,并在客觀上進一步強化了兩性間的對立關系。
五、中國女性主義的本土資源
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潮影響,研究中國女性地位的學者大多認為,傳統中國的女性同西方女性一樣,都處于被動、受壓迫、政治上無權的地位,“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就是這一狀況的典型寫照,而傳統中國的性別格局之所以能夠形成,也來自于與西方社會基本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傳統。當此之時,整個思想界對于“‘自我’(中)與‘他我’(西)的認同進行了激烈而徹底的轉移”[23],“五四父權壓迫模式”自然而然成為了他們分析傳統中國社會的性別關系的固有模式。但是,這種觀念忽視了中國政治思維模式與西方政治思維模式之間的差異,從本質上而言是服務于當時特定時代任務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整體性”和“關聯性”特征,曾內在地賦予了中國女性以廣闊的活動空間與富有靈活性的政治權利,兩性之間的關系和地位,也遠不像五四父權壓迫模式所認為的那樣,充滿了殘酷的壓迫與激烈的對抗,而是更為溫和、協調。
目前學界對于中國漫長歷史中兩性分工模式之下的女性日常生活的諸多研究已經證明,事實上這一女性群體并未被局限于家庭生活的內部,而是也有諸多跨越界限、參與外事的舉措,而且,這一群體對于外部的經濟生活、法律訴訟以及宗教生活等各類活動的參與程度之深、范圍之廣,實際上遠遠超越了五四“父權壓迫模式”影響下的人們所能想象出的場景。如鄧小南在《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婦女———以蘇州為例》中就已指出,由于男性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治學、入仕和經商等事務之上,因此,事實上宋代蘇州士人家族中的女性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管理著家族的產業,并成為家族事務正常運轉和提高家族聲望所倚重的對象,并非只是男性的附屬品。[24]而美國學者白馥蘭的《技術與性別》、伊沛霞的《內闈》、高彥頤的《閨塾師》、曼素恩的《綴珍錄》等等著作,已經通過對傳統中國女性的生活和地位等問題的詳細考察,令人信服地證明,傳統中國的女性享有非常靈活、充滿彈性的社會活動空間。即便是在被普遍認為是婦女地位最低、最受壓迫的宋、明和清三代,將女性嚴格限制在“內”的空間之內、從而剝奪其參與外事的機會與可能性的觀念,在實際上也并沒有被真正嚴格地執行過。女性并沒有處于徹底被動、受壓迫的悲慘地位,恰恰相反,她們的生活充滿了活力,并且明顯地享有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權力與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在理解中國傳統思維之“整體性”和“關聯性”特征的基礎上,重新認識中國傳統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歷史處境,并進一步反思如何在此基礎上解構中國式的父權體系,而非簡單沿用西方早期女性主義的理論范式,也許才是中國式女性主義得以誕生的本土文化資源。#p#分頁標題#e#
六、結語:西方早期經驗的局限與中國本土女性學研究的展開
1990年代之后,受福柯學派要求解構宏大敘事的傳統論述方式與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強調多元文化論的理論強烈影響,后現代女性主義逐漸興起,并開始重新反思西方早期女性主義理論的單一視角和對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的解釋框架的執迷。換而言之,她們開始承認不同文化傳統具有不同的內在特征,并相信這種多樣性、多重性和差異性,才是“構成歷史的全部內容。”[2](P180)自此之后,這些學者關于兩性之間的關系認識與政治權利定位,逐漸摒棄了早期的對抗、沖突、張力的特征,轉而強調應當承認和尊重兩性不同的特征,并提倡應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彼此和諧、互為補充的整合性的女性主義。如法國學者雪維安•愛嘉辛斯基就在其《性別政治》中提出,女性主義者不應當沿用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強化甚至對立男性或女性中任何的“一元”,而是應當強調“多元”,承認兩性之間的差異,“勇于迎接混合所帶來的無法化約的差異”[25](P40)。兩性從本質上而言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差異互補、不可或缺的關系,女性應當與男性一起從不同的方面、角度共同解決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理想的境界絕不是男女互相抗爭,而是彼此認知到男女兼容并蓄的價值。”[25](P151)而且,她們也開始格外關注傳統中國的社會性別結構,并逐漸傾向于認為,傳統中國這種性別結構在很大意義上暗合了她們的價值取向,是非常值得鑒戒的一種性別模式。可以看出,中西政治文化傳統以及蘊含其中的思維模式的內在差異,曾造就了中、西兩種不同的女性主義特征。而在西方后現代女性主義與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資源的暗合之中,如何從中國自身的傳統中尋求資源,發掘兩種不同文化的有益因子,并彼此借鑒對方的積極之處,以便促進中國本土女性學的逐步建立和進一步展開,而不是一味地跟隨西方早期女性主義的單一視角和早期經驗,從而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旋渦,無疑應當成為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者和婦女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和任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