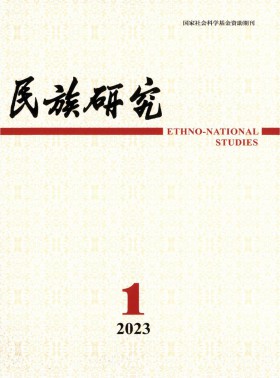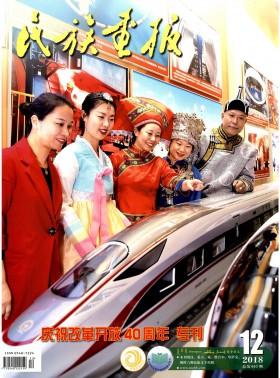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民族歷史精神法學啟發,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裴會濤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自1998年最高權力機關將民法典的起草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圍繞著民法典制定相關問題展開的研討論爭更是法學(界)的熱點,并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熱點。官方民法典草案已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分組審議。但距離最終產生一部內容完善、形式完備的民法典還遠,民法典相關問題的研討還將持續進行下去。筆者對民事法學了解極其淺薄,不過,技術性的規范留給(民)法學家解決,不會有什么困難,關鍵在于立法指導思想。出于對一部21世紀可能的中國民法典所承載的意義和負擔的使命的體認以及對歷史地位的期許,筆者藉由閱讀薩維尼名著而聊發淺議希能有裨益于是。
一、薩維尼的歷史法學思想
(一)歷史法學派和薩維尼
歷史法學派發軔于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鼎盛于十九世紀中,其創始人是哥廷根大學法學教授胡果,其主要著作是《從自然法到人定法哲學教程》。其學生薩維尼(F.C.vonSavigny,1779—1861)通過名著《論立法和法學的當代使命》、《中世紀羅馬法的歷史》《當代羅馬法歷史》以及《論占有權》全面而系統闡述使之蔚為大觀而成一主要思想流派。歷史法學派在德國以薩氏為代表,在英國則以寫出《古代法》而聞名的亨利•梅因(1822-1888)為代表。可以說歷史法學派是對興盛于十七、十八世紀的宣稱法律秩序是理性與正義的永恒表現的自然法論的“反動”,與中世紀的自然法論相信神是理論的最后歸依,和近代自然法學論以人類理性為理論基礎不同,歷史法學派著眼點不是法的目的而是法的歷史與成長。“在十九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薩維尼創立的歷史法學派的興衰史雖說不上是整個十九世紀的法學思想史,但是它卻是這部歷史的核心和最主要部分。”[1](P2)歷史法學派掌控德意志民族法律心靈幾近百年。迄《德國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正式頒行,薩維尼的嫡傳弟子于世紀之交相繼去世,其影響力日漸式微。正如十九世紀各個學派都是在自然法學派的衰敗中興起的,今天的各個法學流派也都是在薩維尼歷史法學派的衰落中興起的。
(二)薩維尼的法思想
薩氏學說主要是為了反對立法化和法典化時期自然法學派的立法理論。自然法學派認為只要通過理性努力,法學家就可以塑造出一部作為最高法律智慧而由法官按一種機械的方式加以實施的完美無缺的法典。在此思想指導下的立法往往忽視或者說蔑視歷史并無視傳統上的法律材料。他們認為人們僅僅做到如下三點就足夠:“第一,調動國內最強有力的理性;第二,通過運用這種理性去建構一部完美的法典;第三,是那些具有較少理性的人臣服于該法典的規定。”[2](P21)薩氏通過其對羅馬法的嫻熟掌握,以及對歷史的深刻憂慮在一個較短時間撰寫出有關立法和法理學的時代使命的小冊子對自然法思想進行批判,在無意識中創立歷史法學派。薩氏認為:第一,法是發現,而不是制定的。法的成長實質上是一個無意識的、有機體的過程。因此立法(Legis-lation)與習慣(Custom)相比較時立法處于從屬地位。薩維尼對法律產生的論述“……所以,這一理論總的意旨就是,一切法律均起源于行為方式,在行為方式中,用習常使用但卻并非十分準確的語言來說,習慣法漸次形成;就是說,法律首先產生與習俗和人民信仰(popular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學———職是之故,法律完全由沉潛于內、默無言聲而孜孜的偉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law-giver)的專斷意志所孕就的。”[3](P11)席瓦勒(SCHWANERT)指出:“吾人之所以得稱彼等為歷史派者,不過僅因彼等反對從來法由理性而生與法為任意創造物之假說,而主張法為國民生活之有機的發展之一點而已。”
其實關于法究竟為何物,是發成物(WERDEN)———演進的過程物,抑或作成物(MACHEN)———理性創造或者建構成物,或許是個永遠的話題,對于此做出過論述的學者如過江之鯽。比如哈耶克曾經根據進化論(在社會領域與其說是進化還不如說是演化更為確切,對進化與演化的區別及其背后不同的歷史觀,哈耶克曾經做過深刻論斷,沿用“進化”為了忠實原文)論述如下:“當然,人類交往的傳統規則,就像語言、法律、市場和貨幣一樣,都是一些萌發進化論思想的領域……人類現在必須放下架子,承認它也是起源于進化。”[4](P19)對于薩氏言,逐步地演化而形成的傳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傳統?哈耶克指出:“遺傳傳遞和文化傳遞的結果都可以稱為傳統。”[5](P22)習慣的產生與其說是由于民族內在的正義信念,不如說由于模仿的力量所形成。哈耶克看來,這種通過學習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規則的行為模式,是一個進化和選擇過程的產物,“它處在人類的動物本能和理性之間———它超越并制約著我們的本能,但又不是來自理性。”[6](P28)當其時,“理性主義”思潮彌漫整個歐陸學界,理性主義者認為“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圍的環境。”[7](P28)由于這種“建構論理性主義”把人類社會獲得的一切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于理性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的遵從,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對目標做更為恰當的籌劃和“理性的協調”,就能消滅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現象。而針對這種對理性的極致夸大,許多學者都進行過深刻剖析、反思。薩維尼對“追求改善的盲目激情”[8](P89)法典化思維后面的極致的科學理性思維做出深刻批評。而對于最為重要的立法問題,薩氏認為:“立法的目的可能有二:裁決糾紛(爭議事項),記錄古老習俗。經由對于爭議的立法裁決,將會消除人們迄今一直認為乃是阻礙實際使用羅馬法得一大障礙……立法的第二個目標是將習慣法記錄下來,據此方式,習慣法可得之于一種監理之下,一如羅馬法的敕令之于習慣法的效果。”[9](P97-98)
對習慣的重視使之認為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一部完美無缺的法典而是“……使習慣法復活———因而,也就是獲得真正的改善……那陷吾人于困境的法律史諸題,將會為我們了然于心,成為我們的財富。那時,我們可能會將羅馬法還諸歷史,而我們多擁有的,將不再僅僅是一種對于羅馬法制度的拙劣仿制品,而是我們自家的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10](P98)第二,堅持對法律史采用某種唯心主義(實證主義)(《法律史解釋》中說“某種”為已故西南政法大學薛倫倬教授在《近代西方法律哲學》一書中提出的)的解釋方法。薩氏接受十七、十八世紀自然法學派所主張的法律僅僅是“宣告性的”主張。薩氏還從實際的考察出發而斷言:“一切的法都是以習慣法這種方式發展而成的。”[11](P18)對于其觀點,著名法學家耶林在其名著《為權利而斗爭》中欲以闡述薩維尼、普塔二氏法律起源論之謬誤主張意思力為法之起源要素說到:“與我這見解相對立,至少在今日羅馬法學中,仍然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其他見解,我在此權且簡單地把它用兩個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字命名為‘關于法成立的薩維尼(SAVIGNY)———普夫達(PUCHTA)說’。依據這一學說,法的形成同語言的形成一樣,是在無意之中,自發自然形成的,既無任何角逐,亦無任何斗爭,就連任何努力也不需要。毋寧說,法的形成所依靠的是不費絲毫勞苦、緩慢且穩健地自行開拓前路的真理的無聲作用的力量,是徐徐的沁透人心的,并逐漸表現于行為上的信念所具有的威力———新的法規正如語言的規則,悠然自得降臨人世。”[12](P13)我們仔細考察薩氏的思想可以知道耶林的批評是精當的。對其精深掌握的羅馬法,薩氏深刻論證,做出了其來自自身內部的論述:“由此表現可以看出,羅馬法如同習慣法,幾乎全然是從自身內部,原融自洽地發展起來的。#p#分頁標題#e#
更為詳細的羅馬法歷史表明,整體而言,只要他繼續保持自己的生命狀態,則立法對他的影響是多么微乎其微啊。甚至對于上述制定一部法典的必要性的討論,羅馬法史也極具啟發意義。只要法律處于生機勃勃的進步狀態,則無需制定法典,即便在各項情勢均于其最為有利之時,益且無此必要。”[13](P26)從而為其反對當前法典制定找出歷史反對依據。第三,薩氏及其歷史法學派與此前的哲理法學派強調正義規則在約束道德體方面的內在力量和此后分析法學派強調政治組織社會的力量不同,堅持強調法律規則背后的社會壓力。[14](P24-26)薩維尼對應該如何立法、立法對習俗的態度、習俗對立法的作用做出如下論述:“立法……常常對法(law)的特定部分產生影響……立法者在變更現有的法律時,或會受到強有力的國家理性的影響。”“這里,或可制定一項立法,該項立法與習俗攜手協力,將凡此種種疑慮和不確定性一掃而光,而解釋和保有純粹的、真正法律,民族的固有的意志(theproperwillofthepeople)。”[15](P14)在此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也備受爭議的重要觀點———法應該契合民族精神。而這種局部性的民族精神或者說德意志民族民族性的和所謂的普世“異域因素”羅馬法的關系是什么呢?狹隘民族主義者做出“羅馬法剝奪了我們的民族性,我們的法學家們只關注于羅馬法,便阻止了將我們本土法律提升至同樣獨立而科學的狀態”的指摘。對此薩氏做出了精彩的論述:“事實上若無內在的必然性,我們的法學家對于羅馬法的研索永不可能達臻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持續下去。而且一如古代民族的發展,一個國族的獨立發展,通常并非絕對循沿大自然所已昭示于現代人的那種既定軌程亦步亦趨。各國族的宗教并不一定是他自身所獨具的,其文學亦甚少擺脫最為強勢的外部影響……基于同一原理,他們擁有一個外來的、一般的法律體系,亦未非不自然。”[16](P29)這樣為繼續沿用羅馬法做出了論斷,從而在反對新的立法之時不至于沒有可以使用的法律。
在一個歷經拿破侖推行法語傷害德國人民族情感,直可和滿清入關強令漢人削發相比的時代,在大革命余韻不絕如縷的時代,薩氏從自身情感出發,本能地反對對法國亦步亦趨。但是他用一個巧妙的藉口,就是復興羅馬法,而復興羅馬法在一個追求進步的時代是會被斥責為倒退、保守的。要是想使他們不打著進步的旗號去做翻天覆地慨而慷的事情,使民族精神、文化得以傳承,薩氏論述了立法能力不足的問題:“如果我們的能力不敷應對,則我們竭思改善自身狀況反而必會為一部法典所損害。”薩氏引證了培根的話:“應該制定一部法典的時代,必當在智慧上超邁此前的一切時代,因而,一個必然的結論乃是,其立法能力必定為其他時代所闕如。”[17](P35)從來都是認為時代是在一直進步的,今人勝前賢,從不承認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道的人會發現:“不幸的是,其整個十八世紀,德國不曾誕生什么偉大的法學家。的確,亦曾有過一些勤奮耕耘者,他們鋪陳了極有價值的準備工作,可除此之外,便乏善可陳。”[18](P35-37)薩氏說的話或許不僅僅對當日的德國適用,亦適應今日我們這個偉大祖國的偉大時代,當然了,我們實際上或許沒有感受到而已。培根說:“倘無迫切需要,則不當立法;即便立法,亦當慮及現實的法律權威。首先,審慎認真地繼受可得適用于現有法律權威的一切;其次,凡此應續予保留,并時常查考。”總之他說:“只有在文明和知識已然超越前代的時代,才可操持此業。如果以往時代的作品因為當下的無知而遭毀棄,那才真正令人堪悲呢!”[19](P35)對以往有清醒的認識,同時認真鑒別當今,如果想做到這樣,那么,“法學家必當具備兩種不可或缺之素養,此即歷史素養,以確鑿把握每一時代與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統眼光,在于事物整體的緊密聯系與合作中,即是說,僅在其真實而自然的關系中,省查每一概念和規則。”[20](P37)
二、今日民法典制定爭議之場景
如前面所說,對于一部民法典制定的急迫而在法學界引起的討論可謂轟轟烈烈,出于各種莫可名狀的心態支持早上、快上的論調更是統治了輿論的走向。梳理一下大約可以說得出口的理由有如下:第一,時代的需要。比如梁慧星教授說:“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動力是我們的民族要現代化,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我們要求民主法治。”[21]第二,歷史發展的必然。梁慧星教授說:“依據法律發展史,法律的發展軌跡,是由習慣法進到成文法,在進到法典法。先后發生過三次民法典編纂熱潮……可見,制定民法典是現代法治的一個共同經驗。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當然也應通過制定民法典來實現。”[22]第三,拔然超乎其上。謝懷木式老人說:“法國民法典史19世紀初世界最優影響力的法典,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初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典,我希望中國民法典能成為21世紀初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典。”[23]第四,民族智慧展示。楊振山教授說:“我衷心期盼著中國民法典能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和智慧,并能在中國古老輝煌的文明史上續寫出絢爛奪目的一章,使誕生于21世紀之初的中國民法典更好地造福于中國人民,并為全人類做出貢獻。”[24]第五,為全世界做貢獻。劉凱湘教授指出:“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能向世界法治做出貢獻的惟一一次機會。”[25]第六,使命感。憲政專家季衛東博士:“由于中國的現代化以及經濟體制發展的路徑有其鮮明的特點,加上全球化導致社會范式大轉換,所以這次進行民法典編纂可以說是負有宏偉使命的。
即:以20世紀的制度文明的集大成為基本目標、以適應國情和未來世界趨勢的理論創新為更高追求。”[26]其實,每一個學習法學的人都會對自己領域能有一個規模宏大的活動感到興奮,民法典制定這個大事件對于一貫孱弱的法學理論界、法律實務界可以說真的是很挑撥神經的。但是面對一個莫名的驚喜我們應該抱以什么態度呢?欣喜若狂地歡呼擁抱抑或仍然保持冷靜理智、用深刻的歷史分析去面對呢?智者早就告訴我們在任何時間都應該保持頭腦冷靜,而我們包括那些擁有聰明腦袋的大學者們在出現看似驚喜的情況下是會忘記智者的教誨的。人是容易自以為是的,而歷史對我們屢屢重復的踏入同一條河流總是無可奈何的。卡多佐大法官說:“你們要學習歷史的智慧,因為在各種相互沖突的告誡的曠野之上,它為你照亮一條小路。”“歷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時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際又照亮了未來”[27](P31)歷史為我們照亮了也許是太多的路,所以我們依然會迷失。對于我們當下的立法,如果我們驀然回首一下,其實那人(歷史老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對我們微笑。“這一立法活動,按其本性,本當立于整個國族的知識與智慧(science)之上,而現在就竟然這樣如同該國之一樁普通食物聊予完成了。凡此立法活動與民族智慧的量相分離,對于其所追求的結果來說,如果不是背道而馳,也是充滿危險的。”[28](P71)#p#分頁標題#e#
三、我們怎么辦
(一)我們知道,“從某一視角來看法律并無什么可得自我圓潤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質乃為人類生活本身。”[29](P24)其實正是我們看不上眼的世俗的繁雜的人類生活才具有真正的終極意義。對于我們真切的人生來說,正如薩氏提到僅僅“當法律是類如一種乖戾專擅之物,而與民族相背離”時才是應予譴責的。每一部分各有其分各盡其責以維持整體與部分間的均衡。而特性分明多元紛呈的個體性并不會對整體有任何不好作用,相反會增益整體的公共福利。”“任性隨意而突兀多變的法律”是最為有害的。”[30](P32-33)維持我們生活穩定其實是很重要的,對于我們一直持續的歷史進程抱以敬畏態度也是很有必要的。“歷史,即便是一個民族的幼年,都永遠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導師,而在類如我們這樣的時代,她還負有另一項更為神圣的職責。只有通過歷史,才能與民族的初始狀態保持生動的聯系,而喪失這一聯系,也就喪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為寶貴的部分。”[31](P86)而我們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年那么久歷史的國族呢?
(二)我們這個時代到底需要不需要一部法典呢?睿智的薩維尼說:“但是,這樣一個時代自身并不需要一部法典:正如我們為冬季預先儲物,它只是在為更為不幸的后繼時代創制一部法典。可不,沒有一個時代不為子孫后代而未雨綢繆。”[32](P20)對,就是這樣,切記是我們這個時代自身不需要,但我們切切不可以因此而無為,我們今天做的一切或許沒什么意義,但是如果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來說我們做到了承上啟下,縱不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僅僅為后人奠定些許基礎也就可以了。退一步講,即使我們需要甚至不止一部法典,也不是現在。薩維尼曾經論述立法活動尤其是在沒有充分基礎的立法活動是對法學本身的扼殺,可以說是法學“終結者”。比如他提到:“在公元6世紀,當其時,所有的知識和理性悉皆沉寂,往昔較好時光的流光碎影遂被收集起來,以滿足時代的需要。這樣在一個極短的時段中,若干羅馬法遂的編纂……不過,很顯然,只有在羅馬法極度衰敗之時,才會出現編纂這些法典的念頭。”[33](P26-27)我想任何一個倡言制定民法典的法學家對這個論述都會觸目驚心吧。
(三)假使我們真的非要制定一個彰顯文治武功的東西,我們也必須具備歷史的頭腦我們應該這樣去做,“如果我們以飽滿的創造力全力應對,將我們的一切深植于歷史而掌握歷史,以先輩的全部智慧財富武裝自身,則可受其嘉惠。職是之故,我們沒有選擇,要么如同培根所說交談本身即為一種溝通,要么藉由對于乏力的精深研究,學會如何自如運用歷史材料作為我們的工具……此外便別無選擇。”[34](P84)真正應該采取的態度其實應該是:“我們必須責令自己對子孫后代負起一切最為沉重的責任。歷史精神乃是低于自我妄想的唯一保障,這種自我妄想不僅在一切國族和時代,而且尤其在某些人群中,時時復活。就是說,對于我們來說,可能極少報持這種妄想,而就人性來說,總體上看卻很普遍。”“只有當我們藉由廢寢忘食的研究,使我們的知識臻達完美境界,尤其塑育了我們歷史感與政治感之時,才可能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作信實的評判。”[35](P85)只有如此我們才可以面對我們所面對的真正的問題。“當西奈山上的猶太人厭倦了遵奉上帝律法之時,他們迫不及待地鑄造了一頭金牛,真正的律表隨即被摔成碎片。”[36](P99)“歷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時也照例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際,也照亮了未來。”“如果這個新時代確實是那時候到來的,那么他還在濃重的云霧之中,透過云霧的稀疏光芒也許已經預示了新一天的到來,但這些光線還不足以照亮道路。”[37](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