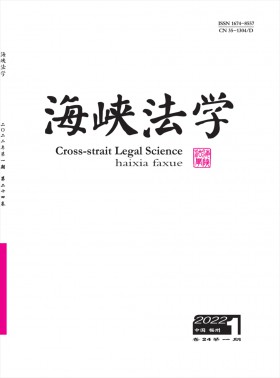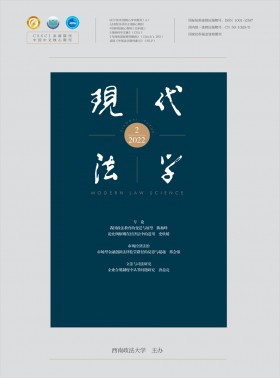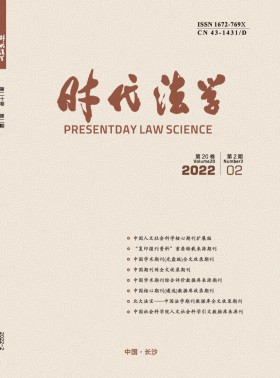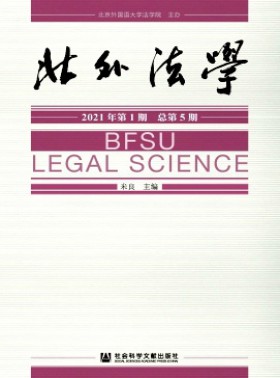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法學研究中的實證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社會學方法又稱“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由自然科學移植而來。這種方法認為社會研究的邏輯是假設演繹,科學假說的陳述必須由經驗事實來檢驗,理論僅當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時才是可接受的。實證的社會科學把自然科學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把自然科學當作科學的范例。 法學研究中運用的實證科學方法主要包括:(l)歷史文獻方法,即從歷史文獻中尋找經驗材料,從而使法學理論具有歷史根據。(2)調查,主要指對現狀的調查,可以分為抽樣調查和普查。抽樣調查的效果通常取決于樣本數量和樣本的代表性。(3)觀察,即借助于觀察者的眼、耳、鼻、身等感官,直接感受研究對象的特點。觀察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觀察即研究者的觀察,這種方法在法人類學、犯罪學、法律實施效果的研究中有廣泛的應用。另一類是機器觀察,即研究者借助機器設備如錄像機、錄音機等觀察研究對象。(4)實驗,將研究對象放在一個可控制的環境中,觀察和研究在條件發生變化時對象的變化,即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一個變量的變化是否會導致另一個變量的變化。 歷史文獻的真實可靠一直是歷史考證的關鍵問題。史料的重要性對社會科學研究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史料的發現往往是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但對已有史料的整理也很重要。歷史文獻的作者不可能將歷時發生的每一個事實源源本本地記錄下來,總要經過加工、整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現在有許多翻案作品,其實就是把過去被史家隱去的東西曝光,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許多后現代的研究即屬此類。這顯然和研究者的主觀性,包括他們的歷史觀有直接的關系。比如,過去占主流的羅馬法律史學家一直把現代西方法律傳統看作是古羅馬法的繼續,而羅馬法具有原生性、獨特性、純粹性、優越性、自我更新能力及其自身歷史的連續性,似乎羅馬法是優等民族的產物,不受其他文明的影響。意大利羅馬法學者孟納特里運用“去合法化”(delegitimizing)理論或福柯“考古學”的方法提出,“所謂‘羅馬法’,其實不過是一種包括非洲、閃族和地中海文明等在內的多元文化的產物”。早期羅馬法所固有的重大缺陷,如缺乏一般契約、政府理論,私法實踐中的巫術色彩,解紛機制中缺乏強制執行機制,缺乏法律學院與專職法官等,直至公元3世紀大危機之后才獲得明顯改觀。現在人們所推崇的羅馬法并非羅馬人原生的產物,而是羅馬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非羅馬化”的產物(P.G.Monateri,BlackGa乞us:AQuestfOrtheMulticulturalOriginsofthe“WesternLegalTradirion”,slHastingsL.J.479,Mareh,2000)。 在觀察、調查和實驗時,人們經常會發現,當被研究的對象了解到自己被觀察、調查和實驗時,他可能特別警惕,他的回答或行為可能根本不是他平時的狀態。如在進行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調查時,問卷提出“當你被你的領導或老板打傷,你將采取那種方法解決”,選擇的項目有:找本單位或本村的領導,找工會婦聯等,找打人者的上級,找司法部門,暗中報復,忍忍算了。 研究對象平時很可能視環境采取私了或忍忍算了的方式,但他考慮到找司法部門解決可能是這道題的最佳答案,又聽說這是上級機關或法學研究機構主持的調查,從而對該問卷的回答可能和他平時的態度和行為完全不一樣。 研究者應該盡量把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排除,不能先人為主。與自然科學家不同,法社會學家本身的價值觀念常常不可避免地帶人到研究對象中,因此要想保持價值無涉,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國社會早己進人了利益多元化時期,在許多強勢群體的利益鏈之下,研究者本人的利益往往也滲人其中。很多時候,持有不同立場的法律研究者,往往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場的各種“證據”。所謂客觀公正的調查,常常只不過是為固有的立場找根據而已。 社會學研究離不開統計數字,用事實說話、用數字說話,是法社會學研究的特點。但是在運用統計數字時,必須注意數字的真實性,防止數字造假。如在進行社會治安、環境污染、計劃生育等情況的調查時,有研究者經常依賴當地主管部門的統計數字,而這些數字又往往和各種各樣的“一票否決制”相關。為了壓縮這些數字的“水分”,研究者必須學會運用其他的方法校正。 比如,判斷一個地區治安狀況,不僅要看犯罪率等指標,還要看當地普通群眾的安全感。如果一個地區報告的犯罪率很低,但是群眾的安全感卻很差,犯罪率的數字很可能水分大。在進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律指標、統計數字的比較時,不應一味迷信數據,要注意數據的內涵和可比性。比如,在犯罪率的研究中,由于在不同國家犯罪的定義可能不同,在美國屬于輕罪的行為在中國屬于治安管理處罰的范圍,不了解這個前提而單純比較中美兩國的犯罪率,就毫無意義。在一國范圍內,盜竊1000元在一定時期內作為立案標準,修改法律后,盜竊罪的立案標準改為2000元,這樣就會使相當一部分盜竊行為“非罪化”。如果不了解這個變化,單純看犯罪率的變化,常常也會誤讀。在調解結案率的研究中也是這樣。1990年代以前我國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為70%多,民事訴訟法制定以后,審判結案率上升,調解結案率下降到30%多。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以來,又開始強調調解,現在的司法統計中把撤訴的數量也算在調解結案率中,這樣調解結案率變為60%或70%多。撤訴可能包括調解作用的結果,但有些撤訴與調解無關。把調解結案率與撤訴率捆綁在一起,有些像文字游戲,而且和以前的調解結案率內涵不一樣,是不可比的。 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防止研究的主觀性,增強客觀性,從而使研究的結論更加客觀、公正和可信。但是如上所述,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歷史文獻、調查、觀察、實驗等,任何一種對研究基本素材的處理方法,統計、比較、指標的設計等,都不可能擺脫研究者或被研究對象主觀性的干擾。 關于如何解決上述難題,一直存在爭論。一種觀點主張增加法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改進研究方法,在方法上盡量仿照自然科學,從而使法社會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這種觀點認為,法社會學應該盡量使用客觀的數據、法律指標,如犯罪率、離婚率、訴訟率等等,來描述和衡量研究的對象,“問題不在于是否能把研究對象轉變為法律指標,而在于怎么轉變的問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能過分依賴所謂的客觀數據和法律指標,過分依賴這種方法的結果是徒有大量的數字,卻對其不甚了了。他們所依賴的常常是自己對行為的主觀描述和解釋,而不管這些描述和解釋是否能被別人接受,是否能得到檢驗。在這些人看來,主觀性是社會科學的本性,完全客觀的就不是社會科學。#p#分頁標題#e# 的確,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現象而不是自然現象,用恩格斯的話說:“在社會歷史領域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3頁)。但另一方面,在社會領域中無數個別愿望、個別行動發生沖突的結果,“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同上),雖然行為的目的是預期的,但卻受到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支配。因此在社會領域,在人們有意識的行為的背后,同樣能發現人們的行為的有規則性、重復性和規律性。這就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基礎。 雖然法社會學研究很難避免主觀性,現有的法社會學研究方法,包括實驗、調查、觀察、歷史文獻,沒有哪一種能夠保證它是完全客觀的,不帶有研究者本人的感情、價值因素,避免由于研究對象的種種不真實的表現而帶來的誤導,但是通過一套社會科學的方法,可以盡量減少主觀性,增加客觀性。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過程就是一個主觀性與客觀性互動的過程。總之,按照社會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雖然不能完全避免主觀性,但是做比不做強,比完全按照主觀臆斷和猜想強。 應該看到,評價社會科學研究的標準,既不同于法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規范標準、合法性標準,如某一判決是否符合法律,某一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和憲法,也不同于價值標準,如某一行為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是否侵犯了人權以及各種不同價值之間的關系。它的標準是事實,即結論所依據的事實是否站得住,是否真實、可靠、全面。在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圍內,對某項研究的批評與反批評,往往也集中在引用材料的來源、獲取方式、可信度,真偽的辨別,材料所能說明問題的范圍,材料與結論的因果關系等等。一項認真的社會科學研究,盡管也難免主觀性,有些材料的取得和應用難免有問題,在材料真實性、全面性、可信性和結論之間經常受到質疑,但所有這些在方法論上都是可批評的和可改進的,由此可得出更接近客觀真實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