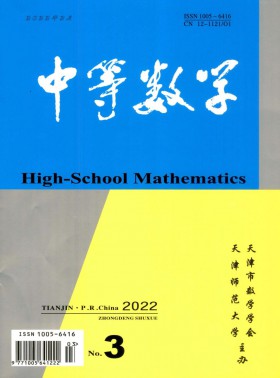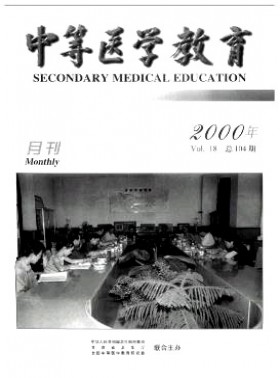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錢穆中等教學教育思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陸玉芹 單位:鹽城師范學院社會學院
教育是國家的基石。中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知識認同、人才培養的潛在中堅,作為學制系統中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中等教育改革的成敗,關系著整個學制系統的暢順與否,關系著各類國民教育之間能否和諧統一。但中國近代教育史的演進告訴我們,“1922年新學制(壬戌學制)的誕生,中等教育才完成了它的根本性的變革。”[1]歷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新學制在施行過程中,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社會對此褒貶不一。在時下教育部緊鑼密鼓地征集《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意見時,更有學者撰文“溫故壬戌學制”[2],該學制再次引起國人關注。1922年新學制頒布之時正是錢穆執教中學之始,本文以他1922—1930年執教中學的實踐為切入點,闡述他對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評和建議,從而闡發其中等教育觀,希望能為當今中等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1922年秋,錢穆辭去無錫老家的小學教職,接受廈門集美中學的聘請,開始了他的中學任教生涯。錢穆在集美學校擔任高中部、師范部兩個畢業班的國文課。他扎實的學問功底不僅得到了兩個班同學的認可,而且也得到了校長葉淵的稱贊。由于集美學校環境優美,藏書豐富,教學之余,他以讀書為首務。當時他對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很感興趣,以讀《船山遺書》為主,他不但通體細讀,而且還注意筆錄,積累了不少資料,這為他后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莊子纂箋》提供了不少幫助。1923年5月,集美學校發生學潮,錢穆因不滿意學校開除學生的做法,辭去教職,返回了無錫老家。錢穆返回無錫不久,當年秋天便轉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任教。錢穆進三師執教為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所推薦。他在無錫三師任一、二年級的國文課,按照學校的舊例,國文教師必隨班遞升至四年級畢業,而且每個國文教師每年必須兼開一門課。錢穆第一年開文字學課,第二年講《論語》,第三年講《孟子》,第四年講授《國學概論》。當時的錢穆雖沒有錢基博有名,但是他熟稔古籍,又善于下苦功鉆研學問,所以講授時有許多新的見解,很受學生的歡迎。據他當年在三師的學生、當代著名新聞學家、原《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回憶,“國文課特別重要,一周五天有國文課,還有幾小時讀經課。我就聽了錢先生一年課。這一年,他教《論語》、《孟子》。他教得與別人不同。他喜歡創新,喜歡突破別人做過的結論,總是要自己想,執著自己的見解。學生們對他很欽服。”[3]81
無錫三師是錢穆一生中正式開始從事著述的地方,他在研習這四門課時,自編講義,后來根據講義,編成了《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后改名為《孟子研究》)兩本著作。教學與研究緊密聯系,這種認真的教學態度和嚴謹的治學方式對他以后的教學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無錫三師這四年里,是他一生中較為愉快的一段時光,“三師風氣純良,師生如家人,四年未遭風波”[4]142。1927年秋,由無錫三師同事推薦,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任教學校最高班的國文課,兼任全校國文科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錢穆在蘇州中學成為最受歡迎的老師,據他的學生、原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胡嘉回憶,錢穆“講解古文,巧譬善導,旁征博引。他的‘國語盡皆吳音’,但吐音明白,娓娓動人。有時高聲朗誦,抑揚頓挫,余音繞梁……講課同時,他又講當時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還教學生做筆記。我因記錄詳細,并參考各書引證,受到錢先生的贊賞。”[3]87由于時局動蕩,教育部門經常發生拖欠教師薪水的情況,因此許多老師罷教,然錢穆“獨上堂不輟”,他認為“學校欠發薪水,乃暫時之事。諸生課業,有關諸生之前途,豈可隨時停止”[4]142。不管時局多亂,生活多苦,錢穆堅守崗位,承擔了一份教師所應有的責任。因為他相信教育可以救國,可以培養愛國激情,可以傳承中國文化。
二
1929年,錢穆在蘇州中學結識了當時學界名流顧頡剛,顧頡剛對他的新著《先秦諸子系年》非常贊賞,認為“君似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教歷史”[4]148,并說自己受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的囑托,代為物色有學術前途的新人,并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任教。由于蘇州中學校長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錢穆謝絕了中山大學的聘請。1930年6月,錢穆的又一力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在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此文的刊出,澄清了清末民初風靡學術界的劉歆偽造群經說的學術冤案,破除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在北平學術界造成了很大震動。經顧頡剛推薦,錢穆被燕京大學聘請,從此開始了他的大學教學生涯和治史歷程。錢穆雖執教大學,但對當時的中等教育改革卻是十分關注,加上他1922—1930年八年的中學執鞭實踐,使他對南京政府的中等教育改革有更深的認識,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
(一)中學“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應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五四”運動前后,西方教育思想大量傳入中國,國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教育改革運動。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了經全國教育聯合會充分討論的“新學制”(又稱“壬戌學制”)。“以發展青年身心,培養健康國民為基礎,承擔升學與就業訓練兩大任務,是新學制對中等教育階段的設計”[5]157,此學制關于中等教育目標定位明確,升學與就業并重,這既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新生,又為社會培養勞動后備力量,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5]15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用了1922年的新學制,但更加強調必須提高教育效果及學科標準,因此加大了中學課程的科目和難度,加重了中學生的學習負擔。錢穆指出:“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間江浙平津一帶而論,則中學校課程已不嫌其過松,而嫌其過緊。專就學業知識論,似乎所望于中學生者,已嫌過高,而不嫌其過淺”。錢穆認為,各個階段的教育都應有其宗旨與目標,“各階段之教育,本各有獨特之任務,中等學校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中等教育應該與大學教育不同,“知識學業之傳授,并不當占最高之地位”[6]51。
青年期的教育,主要應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而傳授知識和技能為次要的。然而當時“一二十歲上下之中學畢業生,已漸具書生氣,精神意識已嫌早熟,至大學畢業,年未壯立,而少年英銳之氣已消磨殆盡,非老成,即頹唐。”如此而來,“精神意氣早熟早衰,社會活力日以淪澌。倘更不于當前青年教育加以矯挽,國族前途,復何期望?”[6]52一語中的,直指中等教育學生負擔過重之要害問題。針對當時中學生“掩目于書本文字之中,體魄衰而精力糜”的舊病,錢穆提出中等教育首先應重視青年的體魄與精力的增強。他認為一個健康的體魄對一個人的一生的發展尤為重要,而中學生正處于青少年的發育期,各個方面的可塑性都很強,因此沒必要在這一期間只關注于學業的傳授,因為知識是無止盡的,而應該鍛煉青少年的體魄,培養他們的意志和情操。那么,如何做呢?錢穆“當盡量減少講堂自修室圖書館工作時間,而積極領導青年為戶外之活動。自操場進至于田野,自田野益進至于山林,常使與自然界清新空氣接觸。自然啟示之偉大,其為效較之書本言說,什百倍蓰,未可衡量”[6]52。在錢穆看來,一個理想的中學校園環境,“當使學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學校,恍然于一種新生命新境界之降臨”[6]54。體魄與精力的增強,除了走出校門走近自然外,還可以通過學校內開設體操與唱歌課程來實現。錢穆認為體操、唱歌課好似儒家禮樂,這兩門科目應為學校教育的最高科目,每日必修,不可或缺,師生同時學習,不分上下。初級中學應以樂為主而禮次之,高級中學則應以禮為主而樂副之。#p#分頁標題#e#
初級唱歌,適宜多用些舞蹈,以弘揚和平為宗旨,以大合唱的形式為主,以達到活潑動蕩、開拓學生情趣、暢悅他們胸襟的目的,同時輔助一些晨夕勞作、健身的游戲以及郊外的遠足等活動。而高中生應該以嚴格的軍事訓練和大規模的山林眺覽夾輔并進,以競技運動和一些莊嚴肅穆的歌曲加以輔助,其他的如童子軍青年營等訓練都應當切實重視。錢穆主張,“凡學校師生生活,皆當以禮樂為中心,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慧為目的。而知識技能之傳習,則降而次之”,但也有人懷疑如果這樣的話,則會造成學生學業下降,錢穆認為“不知茍其人體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則智慧自開敏,知識技能雖粗引其緒,他日置身社會,自能得路尋向上去”[6]54。錢穆認為當時的中學課程改革只有兩條路,即“精”、“簡”。只有這樣,學生們才能精力充沛,神智自生,“否則如買菜求多,學海深廣,青年力弱,終有沒溺之患”[6]55。錢穆這種中等教育理念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中學生陽光體育、素質教育十分相似,符合中學生心理身理特征,有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的成長,有利于為國家民族培養健康優秀的人才。
(二)“中等教育當以文化教育與人才教育為主體”。錢穆認為中國創辦新教育,始終脫不掉兩大弊病:一是實利主義,一是模仿主義。實利主義的缺陷主要是眼光短淺,不能從本源下手;而模仿主義則是依葫蘆畫瓢,照搬硬套,不能對癥下藥。錢穆耳聞目睹了實利主義和模仿主義教育模式下中學生急功近利的社會心理。各地的中學生在投考學校時,報工學院的人十分擁擠,而理學院卻很少;文法學院中報經濟學系的人非常多,其中經濟系的課程如銀行簿計會計管理為最,報經濟學原理者又次之;哲學系最不受關注,即使報哲學系的學生,五個人中至少有四個人是學西方哲學的,最多只有一個人學中國哲學。在文學方面同樣如此,學習西洋文學的人遠遠多于學習中國文學的。這樣的事實背后透露出的社會心理和社會風尚都是“實利主義”和“模仿主義”的教育精神在作祟。錢穆不禁自問:“若非為實利主義,何以群趨工科而不習理科?若非為模仿主義,何以群習西洋文學哲學而鄙棄本國文哲”[7]57?所以錢穆指出民國三十年來的新式教育,實際上并沒有擺脫模仿與實利。實利是目的,模仿只是為達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而已。
錢穆針對當時中等教育的弊端,提出了“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兩大口號,兩大口號互為表里,“乃主以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來陶冶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7]57。“文化教育可以糾正新文化運動以來之一味模仿,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時下科學教育專重實利主義之偏狹。”文化教育是手段,人才教育是目的,為實現此目的,他認為當時中等教育方面要作如下改革:第一,中學應分為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兩類。普通中學主要為文化人才的教育而設置,職業中學則為培養職業技術的專門人才而設立,性質不同。為做好學生的分流及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錢穆認為國立大學中以文理學院為中心,其他的專門學科,比如醫工農礦漁牧學等應因地制宜,多設一些獨立學院,同大學中的理工學院分開。前者為文化人才教育而設,后者為養成職業技術之專門人才而設,如此中學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按照錢穆的構想,凡是接受普通中學教育的人,其主旨是與大學中文理學院的教育相同,被看作國家教育的骨干。而各職業中學與各項專門獨立學院就象枝葉一樣,作為附屬的事物,它的施教、課程的安排,可以偏重實用主義教育,也可以模仿外國的成功模式,但不能作為國家教育的主體。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他還建議應多設各項補習學校、職業學校、專修學校,與普通中學并行。第二,中學教育的課務應以本國語言文字之傳習為主。錢穆指出,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應該是文字教育。“一國之文字,即此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之記錄之寶庫也。”[7]59由于1922年的新學制主要采用了美國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其教育理念頗受美國影響,青年學生主要精力花費在學習外國語言上,著重學習外國名著,而輕視研讀本國的語言文字,“二十年來,各大學、中學學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聲朗誦者,百分之百皆誦英文,絕無一人研讀本國文學者。若有之,其人必為儕偶所腹誹,所目笑,而彼亦將引為奇恥大辱”。這種思想的存在,導致中學畢業生都沒有閱讀本國古代書籍的能力,錢穆痛惜道“彼乃不啻生在一無文化傳統之國家。
彼心神之所接觸者,僅限于眼前數十年間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從潛深?意志何從超拔?趣味何從豐博?胸襟何從豁朗”[7]60?這樣的教育怎能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怎能使中學生感受中國的燦爛文明?針對這樣的情況,錢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必須以能夠閱讀本國的古籍為中學畢業的最起碼標準,因此必須調整課程和課時,他建議關于各項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授時間,最多不能超過研習文字文學課程的一倍。而對于外國文字文學研究的時間,最多也不能超過本國文字文學研究時間的三分之一。此外,一方面在大學里培養一批能夠勝任中學國文科目的教師,另一方面由國立編譯機關翻譯大量外國書籍以減少學生學習語言的時間。高度重視研究本國的語言文字,有利于培養中學生扎實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不僅培養了他們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感,而且對自身文化素質的積淀大有益處。“若使青年能讀一部《論語》,讀一部《莊子》,讀一部《史記》,讀一部《陶淵明詩》,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鍛煉,趣味之提高,胸襟之開廣,以至傳統文化之認識,與自己人格之養成,種種效益,與上一堂化學聽一課礦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謂其于教育意義上無裨補。抑且毋寧謂教育之甚深意義,實在此而不在彼”[7]59。
(三)中等教育應重視真正的“國史教育”。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古史辨”運動影響到中學,使師生不相信古史,“疑古”成為一種社會思潮。時在中學任教的錢穆主張治史不應專以疑古為務,“疑非破信,乃立信”。錢穆并不反對疑古,但與古史辨派不同的是,他認為懷疑本身并不是治古史的最高目的。他認為應以信疑偽,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他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就是先破后立的碩果,此文使晚清以來經學上激烈的今古文之爭頓告平息,在近代經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由于此文的深遠影響,加之顧頡剛的再次推薦,使得既無學歷又無文憑的錢穆得以進入燕京大學執教。錢穆在中學教授國文,到大學后講授歷史,他開始反思中學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一是中學文科教育高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結果課程支離破碎,漫無準繩;一是中學理科提倡科學教育而未得其方,大學專門之風氣浸尋波及于中學。”[6]54#p#分頁標題#e#
錢穆認為應該尊重國史,重視國史教育,提出“真正的中國人就必須學習中國史”和“歷史有助于養成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的觀點。他認為,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唯一起碼的條件就是誠心愛護中國,不是空洞的愛,“應該對中國國家民族傳統精神傳統文化有所認識了解”[7]65,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務。錢穆反復強調歷史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挖掘國史中的精華,并用來教育中學生,培養中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意識。錢穆通過自己的教育實踐和研究心得,結合當時抗戰的現實需要,指出了歷史、文化與民族之間互為依存的關系,“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里便是一種文化爭存。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作為民族生命淵源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目前的抗戰,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潛力依然旺盛的表現”。史地教育的責任,“卻不盡在于國史知識之推廣與普及,而尤要的則更在于國史知識之提高與加深。易辭言之,不在于對依然知道愛好國家民族的民眾作宣傳,而在于對近百年來知識界一般空洞淺薄乃至于荒謬的國史觀念作糾彈。更要的,尤在于對全國民眾依然寢饋于斯的傳統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認識與發揮”[7]69。錢穆反對歪曲歷史,反對空洞淺薄的歷史謬論,對史學界盛行的“重估一切價值”的觀念對中學的影響十分擔憂,他強調在抗戰的危急關頭,應通過真實的國史教育來培養學生的愛國激情和民族意識。
三
錢穆對中學教育的批評和建議主要發表于1941年的《大公報》(如《改革中等教育議》)和1942年《為四川省教育廳中等教育季刊》(如《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上,此時身為大學教師的他,看到由于大學強調專精教育和留學教育,從而影響了中學的培養目標。由于大學提倡“專精教育”,“時論多主提高中學程度以為大學專精之階梯”[6]51,由于大學提倡出洋留學,所以“大學各科教科書,幾乎十之七八以采用西洋原本為原則。大學新生,以先通一種外國文為及格標準”[7]58,使得追求升學的中學生將主要精力投在外國語言文字上。1922年,錢穆從事中學教育時正是“新學制”頒布時,民國新學制中關于中學教育的規定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學制系統的合理部分,又在制定過程中結合本國國情不斷加以修訂,浸透了大量學者的心血和汗水,所以就總體格局而言,比較科學合理。但由于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戰爭對學校的摧毀,學制在具體實施中存在不少問題,如由于缺乏經費、師資、教材、設備、校舍,不得不增開大量的選科;由于就業困難,許多中學生轉向投考大學等。錢穆針對當時中學課程繁多、學科紛雜、片面追求升學等弊端,主張青年學生應增強體魄以開發智慧,應感受經典以培養情操,應學習國史以增強民族意識。
與師范教育、小學教育、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民國時期的中等教育相對來說是個薄弱的環節,社會對此關注也不夠。錢穆對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評和建議,完全來源于他個人的實踐,并與其研究中國歷史的心得相結合,更出自于他對教育事業的關注與熱愛及對民族振興的使命與責任。他不僅對中等教育改革的具體問題如培養目標、課程改革、課時調整提出了批評和建議,而且對中等教育改革的理論問題如教育與文化、人文與科學等理論問題做了深層次的探討,不少見解至今仍熠熠生輝,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第一,應正確處理好基礎教育與升學教育的關系。錢穆針對當時中學教育過分重視文化知識傳授,中學生課業負擔沉重,一味追求升學教育的弊端,對中學教育體制下培養的缺乏“少年英銳之氣”、“非老成即頹廢”的“書生”提出了批評,主張中學教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他重視基礎教育,力求給學生的多元成才提供健康的體魄和充足的知識、能力、素質準備。時下素質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幾乎人人皆知,但幾乎每所中學都在違反教育規律,中學生不堪課業重負,自殺現象屢有發生。在國家提倡教育中小學改革的呼聲下,錢穆的中等教育觀對當前的教育改革啟示很大。第二,應正確處理好教育的相對獨立與現實服務之間的關系。教育為社會服務是不爭的事實,但教育改革應依據教育本身的規律。由于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教育改革始終堅持“教育救國”的主旋律,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意識和為現實服務的“實利主義”色彩十分濃厚,中學生重理工輕人文的現象十分嚴重。教育的目的是“人才教育”,人才應是多元化的,為解決中學生就業與升學問題,建議多設各項補習學校、職業學校、專修學校與普通中學并行,他的這些主張對時下社會應該為多元成才創造更寬闊的空間,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第三,應正確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教育改革必然要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模式,但現代化不是“西化”。中國擁有優秀獨特的傳統文化,錢穆主張加強中學生的“文化教育”,中學教育應當加入使學生了解本國文化及民族性的特質的內容。因為要做世界人,非先從本國人做起不可。而民國30多年的教育,中學生常有將康德、盧梭等置于口頭,而不知王陽明、顏習齊是誰。
這樣的教育對當今許多中學生英語流暢而古漢語句讀不分的現象觸動很大。第四,應正確處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系。錢穆提出加強國史教育,培育民族精神,在當時主要是為了抗戰時愛國主義宣傳的需要。全球化時代并不代表世界所有國家建立了事實上的平等關系。全球化網絡化下的中學生處于世界觀人生觀的關鍵階段,價值取向多元化,培養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意識,鑄就中國的“脊梁”,避免民族偏見是十分必要的。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極大的“溫情”和“敬意”,反對“疑古”所帶來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偏見或否定,他的中等教育觀正體現了他的文化觀,正如他在一次演講中所言,“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數千年傳統文化,只許就目前當今以為教,是則教育脫離文化而成為無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難”[7]62。錢穆的教育理念正反映了他對中西文化的價值取向,他反對“全盤西化”,反對當時中國一味“抄襲”美國教育經驗的“實利主義”和“模仿主義”。他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主張學生體能和智能的全面發展;他提倡“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張中學生誦讀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他提倡“國史”教育,培養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意識,擔當起以文化復興來振興民族、建設國家的重任。教育關乎國計民生,如何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將現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的教育優勢互補,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整合過程,任重而道遠。#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