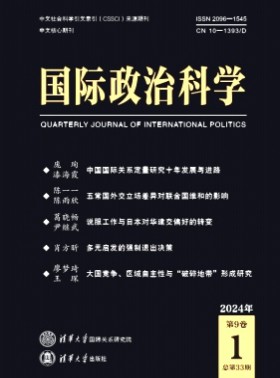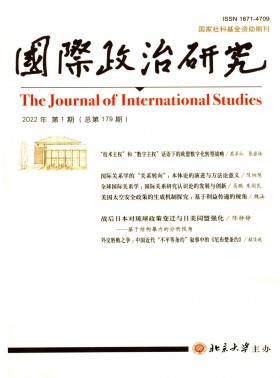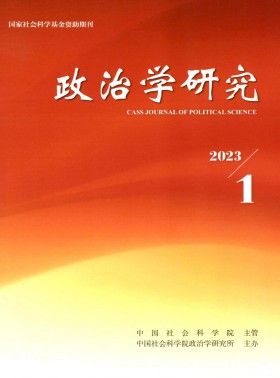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政治社會化的對比淺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胡滌非 單位: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
1.資料來源及樣本概況本研究的樣本均來自N大學。N大學是一所涵蓋了理工、文科、醫科等學科的綜合性“211工程”大學,從建校以來一直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包括港澳地區),是國內港澳大學生就讀最集中的高校之一。從2010年4月7日到7月27日,針對該校本科生做了863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833份,問卷有效率為96.5%。在抽樣設計上,首先按分層抽樣原則,將研究對象分為內地生和港澳生兩大類。再按等距抽樣原則,分別對內地和港澳大學生的宿舍進行編號。對于內地學生,按每間隔3個宿舍訪問該宿舍1個學生的原則,共訪問467個學生。對于港澳學生,按每間隔5個宿舍訪問該宿舍1個學生的原則,共訪問396個學生。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顯拒答傾向和不符合研究要求等情況的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833份。樣本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在生源地分布上,內地生452個,港澳生381個;在年級分布上,調研時恰逢2006級學生臨近畢業,因此大四學生樣本量明顯偏少;在性別分布上,男生345個,女生488個。
2.研究設計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以臺灣學者陳義彥在1975年所做的“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研究項目為基礎,結合當代政治社會化特點(如網絡等媒介的普及)和本項目研究目的修改制作完成。根據本項目研究目的,測量問項分為兩大部分:對政治態度的測量;對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力的測量。由于問項較多,而篇幅有限,本文并未列出具體問項。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將“政治文化”與“政治態度”幾乎是等同使用的[5]12-13。他認為政治文化包括公民對政治系統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參考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界定,在四個具體維度上對政治態度進行測量:對政治知識的測量,設計了4道政治知識題目,每答對1題記1分,分數越高表明政治知識越豐富;對政府政治信任的測量,通過詢問大學生對領導講話的信任度和處于困境時對獲得政府幫助期望值大小進行測量;對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測量;最后通過詢問大學生對自身影響政府決策能力的大小測量其政治效能感。影響政治態度形成的媒介是多種多樣的,大多學者認為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最為重要。我們的研究也選取了這四種媒介,觀察它們對大學生政治態度形成的影響:通過家庭媒介,了解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模式和父母的政治興趣;通過學校媒介,了解高中和大學階段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和學生對學校民主氛圍的感知與評價;通過社團媒介,了解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社團的積極性;通過大眾傳媒媒介,了解學生與電視、網絡、報紙等媒體的接觸頻率。大部分的問項都使用了四點式李克特量表,如在測量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時,針對“大學以前您的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參加討論或表達意見嗎”這一問題,請受訪者從“從不”、“很少”、“有時”、“經常”中選擇一項,在數據處理時,依次對這四個選項以“1”、“2”、“3”、“4”進行計分,分數越高,表明師生相處模式越民主。至于信度檢驗,由于政治態度和家庭、學校、社團以及大眾傳媒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力這五個維度的指標都分別包含了多個問項,因此有必要對每一維度所涵括問項的內在一致性進行檢驗(Cronbach′s a值檢驗),以剔除不相關的指標。根據統計學家Churchill、Kohliet和Parasuraman的意見,凡是總體得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4,且刪除該項目后a值反而會增加的項目都應該刪除。如表2所示,各指標維度Cron-bach′s a值檢驗結果分別為0.658、0.684、0.678、0.649和0.838,總量表的Cronbach′s a值為0.814,均大于0.4,說明本研究設計的各維度指標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資料分析與討論
1.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比較為了比較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是否存在差異,需要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如前所述,政治態度包括政治知識(0-4分)、政治信任(1-4分)、政治參與(1-4分)和政治效能感(1-4分)四個方面,將四個維度得分加總作為政治態度得分(3-16分)。在政治態度得分方面,內地大學生得分為8.915,比港澳大學生得分8.707高出0.208分,兩者的差異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如果將大學生政治態度得分合并為三組:消極政治態度(3-7分)、中間政治態度(8-12)和積極政治態度(13-16),可以發現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得分分布比較一致。如表3所示,內地和港澳大學生主要集中于8-12分的中間政治態度組,其中內地生的比例比港澳生稍高;第二位的是7分以下的消極政治態度,約有17.4%的內地生屬于此類,屬于此類的港澳生則更多一些,約占港澳生總數的22.0%;屬于積極政治態度的內地和港澳大學生都比較少,分別只有1個和3個。接下來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四個維度得分的具體情況逐一進行比較。由表4可知,除了政治效能感外,其他樣本方差都具有齊性。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知識得分和政治參與態度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差異較大:內地生政治知識得分平均為3.14,高于港澳生的平均得分2.72,經過檢驗,其差異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在政治參與方面,港澳生政治參與平均得分為1.73,比內地生的1.60高出0.13分,其差異也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在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上,內地和港澳大學生的態度存在少許差異,但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差異進行比較的同時,還應留意二者的相同之處:首先,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四個維度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序相同,依次為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參與。其次,多數大學生政治態度總分都在8到12分之間,居于中間水平。其中內地生在政治知識得分上最高,但其平均水平也不過3.14分(總分為4分)。在政治參與得分上,內地和港澳生都比較低,尤以內地大學生為甚,僅為1.60分(滿分為4分)。
2.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第一,各維度因子分析。如前所述,問卷主體部分可分為如下五個維度:政治態度、家庭媒介、學校媒介、社團媒介和大眾傳媒媒介。每一維度中又包含了若干具體問項。為了更清晰地觀察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對上述五個維度分別進行因子分析。由于政治態度維度只能抽取到一個因子,不需要進行降維處理,其余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需要進行降維。運用主成分法,通過直角轉軸進行因子分析,將loading小于或等于0.7的小載荷量刪除,根據剩余各變量的因子負載抽取到四個維度共八個因子。如表5所示,它們分別是家庭媒介維度(包含父母子女相處模式因子F1和父母政治興趣因子F2)、學校媒介維度(包含學校民主氛圍因子F3和師生相處模式因子F4)、社團媒介維度(包含校內社團參與因子F5和校外社團參與因子F6)、大眾傳媒媒介維度(包括電視媒體接觸因子F7和網絡報紙接觸因子F8)。第二,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政治態度的相關性分析。阿爾蒙德在對五個國家的公民文化進行研究后指出,家庭、學校、工作經歷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公民政治態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于這些媒介都屬于非政治領域,“非政治參與經驗與政治態度的關系并不是很明確。”[5]329那么,在我們的研究中,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這些政治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其關聯程度如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行二元相關分析,如表6所示。將前述八個因子所包含的問項得分分別進行加總,得到f1、f2、f3、f4、f5、f6、f7、f8共八個變量,再將這八個變量與政治態度進行二元相關分析,發現它們與政治態度之間都是相關的,父母與子女相處模式(f1)、父母政治興趣(f2)、師生相處模式(f4)、校內社團參與(f5)這幾個變量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與政治態度相關,其余變量與政治態度的相關程度均達到0.001的顯著性水平。研究結果表明,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是相關的。第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影響力的比較。將前文所述八個變量(f1、f2、f3、f4、f5、f6、f7、f8)作為自變量,以政治態度作為因變量,建立如表7所示的多元回歸模型I,該模型能夠解釋政治態度16.2%的變異量(Adj.R2=0.162)。其中,學校民主氛圍(f3)和電視媒體接觸(f7)這兩個變量在模型I中通過了水平為0.001的顯著性檢驗,校外社團參與(f6)和網絡報紙接觸(f8)變量在模型I中通過了水平為0.1的顯著性檢驗,其他的變量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變量對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有比較大的解釋力,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變量對政治態度的形成有一定的解釋力,其他變量則對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幾乎沒有解釋力。#p#分頁標題#e#
通過對模型I的分析,保留學校民主氛圍、電視媒體接觸、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這四個自變量,同樣以政治態度為因變量,建立如表7所示的多元回歸模型II。該模型雖然只有四個自變量,但這四個自變量聯合起來仍然能夠解釋政治態度16.1%的變異量(Adj.R2=0.161)。其中,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兩個變量仍然通過了水平為0.001的顯著性檢驗,校外社團參與變量在模型II中的解釋力有所提高,通過了水平為0.05的顯著性檢驗,網絡報紙接觸變量仍然保持了水平為0.1的顯著性。模型I和模型II可以在總體上展示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力,但仍然需要進一步了解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力是否存在差異。借助模型II,分別選擇生源類別作為內地大學生和港澳大學生的樣本,以政治態度為因變量,以學校民主氛圍(f3)、校外社團參與(f6)、電視媒體接觸(f7)和網絡報紙接觸(f8)作為自變量,分別建立內地與港澳生政治態度的回歸模型。如表8所示,就內地大學生而言,學校民主氛圍、電視媒體接觸、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四個變量能夠聯合解釋政治態度21.8%的變異量(Adj.R2=0.218),且所有變量都通過了水平為0.05的顯著性檢驗,其中三個變量(f3、f7、f8)更是達到了0.001顯著性水平,說明內地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與這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在港澳大學生群體中,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有所不同,能夠對其政治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的政治社會化媒介是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對政治態度的形成缺乏解釋力。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著顯著差異。就相同的部分來看,雖然學界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對公民政治社會化影響較大的媒介主要是家庭、學校、社團參與和大眾傳媒,但在我們的研究中,這些媒介聯合起來對政治態度的解釋力并不算大,最多能解釋政治態度21.6%的變異量(內地生回歸模型)。就差異部分來看,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解釋力都不夠大,相對而言,內地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較多地受到這些媒介的影響(Adj.R2=0.218),港澳大學生受到的影響就要小得多(Adj.R2=0.103)。觀察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大小次序時,由表8中標準化回歸系數可以發現,對內地大學生而言,對其政治態度影響最大的媒介是學校民主氛圍(β=0.300),電視媒體與網絡報紙媒介的影響力同列第二位(β=0.168),最后為校外社團參與的影響(β=0.120)。就港澳大學生而言,對其政治態度影響力最強的政治社會化媒介是學校民主氛圍(β=0.313),其次為電視媒體接觸(β=0.125),而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媒介對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則非常微弱。
結論與建議
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后,內地與港澳的交流合作,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影響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因素日益趨同。由我們的研究可知,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總體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對政治知識的了解和政治參與積極性等具體態度上的差異則比較明顯。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等政治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之間存在關聯,但這些因素聯合起來最多能解釋政治態度兩成多的變異量。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形成的影響力存在等級次序,具體而言,內地大學生政治態度較多地受到學校民主氛圍、電視媒體接觸、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等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主要受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導意義。首先,內地與港澳大學生的政治態度從總體上看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一事實說明,內地和港澳大學生并未因為家庭、學校、社會等早期成長環境的差異,形成分裂的政治文化,他們在政治態度上具有比較一致的認知、評價與情感。羅森幫(Rosenbau)認為整合的政治文化對于維護穩定的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就整個世界來看,世界的一方由于擁有整合的政治文化,其人民享有相當程度的和平和秩序,而另一方卻因離析的政治文化,國家深受不穩定的政治秩序之苦。可以說,世界各國政治文化的形態,可以粗略地排列分布于‘離析的’到‘整合的’政治文化的連線上,而中間有許多兩者混合的形態。”[6]因此,我們應該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繼續加強內地與港澳之間的交流合作,以利于整合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維持。其次,從政治態度總體特征看,內地和港澳大學生的政治態度主要分布在中間政治態度組,持有積極政治態度的大學生極少,這與他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高和政治效能感較低有關。這種政治冷漠現象可能會阻礙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順利完成,甚至會影響他們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成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表明,積極的政治參與可以提高個體對國家的責任感,對政治體制的寬容精神,使公民的民主觀念得以加強,民主能力得以提升。而較強的政治效能感則使個體更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因此引導和培養大學生形成積極的政治態度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特別要注重激發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增強他們的政治效能感。最后,研究發現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具有不同影響力,因此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要有針對性地發揮各種媒介的作用,通過最有效的途徑實現最理想的政治社會化目標。對于內地大學生,要特別注意學校民主氛圍的建立,通過電視媒體宣傳、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他們的政治態度進行引導。對港澳大學生而言,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等政治社會化媒介的影響尤為重要,而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的影響則幾乎可以忽略。當然,個體的政治社會化是漫長的、動態的過程,對其產生影響的因素非常復雜。
正如阿爾蒙德所言,“政治態度的來源有很多,它們包括早期社會化經驗和后期青年時代的社會化經驗,以及作為成人后的社會化經驗。它們包括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經驗,包括他人有意無意對政治態度施加影響而產生的經驗。”[5]293我們觀察的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對大學生政治態度形成的解釋力是有限的,尚有更多的因素有待我們去發掘。同時,由于缺乏縱貫的數據和資料,也未能觀察到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趨勢,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通過縱貫抽樣的方法加以彌補。#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