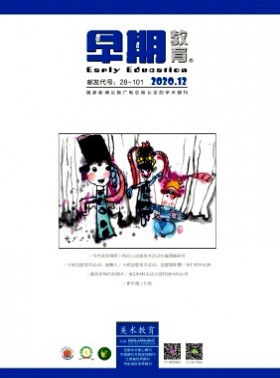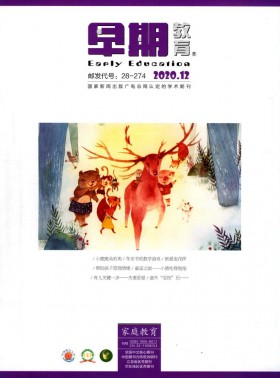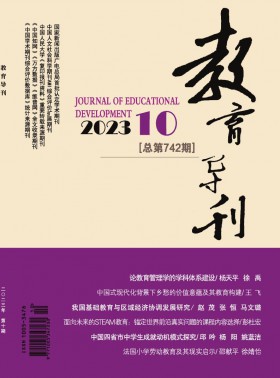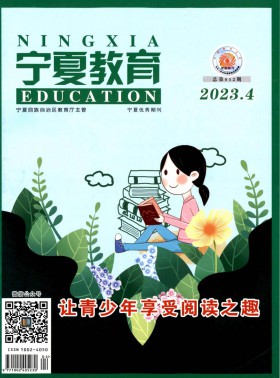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方式,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通識教育理論和實踐中的知識中心傾向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通識教育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界和實踐領域的一大熱點。在中國學術期刊網中輸入“通識教育”進行檢索,從2001到2010年的10年間有1230篇研究文獻與之相關。在實踐中,通識教育從早期的個體的、零星的實踐,到上世紀90年代末政府提倡并大力推廣的文化素質課程(通識教育)①實驗,逐漸演化到當下有組織的制度化的實施。除了通識教育課程的建設外,近年來,浙江大學(2000年建立竺可楨學院)、復旦大學(2005年建立復旦學院)、北京大學(2007年建立元培學院)、中山大學(2009年建立博雅學院)等高校紛紛成立專門的獨立學院對學生進行通識教育,把通識教育從理論到實踐上都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通識教育不再僅僅是一部分課程,而是一種整體的育人理念。在紛繁的通識教育理論和實踐中,如何實施通識教育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在實施通識教育上,中國大陸的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吸取美國的經驗,并努力將美國的經驗加以本土化。這些研究者把通識教育的實施模式分為四種:分布必修制、核心課程制、名著課程制、完全自由制[1]。分布必修制是指課程被分為若干知識領域,學生需要在指定的每一領域中選擇規定數量的課程。核心課程指在課程體系中有一些課程比其他課程更為基礎和重要,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學生必須修讀。名著閱讀是美國個別精英大學所施行的通識教育模式,課程主要內容是學生閱讀并討論指定的經典名著。完全自由制是指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想要學習的內容。這四種課程模式都在致力于解決以下三個問題:*學習內容的廣度(knowledgebreadth):分布制意在使學生能夠涉獵較廣的學科門類,了解并學習多個學科的知識內容和思維方法。集中制則與此相反。我們可以把分布制視為對“博”的追求,集中制是對“專”的要求。*學生對學習內容的選擇:選修意味著學生有較大的選擇學習內容的自由,而必修則與此相反。*學習內容的重要性:分布制認為學生需要涉獵不同的知識領域;核心課程制則認為知識體系中一些知識處于核心地位,比處于“邊緣”地位的知識更重要,所以學生也更應該學習它們;名著課程制則認為,最重要的知識都是那些經過時代考驗的、能夠體現人類文明精華和永恒精神的知識,這些知識通常都蘊含在名著經典中,因此學生需要仔細研讀經典著作。關注學習內容實質就是關注知識。當下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多集中于知識層面,尤其是對具體學習內容的選擇和優化,而通識教育的實踐也體現了這一鮮明特色。最近十多年來,通識教育改革圍繞的主線是通識教育的內容。從政府方面來看,教育部在1998年《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大學生加強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同時對文科學生加強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體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2]考察文化素質的正軌課程體系,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政策主要是指“開好文化素質教育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對理、工、農、醫科學生重點開設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對文科學生適當開設自然科學課程”。不難發現,文化素質教育(通識教育)的關注點是在知識上,具體來說就是知識上的糾偏和補漏,以實現平衡學生知識結構、擴展學生視野、促進學科滲透、提高學生文化素質之目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大學這些年來進行的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建設和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其主要目的和形式也在于此。北京大學的通識教育意在“引導學生廣泛涉獵不同學科領域,拓寬知識面,學習不同學科的思想和方法,進一步打通專業,拓寬基礎,強化素質,為適應21世紀對高素質人才的需要打下基礎”[3]。
復旦大學通識課程則旨在“打破分門別類的學科壁壘、貫徹人類學問與知識的共同基礎,并展示民族文化精神對一個民族的學問創新能力”[4]。表述雖然各有不同,但是對于知識內容尤其是知識廣度的追求(如“涉獵不同學科”、“打破學科壁壘”)基本是一致的。從具體課程設計上看,基本是在原來的公共必修課(如“兩課”和外語)外,加開文化素質類課程。這一類課程在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名稱,例如北京大學的素質教育通選課、清華大學的人文社科類課程、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南京大學的文化素質課等,但是課程內容覆蓋范圍大致相同。從已有的結果看,基本上覆蓋了自然科學、人文藝術類和社會科學三大領域的知識。[5]近年來各個學校自行的課程改革,基本思路也是不斷優化通識教育的課程結構,例如改革舊有的課程內容、增加新的教育內容、重新劃分通識教育模塊,等等。海外華人學者對通識教育也有很多精彩的論述。甘陽大力提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經典閱讀和小班討論模式。他認為,美國本科教育的真正精華是經典閱讀和小班討論。學生需要直接閱讀經典而不僅僅是上概論課;同時應當鼓勵并組織學生圍繞經典進行討論[6]。除回歸經典外,筆者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甘陽對通識教育中教學法(pedagogy)的關注,而這恰恰是當下通識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所忽略的。雖然不少通識教育文獻都涉及教學法,比如鼓勵教師引導學生、提倡課堂討論等,但大都流于空泛而缺乏實踐性。而甘陽則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實踐方案:深度閱讀,小班討論,并配之以相應的助教制度。這些思想大大推動了中國通識教育的前進步伐,也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不少學校的通識教育改革②。臺灣的黃俊杰認為:通識教育應當貫通古和今,科技和人文,本土和全球。他提倡學生閱讀傳統經典,接觸傳統文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思考、分析現代科技發展中的人文話題;在全球化特別是西方化的大背景下,應當繼承并發揚東亞地區優秀的文化歷史傳統,促進本土文化和全球視野的交融[7]。這兩位華人學者都具有濃郁的人文主義傾向。在他們所倡導的通識教育體系中,經典著作的閱讀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他們倡導的是中國式的“名著閱讀”課程,他們筆下的通識教育就等同于名著閱讀。從通識教育體系的構建角度看,在這一思想中,對經典著作(知識內容)的選擇,對人文知識的掌握和理解,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本質上講,這依然是一種知識本位的教育思路。分析上文關于通識教育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我們不難發現,它們都有鮮明的“知識中心”(knowledgecenteredness)傾向。在教育學術語中,這一邏輯通常被表述為學科中心(subjectcenteredness)。這一思路優先關注對知識和課程內容的選擇和安排,著力點都在如何優化教育的內容和學科上。具體來講,它們主要關注下述三個方面:#p#分頁標題#e#
1.哪些學習內容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例如,學生應該學習哪些課程?哪些課程可以作為核心課程?哪些課應該必修,哪些課應該選修?)
2.學習的廣度應當如何把握?(例如,學生需要涉獵哪些學科?每一學科修讀多少學分?)
3.學生對學習內容選擇的自由度應當有多大?(例如,應當讓學生必修還是選修?)
應當說,這種思考方式對于優化通識教育課程和內容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的通識教育也在對這三個問題的不斷深入討論和反思過程中逐漸成長并日益成熟。然而,當下的問題在于,我們過分關注通識教育的知識和內容,各種理論的爭議、現實的變革都旨在優化通識教育內容,而鮮有人對這一思維方式進行反思。
二、知識中心式通識教育的局限性
第一,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學習內容和現實問題以及學生個人體驗的聯系。當下關于通識教育的各種討論和實踐,主要關注通識教育的內容組織形式。具體來講包括:通識教育應當設置何種課程?應當覆蓋哪些知識領域?應當給予學生多大的自由度?而如何將通識教育的內容與現實問題以及學生的個人體驗相聯系,則相對被忽視。教育應當為學生提供好的、有意義的教育經驗③,這種經驗不應當僅僅是所謂的客觀中立的學科內容,而應當努力把教育內容同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當代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使學習成為對學生來說是有意義的活動。
第二,它缺乏對知識內部統一性和溝通性的思考。通識教育的特色不僅在于其公共性(即面向所有學生,為他們提供共同的學習體驗),更在于其系統性和溝通性。通識教育內容應當經過精心系統的設計,不同學科和課程內容應當密切相關并致力于共同教育目標的實現,而非互不關聯。然而,這一理念在當下知識本位式通識課程中面臨嚴峻挑戰。首先,時展和新知識不斷產生,客觀上導致了新科目的增加和課程數量的擴張。不少學校的通識課程數量都有幾十門,甚至上百門之多。龐大的課程數量使通識教育體系內部結構維持相對統一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因此,通識教育課程內部結構日趨凌亂和雜亂無章。而很多學校對通識教育課程數量的盲目追逐更大大加劇了這一趨勢。其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知識領域和思考方式上存在先天隔閡。以哈佛大學社會分析領域的三門課程為例,“經濟學原理”、“心理創傷”和“城市革命:早期國家的考古和探索”的基本概念、理論視角和思維方式彼此迥異,因此很難為學生提供共通的學習體驗。[8]這一弊病在國內的通識教育體系中更為嚴重。再次,通識課程在國內往往因師設課,隨意性較強,而欠缺系統的謹慎設計。這使通識教育更易流于大雜燴式的課程堆砌。在這種模式下,學生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互不相關的、雜亂的知識。
第三,它會逐漸遠離通識教育的初衷。關于通識教育的目標眾說紛紜,并且不乏華麗的表述(例如“全人教育”“、人格陶冶”)。其中一致之處在于,通識教育負責培養的是人之所以為人,或者說是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公民的“公共”部分。我們引用曾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羅索夫斯基對教育目標的表述:(1)能清晰而有效地進行思考和寫作;(2)在某個領域學有所長;(3)對我們獲取和應用知識的方式,對宇宙、社會和自身都有批判性的認識和理解;(4)對道德和倫理問題進行過思考;(5)免于對其他文化和其他時代的無知。[9]可以把上述目標簡要歸納為:培養交流能力(第1項);擴展知識廣度、培養廣博視野(第3項和第5項);具有文化道德意識和獨立判斷力(第4項和第5項)。這些目標遠遠超越了單純掌握知識內容的要求。要完成這些目標,不僅要精心選擇教育內容,更要關注這些內容是如何被傳達給學生,以及如何在學生頭腦中生成意義。傳統的通識教育繼承了學科中心和教師中心的特征:內容上很少與現實生活和學生的自身體驗相關聯;不同內容缺乏關聯,流于堆砌;教學方法也多是照本宣科,學生成為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學生很難有學習的熱情和興趣,只是被動地參與學習過程,更別說實現通識教育的目標了。
三、知識中心式通識教育的認識論基礎
這種過分關注知識和學科的通識教育,從認識論方面來看,在于把知識(knowledge)和生活世界(lifeworld)④看作兩個相對分離的領域,而且片面地把知識凌駕于生活世界之上。這種觀點有兩個基本假設。
一個假設是,知識領域可以統攝生活世界。因為知識是對生活世界抽象化、理論化、專門化的結果,它脫離具體的生活情境而存在,對生活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釋力。由于知識的高度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因此它可以應用于一切情境。另一個假設是,知識可以自發地轉化為人們的行動和實踐。學習者掌握知識之后,就可以成功地把它應用到生活的具體情境之中。在這兩個假設之上,可以把知識和行動視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并在一定時間內優先關注知識領域,讓學習者努力掌握知識。對學校教育來講,關注的主要對象就是知識。
經驗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則反對把知識領域和生活世界對立起來的觀點。首先,知識領域和生活世界密不可分,不可能把兩者從時間和空間上割裂開,兩者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對二者進行割裂具有邏輯上的先天缺陷。對二者進行割裂的行為容易導致知識越來越脫離現實生活和學習者的個人體驗。其次,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生活世界的參與。用杜威的話來說,知識是在學習者和周圍生活世界以及和自身歷史不斷互動的過程中被建構起來的。也只有被建構的知識,才是有意義的知識,有活力的知識,從而避免成為懷特海所說的“呆滯的觀念”(inertidea)[10]。第三,知識未必能自發地轉化為實踐。例如:很多事實證明,道德知識未必能直接轉化為道德行為。
在東方語境中,這一話題被表述為知和行(“行”的內涵要比上文的“生活世界”小)的關系。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曾對知和行的關系做過精彩的論述。在王陽明看來,知和行是不能割裂的。知先行后,容易導致知識脫離實踐領域,流于空想;而行先知后,則容易陷入迷惘。知和行本為一體,所以應該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11]傳統的知識中心式課程的不足在于:一是割裂了知識和生活世界,忽略了學習者的個人體驗以及學科知識和現實生活的關聯;二是割裂了知和行的關系,把知和行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因此,我們的教育活動需要做到:關注現實生活以及學習者的個人體驗,而非僅僅提供一些與個人體驗毫不相關的“客觀”知識;把知識和實踐/行動結合起來,知和行是一體的,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絕對對立;鼓勵學習者之間的交流和互動。#p#分頁標題#e#
四、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通識教育可能的新模式我們需要重新反思這種知識中心和學科本位的通識教育模式,并在溝通知識領域和生活世界、關注學習者個人體驗、推動“知行合一”的基礎上重新構建我們的通識教育體系。⑤在這一思路之下,筆者認為,可以采用“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下文簡稱PBL)來組建通識教育課程。PBL課程與傳統課程設計的邏輯起點迥異:傳統的課程設計是從具體的知識和學科出發來構建課程體系,而PBL則是在知識領域和生活世界相統一的基礎上(體現為具體的問題情境)來設計課程。
PBL具有深厚而廣泛的哲學和心理學基礎[12]。20世紀初期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和杜威倡導的教育思想和實驗都具有鮮明的PBL特色。在高等教育領域,PBL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醫科教育。之后,由于PBL模式在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提高教學質量方面起到了顯著效果,進而逐漸向其他學科、大學和地區擴展。當前,PBL早已從早期的醫科教育擴展到工程學科、社會學科以及人文學科等各個方面。在實施中,有的院校在部分課程中實施PBL,而有的學校則在全校實行PBL,把PBL作為學校課程設計的基本思想。在丹麥,20世紀70年代興建的奧爾堡大學(AalborgUniversity)和羅斯基勒大學(RoskildeUniversity)從建校伊始,就把PBL作為基本的課程設計哲學。在中國兩岸三地,當下理論和實踐對PBL的關注主要還集中在醫科領域。香港大學醫學院[13]、高雄醫科大學[14]、武漢大學醫學院[15]、中國醫科大學都對PBL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他學科對PBL的關注相對較少。就通識教育而言,目前仍然停留在學科中心的思維層面,對教學法的研究相對較少,而對PBL的介紹更是少之又少。有文獻顯示,臺灣的中國醫藥大學在開設通識課程時,有意識地進行了PBL探索[16]。
PBL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7]:
第一,問題中心
它有知識(課程)和教學法的雙重意義。從課程設計上看,是通過實際的問題情境而非僅僅依據學科內容來組織課程結構;從學習過程上看,問題是學生學習的起點,并貫穿學習的全過程。問題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可以是一個困境(dilemma)或矛盾(discrepancy),可以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工程問題,也可以是一個引導學習過程的議題[18]。真正的問題(problem)不是一個只有固定答案和解決方案的問題(question),而是一個需要不斷進行概念化的過程[19]。例如,當我們提問如何改進教育質量時,我們沒有現成的固定答案;而且當我們發問時,我們意識中的“教育質量”一詞的概念和含義可能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我們需要對提問的核心概念進行不斷追問和反思。從問題的提出到問題的解決,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問題本身將成為組織課程和貫穿整個學習過程的主要因素。另外需要澄清,PBL與案例學習(casebasedlearning)有著本質不同。案例學習的課程設置基礎依然是傳統的學科知識,案例居于次要地位,只是輔助學生應用書本知識,以便更好地理解所學內容。而PBL的邏輯起點與傳統課程模式有本質差異,PBL是通過問題(而不是固定的學科知識)來組織課程內容和學生的學習經驗。從學習初始,學生就被置于一個具體的問題情境中,通過問題的形成(problemformulation),學生在教師指導下自主地選擇學習內容,拓展學習經驗,實現問題的解決并在此基礎上對學習過程進行反思。
第二,跨學科學習
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是一個具體、復雜而又綜合的存在。學科知識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抽象性和專業性的特征。不同科目都有著自身獨有的理論視角、概念術語和思維方式。在傳統課程模式中,不同課程之間缺乏溝通,往往各自為政,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也很難面對復雜的生活世界的具體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打破學科壁壘,在課程設計上引導并鼓勵學生從一開始就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內容和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問題。
第三,小組學習
現代和當代的教育學理論和心理學理論都有一個基本共識:與他人的交流能夠有力地促進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所以,PBL提倡學習者以小組形式開展學習活動,完成學習任務。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能夠提高學生對學習活動的參與程度,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提高學習效果。此外,小組成員之間的交流還有助于學生交流能力的培養。
五、通識教育PBL課程的構建
我們可以以PBL理念為基礎構建一個新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圖1表示一個PBL通識教育單元。整個課程結構的邏輯起點是一個來自生活世界的具體問題情境。學生從課程一開始就被置于一個具體的問題情境中。一個PBL通識教育單元包含一個項目(project)和若干門互相關聯的傳統課程(lecture)。我們可以把圖中所示的PBL通識教育單元看作一個獨立的PBL通識教育包(package)。每一個package是一個問題情境,包含一個項目和2-4門內容上相互關聯的課程。不同的PBL通識教育包有著不同的問題情境,其所包含的學科課程也不同。學校可以負責設計若干個不同的PBL通識教育包,供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選擇,以增大通識教育課程的靈活性。
圖1PBL通識教育課程結構圖具體來講,項目是問題情境的實現形式。問題情境可能是籠統的、概括的、模糊的,所以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對問題情境進行進一步細化和分析,形成自己的問題;然后通過收集資料、自學、小組討論等形式對問題進行分析,并最終解決問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對問題情境的研究發展出自己不同的項目。項目的最終表現形式可以多樣,比如研究性文章、調研報告、產品等。由于PBL中問題占主導地位,項目的比例也相當重。在奧爾堡大學,學生從事項目和參與學科課程的時間大約為1比1。學生真正上課的時間只有50%左右,其余時間都花在討論和完成項目上。⑥
這一通識教育單元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科課程。雖然它們不是PBL設計的邏輯起點,但它們為PBL和整個項目的完成提供知識方面的支持。這些課程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在內容上也緊密相關,共同服務于通識教育目標的實現。在解決問題和完成報告的過程中,學生需要綜合運用從多門課程中習得的理論視角、知識內容和研究方法。這也體現了跨學科研究的特色。項目的完成主要以小組的形式開展。一方面,這符合建構理論的基本假設,即在人際互動中更有利于促進知識的建構;另一方面,這也有利于學生交流能力的提高。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居于主導地位,教師擔任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p#分頁標題#e#
這一方案的另外幾個特色在于:首先,它考慮到我們的現實國情,對原有通識教育課程體系觸動較小。它不需要打破目前的通識教育體系,而只需要對通識課程中的“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進行改造。這一部分在高校課程體系中約有10到15學分的空間。如果我們假定一個PBL通識教育單元中的學科課程為2學分,并且項目和學科課程學分數相同的話,那么一個擁有3門課程的PBL通識教育單元約為12學分,恰好在10-15學分之間,不會影響到現有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
第二,這一思路可以與現有的“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模式進行結合。現有的文化素質教育模式規定:文科生須修讀若干門自然科學類課程,理科生須修讀若干門人文類課程。因此,我們可以設計具有不同學科特色的PBL通識教育單元供學生選擇。例如理科生修讀人文類的通識教育單元,文科生選修自然科學性質的通識課程單元。與其讓學生選擇若干門互不關聯的課程,不如讓他們選擇經過精心設計的PBL通識教育單元。
第三,它可以避免我們當下實施通識教育貪多求大的傾向。PBL通識教育課程的思路是小而精,每一個單元包含一個項目和2-4門相關的學科課程。這一思路要求學校精心設計每一個不同的通識教育包,而不是一味追求開課數量和覆蓋領域的廣度。這也有助于避免學生學到一堆與現實生活毫無關聯的大雜燴的弊病。
第四,它更有利于通識教育目標的實現。經過精心設計的通識教育包,加強了知識和生活世界以及學生個人體驗的聯系,兼顧了知識結構的內在統一性,同時也可以鍛煉學生的行動和實踐能力。